汉斯-彼得·格罗申斯教授线下讲演“人类自然和文化多元性:文化多元性有共同的人类学基础吗?”
点击次数: 更新时间:2025-03-28
本网讯(通讯员 鲁彦君) 3月25日上午,应武汉大学哲学学院陈波教授邀请,德国明斯特大学神学教授、国际科学哲学院(AIPS)正式院士、欧洲宗教科学院前任主席和现任副主席汉斯-彼得·格罗申斯做题为“人类自然和文化多元性:文化多元性有共同的人类学基础吗?”的讲座。讲座由武汉大学哲学学院陈波教授主持,武汉大学哲学院郝长墀教授评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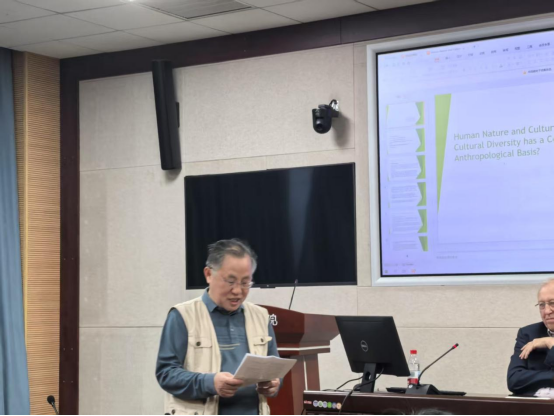
武汉大学哲学学院陈波教授主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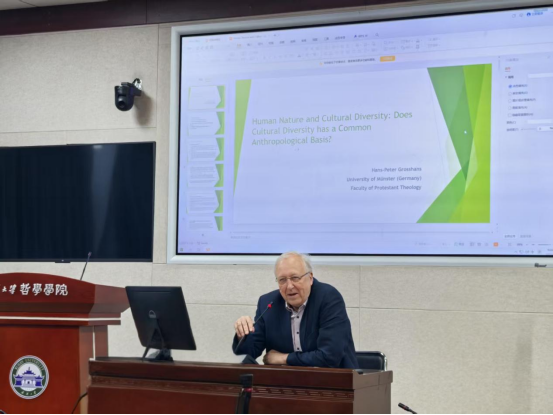
汉斯-彼得·格罗斯汉斯教授主讲
格罗申斯以全球化移民活动下跨文化的社会共存问题切入,围绕“宗教多元性是否具有共同的人类学基础”这一核心问题展开讨论,通过分析宗教多元性理论的历史演变和社会现实,提出需结合“主题性思维(topical thinking)”重构宗教多元性的理解框架。最后,通过德国哲学家施莱尔马赫的宗教人类学理论,论证宗教多元性根植于人类本性的内在特征,即宗教作为个体感知宇宙的独特经验,必然在表达与实践中呈现多元性。
讲座伊始,格罗申斯梳理了“文化”的四种定义:个人实践的文化(如农业、语言修养)、个人拥有的文化(如艺术家的技艺)、个人生活于其中的文化(如宗教、科学)以及被创造和推广的文化(如文学、音乐),并明确将第三种定义下的狭义文化作为讨论宗教多元性议题的基础。
格罗申斯指出,宗教是人类共识的一部分,正如罗伯特·贝拉将宗教分析为人类进化史的一部分,自轴心时代以来,宗教通过仪式与信仰凝聚家庭、群体和社会,促成了基督教、佛教等“世界宗教”的建立和帝国秩序的形成。但宗教对于一个社会或国家的身份认同与社会凝聚力越重要,它们就越深地渗透到与其他社会群体的所有接触之中——无论这些接触是友好和平的还是敌对侵略性的。而现代社会中的移民与信息流动使欧洲城市更加突出地呈现了多元宗教共存。
基于此,格罗申斯重新审视了传统宗教多元论。一般来说,宗教多元论是一种将一个社会(或全球)的宗教多元性及其相互作用概念化的理论,其既可以从社会中所有特定宗教的外部观点出发,也可以从特定宗教内部的各种观点出发。必须在每一种宗教内部或多或少地界定如何理解其他宗教及其信徒。在神学中,宗教多元性在神学伦理学和教义神学两个视域中体现。在神学伦理学中,讨论的问题涉及宗教与政治的关系或宗教与公法的关系,也涉及宗教组织与国家的关系,宗教组织彼此之间的关系,或者宗教与公共空间之间的关系。具体的概念(如宗教自由、世俗化、国家的宗教中立或宗教组织的自治)在所有这些关系中都具有中心作用,并给予导向,其核心在于自由。
在第二个视域中,阿兰·雷斯1983年提出的排他主义-包容主义-多元主义模型是理解和定义宗教多元性的典范,在此基础上也诞生了许多变体,然而,此类包含普遍化倾向的模型难以解释全球化下宗教之间的复杂互动,因此有必要发展新的理论和方法。超越三分模式的一种路径是放弃发展一种全球宗教神学的单一模式的尝试,通过实践“一种具有视角和视野的主题性思维”,从具体社会语境出发,分析宗教群体如何通过神学策略应对多元化。
鉴于宗教是由人实践的,格罗斯汉斯由此转向本次讲演主题——人性和宗教多元性的关系,并借助施莱尔马赫的宗教人类学来提供一种人类学视角下的宗教多样性分析。施莱尔马赫认为,那些把宗教排除在自己生活之外的受教育者在对世界和自己的认识上存在自我局限,与这些蔑视宗教者的意见相反,宗教是人类本质的一部分。而揭示宗教的本质意味着在宗教多元性中展开,大多数宗教“建立在宗教的本质上”。施莱尔马赫将宗教定义为“感知和感觉”,并进一步将之定义为人的一种独立的官能。
施莱尔马赫基于莱布尼茨的一元论模型来解释宗教多元性的生成逻辑:每个人对宇宙的感知不同,因此宗教全然是个人(但非私有)的东西,宗教整体也只能通过无限多样的形式呈现。当某种个体性宇宙观凭自由意志被确立为整个宗教的核心,宗教内所有元素都与此核心相联结时,便诞生了特定的历史宗教。宗教内部共同体的形成及宗教本身的创生,亦可溯源于宗教情感的交流需求,个体需通过符号(仪式、神话等)将体验外化,形成“可见的教会”,宗教作为人最内在的维度,必然外化为公共性的共同体形态。
对宗教情感的分析表明,人们在宗教中依赖于唤起宗教情感的对象——宇宙和其中的世界精神。然而,在宗教中,人不仅是由他人决定的,而且是完全由自己决定的。因为施莱尔马赫把感情特别理解为宗教中的“自我活动”。它们不仅是个体的、由个体自我产生的(虽然是由外部引起的),而且在赋予人普遍性的意义上也是自我行为的。人类心中对宗教的自我体验及其所有丰富的感情,是宗教人士在所有宗教多元性中的共同参照点。这为有意义的宗教间理解提供了基础。
格罗申斯最后总结道,尽管其本质主义倾向导致忽视了社会权力对宗教形态的塑造,但施莱尔马赫以一种高度建设性的方式,将人的本性与宗教主题结合起来,并且恰当地展示了主题性思维的优势。

郝长墀教授评议
在评议环节,郝长墀总结了讲座内容并充分肯定了讲演内容的丰富性,并提出两个问题:(1)什么使一种信仰成为宗教?施莱尔马赫将宗教本质归结为个体与宇宙相互作用的瞬间体验,认为这种不可言说的神圣感受根植于人性。但其理论存在三重困境:首先短暂体验需通过符号重构会陷入解释学循环,其次强调人性自发的宗教性可能使神圣沦为需求投射的偶像,最后从佛教的角度来看,佛性、宗教性并没有人类学基础,正是佛性自身使人类或蚊子具有佛性。这不由使人追问:若真理仅存于个体体验,那么该如何解释建制宗教的历史权威?(2)如何基于施莱尔马赫的理论对历史宗教的形成给出合理说明?施莱尔马赫将宗教本质归结为个体与宇宙的“神秘性合一”,认为宗教体验具有绝对个体性,但这不仅会滑向相对主义,而且个体一旦想要向他者表达或再现个人的感受和体验,个体体验就面临被中介化、外在化以至于与神秘般的体验相疏离的风险;另外,将历史宗教归因于创始人核心信仰的自由选择与道教、佛教等宗教的创立历史也是不一致的。
格罗申斯表示其中一些问题的答案之于他是无法给出的,需要强调的是,施莱尔马赫提供的不是一种关于宗教的历史解释,其目的在于恢复人们对舒适生活之外的本质的关注,重点在于通过随机被宇宙触及而获得对于整体的感受,尽管每个人关于这种体验的描述不尽相同,甚至许多人都不曾有过这样的宗教体验。
陈波就“来自其他文化、宗教的移民在保持原有生活方式的情况下如何融入当下生活环境”进行了提问。格罗申斯结合德国现状简要分析了这一问题,表示其思考重点不在于强调差异或趋同,而在于探索多元文化共存的沟通可能性基础,即我们必须追问:应在哪些层面建立对话基础?又应在哪些层面保持其原生状态的不可通约性?还有几位学生提出问题,格罗申斯做了简要回答。
(编辑:邓莉萍 审稿:刘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