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度当代英美道德哲学前沿工作坊召开
点击次数: 更新时间:2020-12-11
本网讯(通讯员 李忠泽)2020年12月3日至4日,由武汉大学哲学学院主办的“当代英美道德哲学前沿工作坊”在振华楼哲学学院B214会议室召开。此次工作坊共分为两场举行,来自厦门大学、武汉大学、华中科技大学、湖北大学等高校的十余位学者参加了本次会议。
12月3日下午三点半,报告正式开始。本场报告由武汉大学哲学学院伦理学与政治哲学教研室陈江进教授主持。厦门大学刘晓飞副教授进行了题为“知识与事实性条件——关于汉语中‘知道’一词使用的实验哲学研究”主旨报告,华中科技大学的徐敏、汤志恒,武汉大学哲学学院的潘磊、冯书怡等数位老师和同学对主旨报告做了评论和讨论。

刘晓飞老师指出,对于“有据的为真的信念(justified true belief)”这一知识的经典定义来说,有很多关于信念、有据的研究,而这次报告主要针对于“为真”这一条件进行讨论。这个研究起源于自己在阅读关于知识的相关文献时,发觉在中文语境下,称“知道某一命题”并不需要这个命题为真。
刘老师讨论了英语中对为真条件的争议。Hazlett认为“知道”这一谓词是事实性的(factive),即“S知道p”仅当p为真。然而,Hazlett的一个例子似乎挑战了这一命题:“每个人都知道压力导致了胃溃疡,直到两个医生在上世纪八十年代证明细菌感染才是导致胃溃疡的原因”。

对于Hazlett,Buckwalter则提出了另一个批评,即“主角投射(protagonist projection)”。主角投射指,说话者使用“知道”一词时,说话者实际上是站在故事主角的视角来判断是否适合使用“知道”这一谓词的。以上述的命题为例,当某个人说“每个人都知道...”时,这个人是站在八十年代之前人们的视角是使用“知道”这一谓词,进而“每个人都知道...”这一判断是可以接受的。
接着,Buckwalter设计了相关实验,实验结果表明人们认为“每个人都知道...”这个命题表达的是“每个人都认为他们知道...”而非“每个人都真的知道...”。进而,Buckwalter认为“如果被试接受知识是事实性的,那么被试会更可能接受主角投射;如果被试不接受知识是事实性的,那么被试则不会接受主角投射”。
刘老师认为,Buckwalter的论述中的一个前提存在着歧义,并区分了语言学事实(LF: linguistic factivity)与哲学事实(PL: philosophical factivity)。前者指仅当说话者相信p为真,“S知道p”才是正确的用法;后者指仅当p客观为真,“S知道p”才是正确的用法。这个区分使得Buckwalter认为的“如果被试不接受‘知道p要求p为真’,那么被试就没有理由选投射性回答而不选非投射性回答”。这是因为即便被试不接受PF,LF仍然可以提供理由使被试拒绝非投射性回答。目前我们提出了PF与LF的区分,而尚未证明被试的选择是因为接受LF还是PF导致的。要证伪PF,需要S知道p为真,而P不客观为真。而主角投射的存在使得我们无法确定“S知道p”是否为真,进而,证伪PF的反例中还要满足“被试没有理由认为S相信p为真”这一条件。
刘老师通过三种方法构造了符合上述三个条件的反例并制作了问卷。这三种方法分别是:构造势均力敌的争议(智慧的外星生物对基本数学命题的争议)、构造来自权威人士的理由(天体物理学家对宇宙膨胀的质疑)、构造众所周知的怀疑(伦理学教授称“我们知道虐待婴儿在道德上是错误的”、对未来事件的预测)。

通过对500多位中文使用者的调查表明,在数学和道德命题上,被试普遍认为当事人“知道xx命题”,在天文和未来事件两个命题上,被试认为当事人“知道xx命题”的样本数量更少;在选择当事人“知道xx命题”的问卷中,被试否定PF的数量比否定LF的数量多得多;其中,对于未来事件,将近70%的被试否定了PF,而只有不到30%的被试否定了LF。
据此,刘老师得出结论:我们有理由相信在日常汉语使用中,“知道”的哲学的事实性条件没有被广泛遵循。
在评论环节中,华中科技大学徐敏老师认为实验哲学基于这样一个前提:“如果直觉是正确的,那么...”。而问题的关键则在于这个前提的前件是否为真,并对报告中是否面临循环论证、实验哲学的有效性、知识能否被定义等问题进行了评论。刘晓飞老师对此做出了回应:实验哲学是可以做出许多贡献的,它价值之一就是可以揭示其他文化语境中对概念的不同理解、突破对于概念理解的局限性,而知识能否被定义本身是一个长期讨论的问题。

华中科技大学汤志恒老师认为问卷中可能涉及歧义的地方,可以通过进一步的调查,进而解决可能遭受的质疑;同时,也对问卷方法本身的合理性进行了质疑。汤老师认为普通人的观点是未经反思的,因此可能不具有有效性,如果这些观点是经过反思的,那么问卷将类似于一篇分析哲学的文章,此时实验哲学已然不存在。刘晓飞老师肯定了汤志恒老师的第一点评论,认为这是之后要进行的工作;关于对实验哲学的方法的质疑,刘老师认为实验哲学或许可以通过问卷的方式揭示另一种可能性,消除之前固有的偏见,因此实验哲学是有价值的。

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潘磊老师指出,知识的讨论本身带有形而上学的要求,人们追求的是真相,而不是意见。首先,刘晓飞老师对知识的讨论似乎只涉及语用的层面,而对语用的讨论并不会冲击对知识的形而上学的要求;其次,问卷中对于道德命题和涉及未来命题的设计似乎是不合适的,因为人们对这两类命题的确定性存在争议,例如人们可能认为这两类命题并不具备对于数学命题那样的确定性。因此用道德命题和涉及未来的命题进行攻击似乎是不公正的。同时,潘磊老师对PF与LF的关系、论文中的论证是否出于独立的理由进行了评论。刘晓飞老师首先对潘磊老师的一些观点进行了肯定,接着指出问卷只是为了进行经验性的调查,并非意在摧毁PF的合理性。而设计问卷的初衷以及问卷具有合理性的一个理论预设是:形而上学的规范大概要与实际中人们语用的规范相符。

武汉大学哲学学院冯书怡老师就问卷中天体物理学家的例子的合理性进行了评论。冯老师认为宇宙膨胀的例子似乎并不是一个合适的例子,或许用细胞、引力等更为常见的例子更能说明问题。刘晓飞老师回应道:问卷的设计不需要考虑例子是否可靠,重要的是要考虑是否能构造出反例;之所以不选择普遍接受的例子,是因为要避免“大家普遍接受p进而我相信p”的情况。

12月4日下午三点半举行第二场报告。武汉大学哲学学院伦理学与政治哲学教研室葛四友教授主持,厦门大学刘晓飞副教授做了题为“操控,责任与同一性”的主旨报告,华中科技大学的叶金州老师、湖北大学的陶文佳老师,武汉大学外籍教师Matthew Lutz副教授和Timothy Perrine特聘副研究员对主旨报告做了评论。
刘晓飞老师首先讨论了有关相容论的一些争论问题,对相容论内部的立场进行了区分,并就“强硬的(hard-line)”相容论者和“温和的(soft-line)”相容论者的立场分别进行了阐述。刘老师指出,其中一种回应被称为“其他存在者回应(another-agent reply)”:在日常情境下被因果决定和被他人操控的情境存在着显著的区别,这个区别是前者不存在操控的主体,而后者存在操控的主体。
然而,其他存在者回应面临着一个反例:这个反例与Pereboom的例子非常相似,差别仅在于主体不是被科学家,而是被一个机器操控。我们似乎认为,在这种情境下主体负有的道德责任应当与主体被他者操控负有的道德责任相同,而其他存在者回应并不能解释这一现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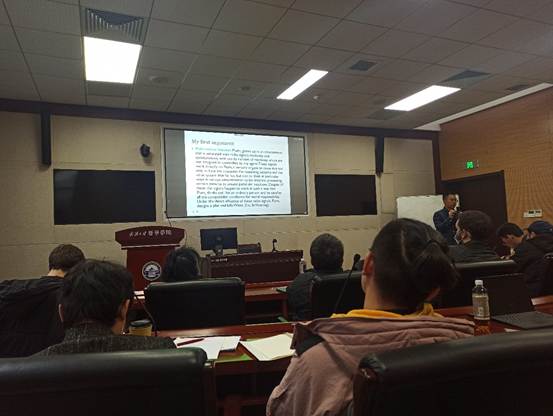
刘老师认为,被一个机器完全操控的例子对“其他存在者回应”并不构成一个真正的挑战。相反,这个例子为温和的相容论提供了采取“其他存在者回应”的理由。
刘老师提出了这样一种情境:这个情境与上述的情境都十分类似,唯一的区别在于行为主体的行为是被无数个机器,而不是被一个机器影响。刘老师指出,这个情境与现实的环境十分类似,而认为操控主体的机器数量的不同会导致道德责任的不同是荒谬的,因而在日常环境、被无数机器诱导的环境中和被单一机器诱导的环境中主体负有的道德责任应当是相同的,即在相容论者看来,行为主体不负有道德责任。因此,被一个机器完全操控的例子并没有对“其他存在者”回应提供一个真正的反例。
接着,刘老师考察了Mele的温和相容论立场:Mele认为道德责任要求自主性(autonomy)、真实(authenticity)的存在,而这使得获得相关支持态度(pro-attitude)的历史中不能存在强迫的因素。
刘老师认为Mele的理论面临着严重的问题:一方面,如果在被单一机器控制的情景下,主体的相关支持态度的获得是被强迫的,因为单一机器控制的情景与日常环境的道德责任相同,那么在日常环境下主体的行为也是强迫的,因此是不具有道德责任的,而这否定了相容论立场本身;另一方面,如果主体在被单一机器控制时产生的相关支持态度不是强迫的,那么我们可以将机器换成另一个实施操纵的主体,情境的其他因素保持不变,而这导致主体在被他者操控时仍然不是被强迫,因而仍然是负有道德责任的,而这是强硬的相容论,而不是温和的相容论。刘晓飞老师指出,对于任何一个温和的相容论者来说,如果他/她拒绝“其他存在者回应”,那么他/她都会面临这样的两难困境。而这使得温和的相容论不得不仔细考虑“其他存在者回应”的合理性以及对这个回应的辩护。如果情况果真如此,那么对于相容论者来说,决定道德责任的因素不仅是行为是如何导致的,还包括是什么导致了行为(例如是被机器决定还是被其他主体决定)。

在报告的第二部分,刘晓飞老师通过“白门楼”和“安德的游戏”两个例子 批评了试图通过操纵者的意图解释道德责任的理论。接着,刘老师尝试通过Strawson的反应性态度(reactive attitude,例如表扬、憎恨、责备等等)和意志的来源(origin of will)等概念建构一个更具说服力的理论(此处称之为意志来源理论)。最后,刘老师用意志来源理论对数个例子中的主体是否负有道德责任进行了说明。
在评论环节中,来自华中科技大学的叶金州老师首先对刘晓飞老师的理论进行了简要的梳理和总结,接着提出了几点疑问:首先,我们似乎不知道意志来源的形而上学上的地位。这是因为根据Strawson的理论,我们对意志的理解似乎来源于观察者的猜测和反思;其次,我们应该如何理解观察者也是一个问题。也就是说,观察者的情况也是不清楚的,例如,我们不知道观察者应该是某种机器、日常生活中的人或是其他东西。

刘晓飞老师首先对Strawson的理论的内容和初衷进行了澄清:Strawson认为之前我们误解了自由意志和道德责任,我们应该以反应性态度来理解自由意志与道德责任。接着刘老师指出:根据Strawson的理论,这里的讨论或许不存在意志的形而上学的问题。
来自湖北大学的陶文佳老师指出刘晓飞老师的讨论和观点十分有趣,接着提出了几点质疑:首先,刘老师的第一个论证似乎是有问题的,这是因为在第一个论证中似乎是用强硬派相容论的立场进行的论证;其次,在单一机器诱导的例子中,为什么将心理状态作为一个独立的因素是令人疑惑的;再次,有人认为强硬派相容论的立场似乎太过强硬与反直觉。然而,我们对直觉、道德本身的含义尚未产生共识,所以以太过强硬、反直觉为理由反对强硬派相容论似乎是不公正的;最后,即便机器没有意志,但人工智能却有拥有意志的可能性。

刘晓飞老师回应道:虽然报告中提及了Strawson的理论,但刘老师并非完全同意Strawson的理论,所以不会面临关于形而上学的质疑;至于人工智能,刘老师认为这是一个以后很好的研究方向,而这也涉及自己的著作《归责与规范:一种道德责任理论》的一些内容。
武汉大学哲学学院外籍教师Matthew Lutz总结道,刘晓飞老师是通过对意志来源的讨论试图指出被机器控制和被他人控制两种情景的区别,而刘老师对意志的来源的理解建立在对主因(primary cause)的理解之上。然而,Matt认为,刘老师对主因的分析似乎是有问题的。在白门楼的例子中,刘备在因果链条上的位置似乎先于曹操,而刘老师认为曹操,而不是刘备,应当对行为负责。那么刘老师必须解释在这个例子中,为什么曹操,而不是刘备是行为的主因。接着Matt指出,主因这个概念本身似乎是有问题的。事件的发生实际上是多个因素的结合导致的,并不存在某个可以被称为原因的东西。从实用的角度考虑,我们才会将某个因素称为原因。最后,Matt就刘老师提供的解决方案是否是温和的而非强硬的相容论进行了质疑。

刘晓飞老师认为,主因似乎的确是个不能让人满意的选项,而对相关问题的讨论正是他今后研究的方向。刘老师认为,我们或许可能通过对意向的生产(production of intention)、因果系统(causal system)等概念的讨论寻找出路。同时,刘老师认为自己提供的方案并不会导致强硬的相容论。
武汉大学哲学学院外籍教师Timothy Perrine以《尼各马可伦理学》为背景,梳理了Pereboom对相容论的批评,试图论证Strawson对自由意志的理解并不能为相容论提供令人满意的解释。亚里士多德认为自由意志与道德责任需要满足的两个条件是行为在主体的控制之下,并且主体对该行为具有知识。面对Pereboom的批评,相容论试图通过存在其他主体控制行为者来回应Pereboom的批评。在这种回应下,如果主体是被一个或多个机器控制,那么这个主体仍然是对行为负责的;而如果主体是被另一个主体控制的,那么这个主体并不对这个行为负责。Tim认为,Strawson的理论并不能为两种情景道德责任的不同提供满意的解释。

Strawson强调他人对行为主体的反应性态度和责任之间具有重要的关系。主体对某个行为A负责,当且仅当对其他人对这因主体的A行为对主体采取反应性态度是合适的。然而,Tim对这个命题是存疑的:他人因为主体的A行为而采取反应性态度是合适的,当且仅当A反映了主体的意志。这是因为这个命题可能违背了亚里士多德提出的道德责任的第一个条件,即行为在主体的控制之下。当主体的意志被外界因素控制时,主体并不对意志负责,行为A也并不在主体的控制之下,也不反映主体的意志,即便这个意志的确是主体表现出的意志。而在之前讨论的那几个例子中,我们会认为主体的行为都表达了意志,但在这些例子中并不存在自愿的意志。因此,按照亚里士多德的理论,在被人和机器控制的例子中,行为主体都对行为不负责,而这是与讨论Strawson理论的初衷相违背的。
有的人或许说,在被多个机器控制的例子中,主体的意志是自愿的,且主体行动的环境与真实世界中的情况极其相似。然而,Tim认为这是不正确的。Tim认为那个例子中的情境从未存在,被那种环境控制的主体似乎并不是日常生活的人。在现实生活中,我们被各种波(wave)影响,但这样波并未对我们的行为产生影响;我们也并非用认知能力去感受无线电波。刘晓飞老师感谢了Tim的评论,并回应道:在现实世界中,尽管有很多外在刺激不会影响我们的认知,但我们的认知的确会受到很多外在因素的影响,例如教育、颜色等等;而且,刘晓飞老师关注的重点在于责任来源的转移、身份的转移,而不是被控制的意志是否要负责,等等。
经过两天的报告,本期“当代英美道德哲学前沿工作坊”在激烈的掌声中圆满结束。
(编辑:邓莉萍 审稿:严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