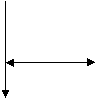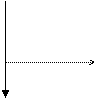《比较哲学与比较文化论丛》 第10辑目录
点击次数: 更新时间:2018-06-01
编 委 会
主 编:吴根友
副主编:储昭华
编 委:
校外编委(以姓氏音序为序):
安靖如 白彤东 贝淡宁 陈立新 邓晓芒
黄 勇 牟 博 倪培民 张祥龙
校内编委(以姓氏音序为序):
程 炼 储昭华 丁四新 郭齐勇 郝长墀
何 萍 李维武 李佃来 彭富春 桑靖宇
苏德超 吴根友 徐水生 翟志宏 钟 年
朱志方 邹元江
吴根友
就比较哲学的基本任务而言是求同存异,甚至可以更进一步地说,是“求异中之同,求同中之异”。但究竟如何才能恰当地理解“求同”与“存异”本身的涵义呢?这是一个需要进一步深思的问题。
一般而言,哲学的根本任务是追求智慧,具体而言,她是求真、向善、致美。围绕这一个根本目标而言,所谓“求同”,即是求得“真是”,而这一“真是”,既可以是认识论领域的真理,亦可以是价值论领域的真好(包括真善与真美两部分内容。好,读第四声,后同)。就认识论领域的真理而言,就是追求在某些问题上大体一致的正确认识,从而为人类的行为提供一些基本的共识,形成人类生活中的一些基本的“常识”。而就价值论领域而言,就是在关于“真好”的问题上大致达成某些共识,或对某些基本的正面价值形成认同感,如今日所谓的伦理上的“金规则”,美的形式上的黄金分割率等。实际上,在认识论领域,“求同”所要达到的“共识”,要比价值论领域所要达到的“共好”,相对而言要容易些。在价值论领域里,由于历史、宗教、风俗所形成的关于何者为好的评判,在不同的民族之间,有相当大的差异。此一领域里,希望通过比较哲学的研究而达成对某些对象的“共好”判断,是相当困难的。在此领域,比较哲学与其要殷殷切切地达成某种“共好”,不如听之任之,以宽容的态度对待各好其好的行为与观念上的差异。换句话说,在此价值领域,以宽容的态度“存异”可能要优于不切实际、急于求成的“求同”。这是我们对“求同存异”原则的第一层思考。
从哲学史研究的学术层面看,“求同”之“同”,是寻找完全一样的思想或一样的观念,还是寻找大致相似的思想,或是说一种基本相同的思想原则,这是两种不太一样的“同”。就中西哲学的一些根本性的思维方式而言,古典哲学都拥有大致相同的思维方式,即寻找世界的开端或形成世界的根本因素。但古希腊哲学家给出的具体答案,与中国哲学、印度哲学是极不相同的,而在中国哲学、印度哲学、古希腊哲学内部,不同的哲学流派给出的答案也是不同。由此,我们在从事比较哲学研究的过程中,就会遇到一个十分尴尬的问题,即我们无法以地域或国别、民族的名义来从事所谓的国别的、地域的、或民族的哲学比较,如中国哲学与印度哲学的比较,而只能从事具体的哲学家或哲学流派之间的比较。而这种极端个别化、差异化的哲学流派、甚至是个别哲学家之间的比较,就会让我们的比较哲学工作陷入牛与马比、鸡对鸭讲的局面。哲学思想的领域里,所谓的“存异”之“异”,根本就不是“求同”过后剩下来的差异,而是天然的以“异”的方式存在着。这样一来,“求同”就成为人类在个体差别的精神世界里寻找某种“类同”,而不是本质上的“质同”的思想分类活动了。这种思想的分类活动能否产生所谓的“知识”,在此我持一种怀疑的态度。
就“类同”而言,经验主义可以说是哲学思考之一类。这一类的哲学家或哲学思想原则,往往通过对经验现象的研究,寻找表象差异背后的相同属性。或者是从事物的表象出发,寻找事物之中的内在秩序或法则。举例而言,中国传统哲学中以自然之气为世界根本要素的思想家,大体上都属于经验主义一类的思想家,他们或者将气的有规则的变化称之为“道”,或者将气的有秩序、有法则的存在方式称之为“理”。而中西哲学史上,一些将大自然看作是由气构成的,甚至将人的肉身、精神性的心智活动,也看作是气的运动的结果的哲学家,在自然哲学层面都可以视之为经验主义一类的哲学家。作为对经验主义一类哲学思想的发展,马克思的唯物主义的哲学亦可以纳入经验主义的思想类型之中。所不同的是,马克思的唯物主义不只是在自然观上坚持唯物主义,在历史观方面也坚持唯物主义。而且,马克思的唯物主义不是机械的唯物主义,而是辩证的唯物主义,即在承认物质性的力量是基础的同时,也承认人的精神力量——无论是个人的,还是人类的精神力量有一种反作用力。因此,作为经验主义类型的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在当代的中国就与一般的经验主义类型的哲学家区别开来了,而单独成为一种类型的哲学思想。
与经验主义相反的是观念主义类型的哲学家或哲学思想原则,这在西方哲学传统里是从柏拉图开始的,而到今天为止都还以各种变相的方式展示这种哲学类型的魅力。在柏拉图看来,任何具体的美的东西都会消失的,而只有美的理念本身永远是美的。柏拉图的这一思想,后来演化成种种形式的观念实在论,亦即当代中国哲学称之为唯心主义一系的哲学类型。这一类型的哲学家,在中国古代哲学中,似乎只有程朱理学中用以表述最高存在的理或天理的观念与之相似,先秦的名学家似乎还不能说是柏拉图一类的观念论者,至多在名学的思想体系中,有观念实在的思想因素,如“鸡三足”“白马非马”之类的命题中包含了一种观念实在的思想因素。但先秦名学家似乎并不承认任何指物之名比任何具体的事物本身更真实。
“质同”的哲学思想家是存在的,但作为“质同”的哲学在纯思想的领域里是没有多少意义的,因为,如果一个哲学家在本质上与另一个哲学家在思想上是相同的,那么这个哲学家就失去了作为原创性哲学家的资格,而只能称之为某一个哲学家思想的传播者或学习者。由一些“质同”的哲学家构成的哲学派别,在思想史上所具有的意义只能形成某种社会思潮,或将思想变成一种社会性的文化心理,对于思想本身而言,是缺乏促进意义的。“质同”的现象应该只能存在于自然界,人的思想、心灵、性格,在本质上是不同的,而只是相似的,而且主要是在不同的侧面、层面上由众多的“类同”而形成某种程度不同的相似性。哲学思想的价值,其天然的性质是追求差异性。在一个国别史的时代里,世界上可能出现了某些“类同”的哲学家,但似乎没有“质同”的哲学家,所谓的“欧洲孔子”,“中国的苏格拉底”等一类的比喻性说法,只是比较哲学为了化陌生为熟悉而从事的哲学宣传的修辞而已。
就比较哲学史研究的学术目标而言,寻找某种“类同”可能是我们的主要目标,因为通过“类同”的分类把握,可以更好地握多样性的哲学思想,从而简化我们对于思想世界或曰观念世界的认识,从而做到以简驭繁。如果说在认识论的领域里因分类而产生知识,在比较哲学的研究领域,因分类而可以相对简明扼要地把握如同万花筒一样的思想世界。在“以类观之”的同时,我们切不可将哲学思想之同当作是一自然的现象,要深切地关注这种“类同”背后的真实之“异”,而这种不可类化之异,不应当等闲视之,更不应该等闲弃之,而恰恰应该以一种尊敬与敬畏之心视之、待之。因为,这种不可类化的“思想之异”永恒地成为人类思想领域中的“陌生他者”,而这种“陌生他者”可以不断地促使我们去思考、去思想。而人类价值领域的“异好”,更不应当以“异端”的态度来对待它们。只要不违背人类的一些基本的底线共识,如反人类,贱视人的生命,我们就应当以宽容的态度来对待这些“异好”,这对于我们当中的有些人来说是难受的,甚至是痛苦的。但对于那些不违背人类基本价值的“异好”,我们不用宽容的态度对待它们,还能有什么更恰当的态度呢?
是为序。
目 录
序
利玛窦研究专题
省思利玛窦来华启动的相互外推策略
----以早期耶稣会士与华人教友论述为例 …………………………………………………沈清松
Matteo Ricci and His Method of Cultural Accommodation ………………Hu Yeping
略谈西方对“理”的三种解释----从利玛窦、莱布尼茨到李约瑟 ………………桑靖宇 程 悦
利玛窦的抉择 …………………………………………………………………………………………方 永
文化“丝绸之路”上的利玛窦 …………………………………………………………………王利民
利玛窦的本土化战略与祖上祭祀的现代意义 …………………………………………… 严震泽
比较方法论止观与坐忘与居敬——三教的身心技法…………………………………(日)三浦国雄
“世界历史”与比较哲学的思想起点----《历史的起源与目标》读后 ………… 吴根友
佛耶比较与对话:个案研究
晚明天(主教)佛对话文存----《辨学遗牍》 …………………………………………… 麻天祥 李彤 韩燕丽
鸠摩罗什与利玛窦的本土化传教策略比较 ……………………………………………………黄 超
学术新人
涩泽荣一的《论语》观研究……………………………………………………………………… 宗辰欣
Contents
Preface
Researches on Matteo Ricci
Reflection on Matteo Ricci's Mutual Strangification Strategy in China:
Taking Early Jesuits and Chinese Disciples as examples ……………………… Vincent Shen
Matteo Ricci and His Method of Cultural Accommodation……………………… Hu Yeping
A Discussion on the Three Different Interpretations of Li in the West:
From Matteo Ricci, Leibniz to Joseph Needham…………………………… Sang Jingyu Cheng Yue
Matteo Ricci’s Choices………………………………………………………………………Fang Yong
Matteo Ricci on the Cultural “Silk Road”……………………………………………Wang Limin
Matteo Ricci's Localization Strategy and the Modern Significance of
Ancestor Worship System ………………………………………………………………………Yan Zhenze
Methodology of Comparative Philosophy
Zhiguan (Meditation and Insight), Zuowang (Sitting and Forgetting) and Jujing (Reverence and Concentration): Methods of Disciplines for Body and Mind in Buddhism, Daoism and Confuicianism………………………………………………………………………………Kunio Miura
“World History” and the Beginning of Thoughts of Comparative Philosophy:A Review on Vom Ursprung und Ziel der Geschichte ………………………………………………Wu Genyou
Dialogue and Comparison between Christianity and Buddhism: Case Studies
Bianxue Yidu: A Book on the Dialogue between Catholicism and
Buddhism in Late-Ming Dynasty ……………………………………………Ma Tianxiang,Li Tong, Han Yanli
A Comparison between Matteo Ricci’s and Master Zhi-Zhe’s Ways of Confucianization
……………………………………………………………………………………………………Huang Chao
New Scholars
Eichi Shibukawa’s View of 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 Zong Chenxin
利玛窦研究专题
省思利瑪竇來華啟動的相互外推策略
──以早期耶穌會士與華人教友論述為例
沈清松*
内容提要:我們正生活在一個全球性的多元文化時代,各文化正在不斷跨越國界並與其他文明互動,我將外推做為全球化時代的文化互動策略,並將文明交談視為相互外推,不同的文化傳統應透過相互外推,以便達到相互豐富。在这样一种思路下,我將集中在近代性興起的時候,從其中抽繹出一個仍適用於今日的互動典範,那是由利瑪竇來華所建立的外推策略,透過友誼交談達致中西文化的相互豐富。
关键字:文化互動 語言外推 實踐外推 本體外推
一、引言:省思的線索──全球化與跨文化互動
由於全球化歷程加深,各文化不斷跨越國界並與其他文明互動。不同文化、哲學與宗教傳統的相互比較、詮釋與對話,須擺脫排他性的國族主義,或東方主義、學術殖民的觀點,重新安置在各文化傳統和政治社會團體在全球化歷程中向外延伸並與多元他者相遇、互動的脈絡中來進行。
然而,全球化是經歷整個複雜的歷史過程,才走到今天的地步。例如,在一次與我同台發表論文時,德國哲學家阿沛爾(Karl-Otto Apel)主張古希臘時期亞歷山大進入印度,是第一次全球化。到了中世紀,蒙古人跨越歐亞進行的軍事與商業行動,也是全球化歷史階段之一。許多學者,如魏澤福(Jack Weatherford)認為:中世紀時蒙古人進行了商業的全球化。到了近代,近代西方帝國主義擴張與殖民運動也是其中的一個過程。我今天將集中處理的,正是這個時期。我想在其中抽繹出符合今日全球化所需的友誼平等精神,而非近代性的殖民宰制精神。
就今天而言,我們正生活在一個全球性的多元文化時代。目前世局的任何重要議題,無論是經濟、政治、疾病防治、犯罪防治、移民、安全、環保等等,都不是在一個國家內部,用一套辦法就能解決的。相反的,沒有一項議題不需要多國的參予,多管齊下,這就涉及不同觀念、文化、作法的協調與合作。本人把「全球化」定義為「一個跨越界域的歷史進程,在此過程中,人的欲望、內在關聯性與可普性在整個地球上實現出來,並在現今與不久的將來體現為擴張至全世界的市場、跨國際的政治秩序和文化的全球在地化(glocalism)。」[①]
總之,文化互動應建立在「相互豐富」的原則上,沒有任何文化可以獨斷獨行。思想、哲學與宗教皆起自文化,也因而不同的文化脈絡會有不同的思想、哲學與宗教。不同的文化傳統應透過相互外推,以便達到相互豐富。我將集中在近代性興起的時候,從其中抽繹出一個仍適用於今日的互動典範,那是由利瑪竇來華所建立的外推策略,透過友誼交談達致中西文化的相互豐富。
二、文明交談的策略;外推與相互外推
(一)外推的意義
我提出外推做為全球化時代的文化互動策略,並將文明交談視為相互外推「外推」(strangification)原出自儒家的「推」概念,如孔子說「推己及人」;在《禮記‧孔子閑居》中子夏云「善推其所有」;孟子說,「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無以保妻子。」此外,我也吸納了瓦爾納(Fritz Wallner)所提出的strangification (Verfremdung)做為科際整合研究的認識論策略,由我加以修正,並將之從科際整合的知識論策略,擴展到文化交流和宗教交談的領域,使其成為跨文化哲學的策略。我所謂的「外推」,意指一種走出自我封閉,走向多元他者的行動,從自己熟悉的圈子走向陌生的外人,從一種文化脈絡走向另一種文化脈絡。
(二)外推三層面:語言外推、實踐外推、本體外推
外推策略依序可以分為三個步驟。第一步是要進行「語言的外推」,就是把自己文化傳統中的論述或語言翻譯成其它文化傳統的論述或語言,或其它傳統所能夠了解的語言或論述,看它是否能藉此獲得理解或因此反而變得荒謬。如果可理解,這代表此一論述有更大的可普化性;如果是後者,則必須對這傳統進行反省和自我批判,沒有必要採取自衛或更激進的護教。當然,這其中總會有一些不能翻譯的殘餘或意義的硬核,但其中可共同分享的可理解性便足以證明它自身的可普化性。如果只在自己的傳統中誇耀自家文化,至多只證明了它自身的局限性。
第二步,是「實踐的外推。藉此我們可以把某一種文化傳統中的理念或價值或表達方式,從其原先的實踐組織中抽出,移入到另一組織脈絡中,看它在新脈絡中是否仍然可行,或是不適應新脈絡而變得無效。如果它仍然能起作用,這就意味著它在實踐上有更高的可普化性。否則就應該進行自我反省和批判。
第三步,是「本體的外推」。藉此我們從一個微世界、文化世界或宗教世界出發,經由對於實在本身的直接接觸或經由終極真實的開顯的迂迴,進入到另一個微世界、文化世界、宗教世界。尤其當人們進行宗教際的對話時,這一階段的外推就顯得特別重要。如果對話者本身沒有參與終極真實的體驗,宗教交談往往會流於膚淺表面。我們對於終極真實的體驗,如果確實是終極的,就該具有可普化性和可分享性,否則若只自我封閉地一味堅持自己的真理唯一,這至多只能是宗教排他主義的一個藉口而已。
(三)「文明交談」做為「相互外推」
文明之間的交談應該建立在相互外推的基礎上。詳言之,在A群體和B群體的交談中,在語言外推的層面上,A應該把他主張的命題或理念、價值、信仰系統轉換成B的語言或對於B來說能夠理解的語言。同時,B也應把自己主張的命題或理念、價值、信仰系統用A的語言表達或轉化成A能理解的語言。在實踐的外推層面,A應該把自己主張的命題、設定的真理、文化表達形式、價值、宗教信仰等,從自己的社會、組織、實踐脈絡中抽出,將它重新放置於B的社會、組織、實踐脈絡中。同時,B也應該把自己的主張、設定的真理、文化表達形式、價值、宗教信仰等,從自己的社會、組織、實踐的脈絡中抽出,並將它重置於A的社會、組織、實踐脈絡中。在本體外推的層面,A應致力於經由實在本身的迂迴,如對人、對某一社會群體、對自然或終極真實的親身體驗,進入B的微世界、文化世界或宗教世界。同時,B也應該努力經由實在本身或終極真實的迂迴,進入A的微世界、文化世界或宗教世界。以上是簡述如何透過相互外推以達至相互豐富。
三、初期來華耶穌會士的語言外推:中西互譯
(一)中西互譯的先鋒
利瑪竇(Matteo Ricci, 1552-1610)和耶穌會早期來華的會士們,了解到為了平等交流,應該把彼此最好的經典,拿出來翻譯,以促成深刻的相互了解,所以他們在這方面做了語言外推的工作。利瑪竇與早期來華耶穌會士帶到中國的,有西方的科學、技術、倫理道德、藝術、文學、宗教…等等著作,但他們也清楚認識到其中必須有理論基礎。也因此,他們有系統地譯介了亞里斯多德(Aristotle, 384 BC – 322 BC)。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第一位被系統地引進中國的西方思想家,正是亞里斯多德;他們也將中國經典譯介到西歐,藉以「習取」中國人的榜樣與論述,而第一位被譯介到歐洲的中國哲人是孔子,他們並把《四書》、《易經》等譯介至歐洲。可以說,當時擔任中、西互譯的接引者,是這些耶穌會士。
(二)文明交談的平等模式:友誼
利瑪竇的第一本著作是《交友論》(De Amicitia),其中引述許多西方作者,如亞里斯多德(Aristotle, 384 BC – 322 BC)、普魯塔克(Plutark, ca. 46-120)、塞內卡(Seneca, ca. 4 BC – AD 65)、西塞羅(Cicero, 106-43 BC)、奧古斯丁(Augustinus, 354-430)、安波羅修(Sanctus Ambrosius, ca. 340-397)等人對於朋友的說法,例如說「朋友宛如自我的另外一半」。這其中的思想,是朋友以友情和平等友善相待;又說,「交友之旨無他,在彼善長於我,則我效習之;我善長於彼,則我教化之。是學而即教,教而即學,兩者互資矣。」[②]利瑪竇這種平等友善互資論,頗接近我所提倡的「相互豐富」的主張。
這一平等而友善相待的想法含蘊著一個根本的典範轉移。原先由近代性產生的帝國宰制對其殖民地而言是不平等的,但現在利瑪竇由於心靈的敏銳、道德的操守和宗教的熱忱,他要從平等而友善的角度,來與中國文化交往,而不是從帝國主義者對待南亞各國那樣文明對野蠻的暴力宰制。這是在互動模式上的基本改變,在今天仍可以有重要的啟發。
其實,《交友論》是在當時中國社會風氣啟發之下撰寫的。利瑪竇在序言中憶及,湖南建安王曾在宴會中移席而來,握利瑪竇的手,問說:你們西方人對友誼有何看法?這一友誼的邀請,促使他把手邊所攜西方人書中對於友誼的論述,加上他的想法,編成了《交友論》。
(三)亞里斯多德為第一個系統譯成華語的哲學家及選擇亞里斯多德的理由
西譯為中,是西學東漸的一個重要因素。把西方經典翻譯為中文,也有中國士人的協助,例如徐光啟、李之藻、楊廷筠等,這三位被稱為早期天主教在華的三大支柱。亞里斯多德是他們第一個系統譯成華語的哲學家。在引介亞里斯多德生平時,他們都會選擇一些中國士人會感動的故事。例如在介紹亞里斯多德時,說他是帝王師,是亞歷山大大帝(Alexander the Great, 356-323BC)的老師,而且亞歷山大大帝曾親口說:「我為天下主,不足為榮。惟一得亞理斯多而師之,以是為榮耳。」[③]在一篇改寫自亞里斯多德〈論睡眠〉(De Somnia)的〈睡答〉中[④],說亞里斯多德睡覺時,手持一顆銅球,下面放一個銅鑼;當他睡著時,手一鬆,銅球掉落到銅鑼上,敲出鑼響,於是就醒來,繼續用功。可見,像亞里斯多德這樣一位大哲,也有像中國「髮懸樑,錐刺股」的精神,這一故事樹立了亞里斯多德勤奮用功的典範。
在《名理探》這本對於亞里斯多德《論範疇》(De Categoria)改寫的書中,寫到中世紀流傳的故事。亞里斯多德晚年退休到歐伯亞(Euboea)的查爾西斯(Charcis),在那裡,海潮每天漲、退七次,亞里斯多德總是想不通。他不斷思考,不顧疲倦,經年探索,到最後生病了。臨終前,亞里斯多德向造物者祈禱說:「萬物的第一根源,請你悲憫我,告訴我這項真理。」[⑤]《名理探》講這故事的意思,是人類單靠自己獲取的知識有限,為此必須從人學轉往天學。天學的主旨是認識創造萬物的造物者,祂知道宇宙ㄧ切奧秘。可見,亞里斯多德被視為人學與天學的中介,也因此亞里斯多德在中世紀被當作耶穌的先行者了。
除了前述理由,還有三項重要原因,說明為何耶穌會士選擇亞里斯多德:
第一,按照耶穌會的教育文獻(Monumenta paedagogica Societatis Jesu)記載,其中的教學規程(Rationem studiorum)十分強調亞里斯多德的學習。耶穌會在世界各地辦了許多學校,都遵循該會一定的教育方針與教育規程。我在上世紀九十年代曾經拜訪從菲律賓碧岳遷回台北輔仁大學的神學院圖書館,內藏耶穌會歷年的教育規程;我翻查過1586年度那一本,[⑥]其中計有63頁提到亞里斯多德的名字。可見,亞里斯多德在文藝復興時期因著「經典的再生」而受到重視的一斑。加上耶穌會在學術上承接了亞里斯多德與聖多瑪斯(St. Thomas Aquinas, 1225-1274)一貫相承的傳統,為此教學亞里斯多德體系比較合乎耶穌會的要求。在文藝復興時代,歐洲總共有四種亞里斯多德全集與評註本出版,其中最體系性的評註,是出自耶穌會在葡萄牙的柯英布拉學院(Coimbra College),由耶穌會學者們根據聖多瑪斯的思想,對亞里斯多德每本著作都做了詳細的評註,我讀到的該套叢書是在科隆(Koln)出版。耶穌會1586年的教育規程明確規定「對於亞里斯多德的教學必須按照以下順序:邏輯學、自然哲學、道德哲學、形上學。」[⑦]
實際上,中文本的翻譯或改寫基本上就是按照這一順序。例如,亞里斯多德的《論範疇》(Categoria),中譯本作《名理探》屬邏輯學著作。進一步,是物理學的著作,如亞里斯多德的《論天》(De Caelo),中譯為《寰有詮》;至於《論靈魂》(De Anima),中文本有《靈言蠡勺》,此外《性學觕述》的內容也多屬之。關於亞里斯多德的倫理學著作,尤其是《尼可馬古倫理學》(Ethica Nicomachea),雖未有全譯本或改寫本,不過,在明末之時,也有王豐肅(又名高一志)(Alfonso Vagnoni, 1566-1640)改寫的《修身西學》。至於亞里斯多德的《形上學》,或許太難了,要不然就是當時的修士還用不到,所以沒有譯出。
第二,是因為耶穌會士們認為亞里斯多德提供了一個從自然、到人、到天主,從理論,到實踐,到創作的一套有系統的學問,可以聯系理論與實踐、個人與群體,人學和天學。亞里斯多德哲學在理論上包含了物理學和形上學。物理學部分,包含了一般自然哲學(自然觀、時間、空間、運動…等),天文,氣象,博物(包含植物與動物),魂論等,主要關心的是運動變化與生命體,連睡眠這樣的生理現象都有所討論。耶穌會士特別凸顯其自然與天象的討論,以這方面的翻譯顯示他們了解自然,了解天體運行,可以處理大清朝廷在天文、曆法方面的問題與需求,然在自己不足的地方,例如曆法的修正,則曾推薦伽利略。當時刻卜勒(Johannes Kepler, 1571-1630)也認為只有伽利略可以幫中國修正曆法,因而也推薦伽利略。可惜,當時伽利略正忙著應付宗教裁判。反倒是刻卜勒回應了在華耶穌會士們所詢問的天文學問題,並對他們多所協助。[⑧]
此外,亞里斯多德的實踐哲學研究做人做事,倫理學處理個人的德行與幸福;政治學先講家庭經濟,再論政權的類型與城邦的幸福。至於創作事物,包含了對技術(techne)的討論,尤其是修辭學、詩學與戲劇。然而,亞里斯多德的第一哲學是形上學,討論存有者做為存有者(to on e on, being qua being),其主要的結構是「存有者‧實體‧神學」,在所有存有者中最核心的是實體,而所有實體中的最高實體、第一實體是神,神是「思想思想其自身」(noesis noeseos),是全面自覺的思想與最高的善。如此一來,亞里斯多德用人的理性從大自然一直探討到神,從人學一直到天學,被視為是最有系統的思想,可以取來和中國交流。
第三,耶穌會士需要一套進行教育與文化對談的經典材料,尤其是提供在修道院中培養修士所需教材,或者提供教友學者們的參考,透過這些經典了解天主教的宇宙觀與世界觀。例如當時的徐光啟、李之藻、楊廷筠,他們都因為讀了這些書,因而有一套論理依據來釐清己見或與別教論辯。可見,無論面對中國士人教友及其友人的需要,或培養中國修士的需要,都要有一套參考書籍。對此,亞里斯多德的著作是最適合的,也因此成為首譯上選。
舉例而言,《名理探》這本書其實是對亞里斯多德《論範疇》的改寫,其中討論十大範疇,包含實體(substance)與其他九種附性(accidents)。如果以桌子為實體,它的數量、性質、關係、習慣、時間,處所、方向、主動、被動等,這些都屬於附性,然而所有的附性皆必須依附於實體。推諸形上學,只有實體才能創造萬物,如果連實體都不是,只是附性,如何能創造萬物?換言之,討論實體和附性,有助於當時士人或修生根據邏輯推論進行區別與論辯。比方說,朱熹的「理」基本上是一種關係,而關係是屬於附性;既然只是附性,就不能創造萬物。利瑪竇因此認為,理不是造物者。根據這點,教育訓練與宗教論辯就有了一定的依據。用於宗教論辯,譬如佛教的「空」或道家的「無」,既然都不是實體,如何能創造萬物?也因此不是造物主。可見,亞里斯多德著作的譯介,對於那些與耶穌會友善的中國士人及修士們,為了論證的依據或教育訓練使用,編譯亞里斯多德是有必要的。
(四)艾儒略在《西學凡》中的陳述
至於進行中譯、西譯、中西互譯的主要理由,是前面說過的耶穌會的文化適應政策,以及友誼平等的交流原則。在此原則下有一基本觀念:要讓中、西雙方聖賢的思想彼此相遇。這在今天來講是意義深遠的。耶穌會士們想在經典的交流中促成雙方聖賢的對談,這一點可以從艾儒略(Giulio Aleni,1582-1649)在《西學凡》這本廣泛介紹西方學術概論的書中所說,得到印證。他說,「旅人九萬里遠來,願將以前諸論與同志繙以華言。試假十數年之功,當可次第譯出,更將英年美質之士,乘童心之未泯,即逐歲相因而習之。始之以不空疏之見,繼加循序遞進之功。洞徹本原,闡發自廣,…使東海西海群聖之學,一脈融通。」[⑨]
也就是說,耶穌會這些人冒險九萬里遠道而來,發願要把《西學凡》書中先前提到(主要是亞里斯多德)的重要經典,用十幾年的功夫,翻譯為華語,使得東、西方聖賢的學問可以相互融通。這樣的想法在今天依然非常有意義,亦即《西學凡》所言,「東海、西海群聖之學一脈融通」。在西賢的部分,主要是選擇了亞里斯多德,這也是早期來華耶穌會士的選擇。在西歐中世紀有一種論點,認為亞里斯多德是耶穌的先行者。對於耶穌會士們來說,亞里斯多德的哲學系統,可以從人學導往天學。
四、初期來華耶穌會士與華人教友
的道德論述與實踐外推
在實踐外推方面,涉及初期來華耶穌會士與華人教友在倫理道德方面的論述,其中包含人性論、德行論以及實踐論三方面。以下將逐一討論。首先將討論涉及人性論的艾儒略《性學觕述》、畢方濟《靈言釐勺》與夏大常的《性說》。
(一)從靈魂論到人性論
早期來華耶穌會士的著作,有兩本涉及亞里斯多德《靈魂論》,其一是艾儒略的《性學觕述》,於1623年出版,署名西極艾思及先生儒略「譯注」,可見有翻譯也有注疏[⑩]。第二本是《靈言蠡勺》,在1624年出版,是由畢方濟口述,李之藻達詞,則是減縮式的改寫。《性學觕述》並不止於亞里斯多德的《靈魂論》,且艾儒略知道中國重視人性論。所以艾儒略命名該書為《性學觕述》。不過,該書第七卷、第八卷這最後兩卷的頁眉書名印為《靈性觕述》,可見其本意是想要講論靈魂,因為「靈性」兩字是用來稱呼人的靈魂的[11]。
在此有兩層轉折須加以注意。第一,亞里斯多德的《靈魂論》本來在亞里斯多德哲學系統中是屬於自然哲學,他在《靈魂論》裡討論植物、動物和人的魂。對他而言,魂是「生命的形式」,在植物裡有生魂,藉之植物可以進行營養;動物有覺魂,藉之動物可以進行感覺運動;到了人的生命,則有靈魂,可以進行認知和意欲。這三魂都是生命的形式,而生命是屬於自然哲學的研究範圍,以人的靈魂為最高。但在聖多瑪斯註解亞里斯多德《靈魂論》時,將它由自然哲學轉為主要討論人的靈魂,以人學為中心,認為其他生魂、覺魂都是靈魂的預備,而且,由於更高形式的魂會綜攝其下各魂的功能,所以,靈魂也會統攝較低的營養、感覺等功能。所以,這第一個轉折是由自然哲學的靈魂論轉成人學的靈魂論。
第二個轉折是由多瑪斯人學的靈魂論,轉成了中國人習於討論的人性論。比較起來,《靈言蠡勺》是亞里斯多德《靈魂論》的改寫本,所以儘量保留「靈言」(De Anima)的原意。但是,到了《性學觕述》就有呼應中國哲學人性論的意思了。至於夏大常的《性說》,則說的就是人性論,但其實仍在討論人的靈魂。由聖多瑪斯人學的靈魂論到配合中國哲學論述的人性論,這是第二層轉折。
(二)艾儒略《性學觕述》、畢方濟《靈言釐勺》與夏大常《性說》
首先,艾儒略的《性學觕述》有三點值得注意。第一,這是一本用中文來教導亞里斯多德《靈魂論》的書,主要的根據是天主教的詮釋,不過它要比後來的《靈言蠡勺》更忠實於亞里斯多德,而且在哲學上的程度較高,意義較大。第二,艾儒略《性學觕述》的主旨,是為了向中國知識份子講論天主教有關靈魂的教義,以及靈魂與上帝的關係。第三,艾儒略的《性學觕述》,是想就亞里斯多德和多瑪斯及其他天主教哲學家對於人的精神能力的看法,來與中國思想和文化,尤其是其中的人性論,相互對話。
所以,雖說在《性學觕述》中充滿了士林哲學的語言和天主教思想,也頗願意與中國哲學對話,但艾儒略基本上還是非常忠實於亞里斯多德的《靈魂論》。該書可以說是在明清之際引入亞里斯多德《靈魂論》思想的著作中,最忠實於亞里斯多德的。艾儒略不但使用了亞里斯多德對「靈魂」的定義,而且詳細討論了靈魂的三個功能,譬如亞里斯多德《靈魂論》所論生長、運動、感覺,而在感覺這部份裡也討論了看、聽、覺、嗅和觸,以及對自我的感覺,乃至於人的更高級的能力:如理智與意志等。
在我看來,《性學觕述》是早期耶穌會士的中文論著中最富於哲學趣味與哲學論辯的一本重要著作,即使在今天仍然值得仔細閱讀與研究。歷來的中國哲學史家之所以加以忽略,要不是由於沒有機會讀到,或者由於帶著誤會去讀,甚至因為認定它只是傳教作品,因而忽視了艾儒略的哲學。其實,艾儒略被時人稱為「西來孔子」,不是沒有道理的。他的學問真好,且思想慎密。他在書中對生魂、覺魂和人的靈魂皆有完整的論述。關於靈魂,他立基於天主教立場,特別指出每個人的靈魂都是獨特的,可謂在傳統上不太重視個人的中國思想裡,給了個人的獨特性以一個靈魂論和神學的基礎,認為每個人之所以有獨特性,是因為每個人的魂都是天主所專給、獨一無二的。
艾儒略說,有人提出疑問:「孟子云:堯舜與人同。心之所同然者何也?禮也、義也。曰同。分明萬人一性,萬人一心,有何差別?」這個問題的預設是:所有人的本心應該是一樣的,是不是同一性,同一心?就像陸象山所說,前聖後聖都是同一個心。換言之,都是同一個靈魂?
「萬人一性,萬人一心」的主張有點類似阿拉伯哲學家亞維羅(Averroes, 1126-1198)和亞維森納(Avicenna, ca. 980-1037)的世界魂(world soul)的意味。其實,在我看來,艾儒略在此所針對的一心之說,更好說是受到佛教《大乘起信論》「一心」說的影響,認為在真如境界,唯有一心,沒有個體。如果個人認為自己有個體,那只是一種形而上的幻覺,就好像一滴水認為自己有個體,其實一滴水只有落入大海才有它真實的存在。在宋代儒學裡,尤其是陸象山所說的,我的心,我朋友之心,數千年前聖者之心,數千年後聖人之心,都是同一個心。心的實體是無限的,如果能完整發展你的心,你就會與天合而為一,同一個心。我想,佛教與陸象山所說的一心,才是艾儒略所針對的。
在此,艾儒略主張人的靈魂的獨特性,是天主特別為每一個人所造。此種對於靈魂獨特性的強調,是用以對抗這種天下一心或一魂的思想。艾儒略在中國的情況,不像聖多瑪斯當時議論的時空背景是在和阿拉伯思想家對話,現在艾儒略是在中國,面對的是宋明心學或佛教的一心思想,而不必多事批評阿拉伯哲學,其論述的時空完全不同。艾儒略批評一心,或所謂東聖、西聖、前聖、後聖都只是一心,堯舜其實並無差別,他所關切的是:如此將使個體性不顯。艾儒略的主要論證有二。第一,如果講一心或一個魂,完全沒辦法解釋人的個體性。在西方中世紀的時候有對個體(individum)的強調,而文藝復興時期有對個人(individual)的強調,利瑪竇、艾儒略等人將之帶進中國,這也是中國開始有突顯個體性或個人的想法。第二,艾儒略指出人的魂或心雖然可以與天主合而為一,但魂不是就天主。人雖可以開悟,達到天人合一,但「合一」並不就是「等同」或「為一」,天人合一不是說人與天主成為一個,不是「天人為一」。
其次,關於《靈言蠡勺》。方豪先生曾指出明末有四本亞里斯多德的翻譯本,《明理探》、《寰有詮》、《靈言蠡勺》,以及亞里斯多德的倫理學。一些研究者認為《靈言蠡勺》是對亞里斯多德《靈魂論》的翻譯。然而,我曾查對亞里斯多德原著,以及葡萄牙科音布拉學院(Coimbra College)對亞里斯多德《靈魂論》的評註。其實,它並不是翻譯,而是一本比較自由的改寫與節錄,是由畢方濟口授,由徐光啟達辭,讓它辭意通順且適合中國。我做過比較,亞里斯多德《靈魂論》的科音布拉學院評註本總共有五、六百頁,其中包含三個部份,第一個部份從14頁到47頁,第二部份從48頁到342頁,第三部份從343頁到559頁。然而《靈言蠡勺》全書只有141頁,而且只包含兩部份,第一個部份1頁到85頁,第二部份86頁到141頁。顯然這是個節錄本,怎麼可以說是翻譯呢?
《靈言蠡勺》一開始就訴諸《聖經》和天主教信仰,說「欲盡通亞尼瑪之妙,非二事不可,一者依天主經典所說。二者依我信德之光也。」[12]顯然,從起頭這就不忠實於亞里斯多德《靈魂論》,因為在古希臘的亞里斯多德,怎會講要依天主經典和信德之光呢。隨後文本也有忠實於亞里斯多德,只在改寫過程中加入天主教的信仰的。例如該書在引言中指出,《靈魂論》是靈魂之學,在哲學中為最有益、為最尊,的確是亞里斯多德說的。但是,隨後一轉就說是為了「認己」,轉成自我的認知,如此一來,就變成人學了。其實,自我的概念是文藝復興以降才有,是近代性產出的重要概念。但是,《靈言蠡勺》居然說是因為要認識自我而視靈魂論為哲學裡最有益處、最值得尊重的科學,甚至是所有科學的基本,因為一切事物都要歸諸於認識自我。其實,這是近代性的說法。
《靈言蠡勺》用「亞尼瑪」(anima)稱呼人的靈魂,其實在亞里斯多德那裡,該詞包含了生魂、覺魂和靈魂。畢方濟用的不是亞里斯多德意義的「魂」,表面上看起來好像是在翻譯亞里斯多德,但其實已經相當幅度改變了原義。他是用《聖經》和天主教信仰來理解靈魂。他在處理靈魂的主題時,常引述柏拉圖、聖奧古斯丁和聖伯爾納德(Bernard of Clairvaux, 1089-1153)[13],而不止於翻譯亞里斯多德靈魂論。《靈言蠡勺》和《性學觕述》一樣,特別要講清楚「魂不是氣」,這點是針對中國脈絡講的,而不是如聖多瑪斯是針對阿拉伯思想家。可見,畢方濟寫作時也是針對中國「一心」的理論和自然哲學理論來加以批評。根據以上的理由,我不贊成方豪先生所講《靈言蠡勺》是亞里斯多德《靈魂論》的翻譯。
其實,亞里斯多德也講開顯的真理,是由主動理智開顯事物的形式。主動理智有如光,當人的感覺對某一事物形成了可感覺的象(species sensibilis, sensible representations)之後,主動理智(agent intellect)便以其光明光照之,開顯出其可理解的象(species intelligibilis, intelligible representations),也就是事物的形式,並因而認識了該事物的本質。這一想法也被聖多瑪斯所繼承。《靈言蠡勺》,並沒有把亞里斯多德這些思想細節弄清楚。《靈言蠡勺》說,明悟,也就是我們今天所謂「理智」,區分為二:作明悟(也就是主動理智)和受明悟(也就是被動理智)。艾儒略說:「作明悟者,作萬像以助受明悟之功。受明悟者,遂加之光明,悟萬物而得其理。」[14]可見,《靈言蠡勺》把主動理智和被動理智的功能弄相反了:畢方濟弄錯了,認為主動理智(作明悟)作「萬像」(各種感覺之像)來輔助被動理智,是被動理智提供了光明,悟萬物而得其理,也就是得到可理解的像,又稱「靈像」。其實,這完全相反亞里斯多德和聖多瑪斯的想法,反而把主動理智的光明給抹殺了,變成被動理智在扮演。別忘了,主動理智才是光明的來源,主動理智的功能並不在於輔助被動理智(如畢方濟言「以助受明悟之功」),而且對於亞里斯多德,只有主動理智在人身體死亡以後還能不朽!《靈言蠡勺》對於兩者沒有掌握的很清楚,甚至有點顛倒混淆。
亞里斯多德《靈魂論》進入中國以後的兩本改寫本或節譯本大致分析如上。此外還有重要的一點:到底中國士人,尤其是早期的中國天主教徒,他們對於改寫過的亞里斯多德《靈魂論》如何接受,如何把它重新脈絡化。這也是我所謂「語言習取」(language appropriation)的一部分。習取他者的語言以改造自己原有的哲學傳統,往往是在互譯互動以後重新脈絡化思索的結果。這部份迄今也還未見討論。很幸運地,在2002年左右影印出版的《耶穌會羅馬檔案》裡,可以看到早期中國天主教徒的文獻。其中,夏大常是一位浸潤在儒學傳統的中國士人,領洗成為天主教徒,取聖名為瑪第亞。他有一些著作署名「夏瑪第亞」,可見是一位虔誠的天主教徒,甚至會用自己的受洗聖名署名。他所著的《性說》(主要是人性論)就是署名夏瑪第亞。可見,他是以天主教徒身份重新思考人性論的問題。
在《性說》裡,我們可以看到夏大常吸收了亞里斯多德、柏拉圖等的靈魂論,來改造傳統儒學最關心的性善或人性論的論述。然而,不同於畢方濟和艾儒略對於亞里斯多德和天主教靈魂論的改寫,《性說》是透過傳統中國人性論來習取亞里斯多德和天主教的靈魂論。換言之,如果說畢方濟的《靈言蠡勺》和艾儒略的《性學觕述》是一種「外推」的結果,《性說》則是一種「習取」的結果。為此,從《性說》一開始,夏大常就表明:凡認識人性者,必須理解宇宙三才之理;凡能盡性者,必須能夠重返與其造物者為一。所謂三才者,就是天之道、地之道以及人之道。天之道無形無象,地之道有具體形象,人之道居於兩者之間。所以人的靈魂是無形的實體,類似天之道;人的身體則是具體的形象,類似於地之道。也因此,在人之內綜合了天之道和地之道。人之所以類似於天之道,而不同於植物與動物者,無論是在天空飛、在地上走,在水中游的動物,主要都是來自其靈魂的美善。
由上述可見,人在三才之中,綜合了天、地二才;人的靈魂類似於天之無形無象,而人的身體則是類似於地之有形有象。如此論述,夏大常已經把人的靈魂等同於人性,所以他才能從《靈魂論》轉成《性說》,而且進一步指出(如同畢方濟和艾儒略),每個人的靈魂都是神最優美而獨一無二的賞賜。也因此夏大常所論的人不同於其它的宇宙萬物,因為人的靈魂都是由上天所賜予的,而其它萬物則都是來自四大,亦即地、水、火、風組合的結果。必須注意:在這裡夏大常使用的是「四大」,而不是中國傳統的「五行」。可見他已經採取了亞里斯多德的「四大說」,而有別於中國傳統所講的「五行說」。就這點而言,他是把人性的尊嚴建立在人天生的組成因素,以人的靈魂論證人的尊嚴,因為上帝把最優美的人性賜給人類,所以人類也應該為此而盡性,也就是全面展開他的人性或靈魂的善性,以便回報天主的恩寵。
從中國哲學的角度看夏大常是怎麼讀亞里斯多德的,其實,他是從中國人的道德善惡的價值中心角度來閱讀亞里斯多德。亞里斯多德的《靈魂論》本來只是自然哲學理論的一部分,但夏大常既然反對性惡論和善惡混,而致力於證成性善論,他已經是站立在中國傳統哲學裡面,以價值哲學中心的想法,去閱讀亞里斯多德的《靈魂論》。而且,在證成人性本善以後,他進一步表示,人性的善表現在人的三種能力上,也就是艾儒略和畢方濟所講的靈魂的能力,有理智、意志和記憶。他不同於亞里斯多德的記憶論,而是採納了柏拉圖和聖奧古斯丁所講的記憶說,視記憶為人性中很重要的能力之一。
中國士人在亞里斯多德理論內部做選擇的時候,並不注意其中有關知識論的一些人學依據。亞里斯多德討論主動理智、被動理智,講論人的主動理智與抽象能力如何能抽出某一事物的形式,交給被動理智,發表為該事物的本質概念,而該本質概念再用語言表達出來,則成為該事物的定義等。然而,這套體系性的哲學思考,並非中國士人所關心的。也因此夏大常會用價值論來讀亞里斯多德,同時在有關理智運作的分析方面,也不關心亞里斯多德所講的抽象論。即使是作為一位天主教友,他也沒有興趣去討論什麼是主動理智、什麼是被動理智。他的重點是在強調這三個能力(理智、意志和記憶)都是人可以藉之以達到天主作為他的人生嚮往的最高對象。
可見,艾儒略和畢方濟的外推工作,現在有了一個由華人習取的成果。在夏大常看來,人性的這三種能力都可以止於至善,達到天主作為最終極的目標。夏大常說:天主是至高的善,我的身體沒有接近天主的門道,然而我的意志可以接近天主,天主可以作為我意志的夥伴;我的眼睛不見天主,但我的理智可以看見天主,天主就是我理智的夥伴;我外在的身形無法接觸天主,然而我的記憶卻能接觸天主,並且以天主作為我的夥伴。[15]從這角度來看,人與天主的關係成為夏大常詮釋中國傳統「天人合一」的方式。所謂「天人合一」或「天人合德」,現在被受到亞里斯多德《靈魂論》影響下的天主教徒,理解為人和天主的關係,尤其是人有理智、意志與記憶三種能力,可以卓越到止於至善,與天主為夥伴。
夏大常引述周敦頤的話說:「士希賢,賢希聖,聖希天」,用白話來說,一般士人希望達到賢人的地步,賢人希望達到聖人的地步,聖人希望達到天的地步,總之,人是可以達至於天,與天合一。如果我能夠全面展開我的理智、意志與記憶的能力,將自我與天主合一,天主一定可以增益我的理智、意志與記憶,以便照亮我心。在心靈亮處有天主,我就能夠與祂在彼處合一。當天主在天的時候,我能夠與祂在天合一;當天主下降於地的時候,我也能夠與祂在地合一;我將可與天主毫無分離,而天主將永不棄我。由以上這些話語,可以見到夏大常是從儒家本性能力的論證,也就是人擁有「性善」的論證,加上了天主教徒「恩寵」的觀念,他似乎可以達到某種密契的論點,也就是把與天主密契結合視為是我展開我的自然本性,並與天主的恩寵結合,達致天人合一的密契經驗。
柏拉圖主義以及中世紀對亞里斯多德《靈魂論》的詮釋,造成了中國士人在習取亞里斯多德《靈魂論》時,對於中國傳統人性論的改造也有一個不良的後果。從以上的論述,我們可以看出有某種二元論,甚至是身心衝突論存在。更糟糕的是,夏大常把身體視為惡的來源,認為身體不但無法接近天主,而且身體好像是惡的。他把善性放在靈魂,是由靈魂論轉向性善論。然而,在他看來,惡的根源就在於身體。這點與利瑪竇和艾儒略那種二元的道德論是相合的,類似「去人欲而存天理」,尊德性而抑身體的想法。
這種對於人的靈肉二元論看法,可以說是自早期耶穌會士們引進了亞里斯多德《靈魂論》和天主教倫理學以後,十分一致的發展,成為中國天主教人性論的基礎。此一思路的不良結果,在於失去了靈肉合一的想法。其實,亞里斯多德本人曾做了非常大的努力,試圖維繫身體與靈魂的合一。來華耶穌會士引進的亞里斯多德的靈魂論以及在早期華人天主教徒的性善論中,所得到的是相反的結果,強調靈肉二元論。這在實踐上也造成在道德上鄙視身體,心存於用抽象的理想提升靈魂,反而輕視了欲望本身的創造性,因而走向抑制性的德行觀,失去了創造性的德行觀。就此而言,明、清的中國基督徒在人性論、倫理學、神學上,也都有類似的問題。從夏大常的例子,可見一斑。
建立在上述靈肉二元論上,耶穌會士及其所影響的教友,很自然地便傾向於主張壓抑身體慾望而發揚靈魂善性的倫理學,換言之,主張壓抑的德性論,因而不同於古希臘或古典儒學的創新的德行論。
(三)耶穌會士的德行論倫理學:壓抑的德性論vs創新的德行論
像利瑪竇這樣的傳教士,在進入中國中國之後,由於他們都是學養極佳、品德高超的人,而中國人的道德意識一向敏銳,也因此他們的道德修養定會受到中國士人的佩服。即使反對他們的人,也不會否定他們的道德。中國人本是道德的民族,對於有德之人,即使立場不同有所爭執,內心多少還是會暗自佩服對方的人品。
關於倫理學論述,在利瑪竇的著作裡,如《交友論》、《畸人十篇》、《二十五言》、《天主實義》等,以及龐迪我(Didace de Pantoja, 1571– 1618)的《七克》,談的都是如何克服慾望以陶成德行。因為明末當時的社會力釋放,挾泥沙俱下,雖然一方面社會文化創造力豐富,另方面則有如孟子所說「人慾橫流」,個人道德與社會倫理不易維繫。龐迪我撰《七克》,論述如何克服七種慾望以陶成德行,也就是說,人要克服驕傲、慳吝、迷色、嫉妒、憤怒、貪饕、懶惰等七種慾望,至於德行則是在於克服這些慾望,轉成謙卑、慷慨、貞潔、欣賞、忍耐、知足、勤勞等美德。這樣子的想法比較接近後來的德國哲學家康德(Immanuel Kant,1724–1804),後者同樣也主張克服慾望,服從良心中的道德法則或義務,並以此為德行。對於這種以克制慾望為德行的想法,我稱之為「壓抑性的德行觀」。
基本上,利瑪竇、龐迪我已及其他明末清初的耶穌會士,大抵都是持壓抑性的德行觀。他們比康德要早一個多世紀,因為康德哲學是要到18世紀末葉才提出其道德哲學,主張壓抑性的德行觀。我用「壓抑性的德行觀」來對比於孔、孟或亞里斯多德的「創造性的德行觀」,後者認為「德行」是在於自身本有能力的卓越化。人本有一些善根或向善的良好能力,如有惻隱之心,有不忍人之心,將之發展,使之卓越化,便成為「仁」德;有認知能力或「是非之心」,將之發展,使之卓越化,便成為「智」德。依同理,仁、義、禮、智皆可成德。亞里斯多德也是如此,對他來說,德行就是良好能力的卓越化;智慧、勇敢、節制、和正義,都是人本有良好能力的卓越化。
比較起來,先秦儒家的德行觀也有不同於亞里斯多德之處。先秦儒家除了講本有良好能力的卓越化,還講關係的和諧化,視之為德行。人致力於與父母關係和諧,是為「孝」;弟致力於與兄關係和諧,是為「悌」;此外,恭、寬、信、敏、惠等等,這些德行也都是關係性的德行,都是取得良好甚至和諧的關係。總之,在先秦儒家裡面,德行包含了能力的卓越化和關係的和諧化,兩者都是創造性的、動態性的,並不主張壓抑慾望,亦非以為壓抑慾望就可以達至德行。
利瑪竇這些人雖然嚮往先秦儒家,但他們之所以嚮往,是因為其中有對天的敬仰,至於他們對於先秦儒家創造性的德行觀,並沒有深切的體會,反而是從壓抑的德行觀來理解「克己復禮」之意。這和他們對於人學和人性論的看法有關係。照他們看來,人有靈魂,有肉體,而靈、肉二元對立:肉體是慾望的來源、是罪惡的淵藪;靈魂則是善的,心中嚮往天主。然而,人要親近天主,就必須克制肉體慾望,陶成美德。這是一種二元論的人性論。他們認為:此世只是暫時的過旅,真正的人生目的是在天堂。為此,必須否定此世的慾望,陶成德行,致力於永恆的生命。
利瑪竇等人來華,著儒服,行儒禮,說儒言,為什麼人們會尊敬他們?理由不但與他們的品德高超有關,另方面也與當時的中國倫理思潮有關。其實,這種二元論的倫理思想和壓抑性的德行觀,基本上和朱熹的「去人欲,存天理」十分接近;與佛家「去三毒」(貪、嗔、癡),恢復三善根,也頗類似。與道教清心寡慾、恬淡無私的想法也頗接近。即使利瑪竇等人與宋明儒學、佛教、道教彼此有批評、相爭論,但中國各教,只要是有德之人,心中總會暗自相互景仰。孔子早說過「德不孤,必有鄰」。也因此,他們的倫理思想能夠在中國受到歡迎,很大的原因是因為宋明儒學、佛教、道教等已經在中國文化的土壤裡為他們預備了友善的環境。所以,我同意法國漢學家謝和耐(Jacques Gernet)的說法:「利氏把佛教及和尚們當做主要敵人,但其實當時的道德與利氏的教導最為相合者,正是來自佛教。」[16]謝和耐只提到佛教,其時當時的儒家與道家也都與利瑪竇一致,持壓抑性的德行觀。
換言之,以上這些宗教在挽救世風上,其道德論述頗為類似,這恐怕也是時局使然。在西方文藝復興時期,由於從中世紀的禁錮中獲得解放,人慾橫流。這從當時繪畫、文學、民風中的尋歡縱慾可以見之。在明末的中國,也是如此。雖然說由於明末社會解放、人慾橫流,各教只能從道德上要求節慾以成德,透過壓抑慾望來約束人心。到了清初,社會逐漸被新的政權納入控制,也要求克己復禮,節制慾望,以便政權容易控制民間活力。道德的約束與政治的控制不同,然其目的都在控制慾望,結果出現禁慾性、壓抑性的德行觀,也失去了原始儒家的創造性,與先秦儒家以追求能力卓越與關係和諧,有所不同。
(四)「實踐論」:以德沛為例
我個人感到最有意思的,是在滿族入主中原以後第一位進天主教的親王德沛,著有《實踐錄》,收錄在法國國家圖書館收藏的《明清天主教文獻》第十二冊。一位清代早期親王對於儒學有深刻體驗,且將儒學和天主教思想初融,令人刮目相看。
《實踐錄》認為,儒家的道統在《大學》和《中庸》裡說得最明白,也因此德沛認為《學》、《庸》是道統之本。他進而認為,《孟子》更能發源繼本,充其廣大。所以,若要懂《學》、《庸》的實踐之途,要從《孟子》下手來了解。為此,他常會引證孟子來討論其實踐之方。
德沛的基本論點是:《大學》的宗旨是「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於至善。」他認為「明明德」所要點亮的光明,就是我本性原有的至善,也就是我的靈魂。由於德沛的天主教信仰,如同夏大常一般,他也認為「性」就是本性的至善,也就是人的靈魂。所以,他以《中庸》所講「天命之謂性」就是天主教思想所講的上帝創造人的靈魂。在《聖經》理,上帝創造每樣東西,都說是善的;到了人,則是用上帝的肖像來造,更是善的。德佩以下這段話頗能顯示他的儒學修養:
大學所言明其明德,自得之。又推以及人以新之,而在止於至善也。明德者,本性之至善,天命之道也。為氣質所牽,失其本善,…天命人之性者,非如萬物陰陽寒熱燥濕上下之性。乃推明格物至善之靈性也。[17]
大學之道也,學之言大者。…乃孟子所謂從其大體為大人之大也。…從其大體為大人,從其小體為小人。…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不能奪也。此為大人而已矣。夫心乃一身主宰,為性之宮,非血肉之心。[18]
夫大體之靈性,秉天之命,大公而無私,純善而無惡者也。[19]
在德沛看來,《大學》講明明德,既然是指人本性的至善之德,是天命之性,也就是天主給每一個人所準備的靈魂。每個人更要進一步透過實踐,推己及人,日新又新,一直到止於至善。個人必須不斷推廣內在本有靈性的至善,這是來自於天主所賜的虛靈不昧的靈魂(明德),也因此人不同於萬物,人的存在在萬物中有它的獨特性。在這一點上,滿人的德沛,正如同漢人的夏大常一樣,都同樣奉天主教信仰,都強調人的性是靈魂,有虛靈不昧之心。人至善的靈性,不同於萬物陰陽、寒熱、燥濕、上下之理。就此而言,朱熹講的陰陽之道,只適用於天下萬物。然而,人不僅止於陰陽;在陰陽之上,人還有靈明,也就是靈魂。
《大學》之所以為大,是因為它是尊從大體的成德之學。所謂的大,要從孟子下手,就是孟子所說「從其大體為大人,從其小體為小人」。所以,要先「立乎其大者」(陸象山的話),以大體為主,其小者就不能奪了。心是一身的主宰,如果人秉天之命,明其明德,大公無私,那就會成就純然的善。心就是大體,身只是小體。所以,在德沛的實踐論裡,最重要的就是要先立乎其大者,要以心向德行的要求為主,大公而無私。這一點並不止於個人修身,須更提振於公共事物。實踐的方向,除了倫理實踐,還有軍事、政治等各方面。
不過,德沛的基本論點仍是靈肉二元,大體、小體對立的思想。他認為,靈性的大體都願意盡忠盡孝,靈魂才會安心;然而,軀殼小體只圖自己安逸。他說,「如待漏侍朝於君,問安視膳於親,靈性大體,惟願致身竭力,以盡其忠孝乃安。若軀殼小體,則避寒暑奔勞,而惟安逸是樂。」[20]可見德沛在實踐論上和夏大常一樣,都秉承早期利瑪竇等人引進的靈肉二元論思想。對他而言,小體指身體及其慾望,大體則指靈性修德之心,雖然說大體、小體在倫理上(如侍親),在政治上(如侍君),可以有不同的表現,但無論如何,人必須克制慾望,才能達到德行。若是譬諸軍事作戰,用兵行陣,又如何解,如何實踐呢?德沛的詮釋是:「用之行陣合戰,靈性則知捨生不避鋒刃,盡天命以思報於朝廷。小體惟恐利鏃之穿骨,肉身之難當,而求邀幸遯避耳。」[21]
德沛本人很有儒者風範,他到處講論儒學,甚至在軍中也講,每講完之後若部下有所補充,德沛都會在聆聽以後,走下台階向部下表示佩服。當然,這也可以視為滿人學習統治中國的一部份技巧,然而我們不能說因為滿人需要儒學來統治中國,就忽略了個別人物的儒學風範。綜合起來,德沛又引孟子之言說:「孟子又曰,仁義忠信,樂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古之人,修其天爵而人爵從之。今之人,修其天爵,以要人爵。」由此可見,德沛的政治批判除了反省政治劣跡,還包含了揭櫫理想。他認為理想的情況應該是,個人修好德行,才獲取人爵。換言之,道德的實踐應該優先於政治和軍事的實踐。這也是孔孟之道一貫的精神。
諸德行中,德沛特別強調「仁」與「勇」,主張倫理的實踐是「仁」,政治與軍事的實踐則是「勇」,並認為到了至仁大勇,就可以守住靈性的大體,而不受小體利害的負面影響。「如至仁大勇,守靈性大體者,豈肯為小體利害所奪哉。」[22]在他看來,陸象山所謂「先立乎其大者」就是以仁、勇為先;先修好仁勇之德,便不為小體的利害所奪。仁、勇這些德行的獲得基本上屬於壓抑性的德行,而且把世俗所謂的福當作禍、當作苦;把世間所謂的禍、苦當作是福。基本上是激勵人抑慾進德。須知當時天主教強調壓抑慾望,在宗教上不強調求福。德沛說:「世之所謂福者,道之所謂凶也,人之所謂禍者,理之所謂大吉也。」[23]所以他不接受世俗的禍福標準,要克制小體對世間福樂的追求,克制慾望才能成就德行,完成至仁大勇之德。
原則上,德沛的靈肉二元論與壓抑性德行觀,都與明末清初的天主教思想和儒釋道倫理思想一致。就此也可看出,無論夏大常或是德沛,一位是漢族士人在逃難中思考問題,一位是新統治者滿族親王,雖因政權轉移,禍福不一,但他們都信仰了天主教提供給他們的核心思想,並在這核心上融合天中西傳統。在我看來,無論是在朝在野,這個中西思想的初步融合逐漸形成了清代的一種思想趨勢。雖然其中仍有不少問題值得檢討,但我們也可以看出他們中西融合的努力,以及他們對融合天儒的貢獻。
五、初期來華耶穌會士與華人教友
的宗教論述與本體外推
(一)天主的觀念與天主存在證明
首先,在語言的外推上,很難把這一神論的信仰用適當的中文語詞表達。例如,對於三位一體的神,在語詞方面到底是使用哪個語詞好?用《詩經》、《尚書》中使用的「上帝」?或其後耶穌會士訂定的「天主」?從其最初的文獻可以看到,耶穌會內部也開會討論,做過論辯。在日本,也曾用「天道」「天尊」「天主」等語詞,但方濟‧沙勿略(Francis Xavier, 1506-1552)最後仍決定使用音譯原則,譯為「陡斯」,這是拉丁文Deus一詞的音譯。在中國,由於羅明堅、利瑪竇等人對中國經典的熟悉,也深知在中國「文采不彰,其行不遠」,所以,他們雖也用過「陡斯」一詞,但他們也深知,該詞於音雖勉強類似,但於義則並不雅馴。若用中國經典中的「天」或「上帝」,則會導致與多神論糾纏的問題,因為中國的「天」或「上帝」都仍與四方、山川、河流諸神同在且密切相關,是多神論的脈絡。此外,他們也擔心如此採用「天」與「上帝」,好像是說中國人不經啟示便早已認識了宇宙的創造者,但卻又主張多神論。基於謹慎,耶穌會士曾經多次論辯,也開過幾次會議,最後在1628年的嘉定會議中,決定禁用「天」與「上帝」等詞,而承認利瑪竇採用的「天主」一詞,雖然這一詞仍有不少問題,他們也清楚認知到。
在哲學上,對於「天主」存在的證明,當時利瑪竇是運用聖多瑪斯的五路證明(Five Ways,拉丁文Quinque viæ),加上一些他認為較切近中國心靈的論證。五路證明的前三個,基本上都屬於因果論證;第四個是等級論證,說的是所有美善都有等級,從美善,到更美善,到最美善,那也就是天主。最後,第五路是目的論論證或設計者論證:看到宇宙萬物如此有次序,應該是出自一偉大的設計者,按照目的來設計的。這五路證明,對於中國人來講,太過抽象。中國人按照宋明理學所認為,人可以從內心「對越在天」,來感應於終極實在,[24]也就是從道德體驗出發,超越到對於天的感應。對此,利瑪竇也有所覺察,所以他在《天主實義》中,在提出五路證明之前,先討論了道德論證。可惜,這點到了後來,沒有再獲得發揮,等於是略而未詳,沒能詳加論證,或深入發展,來與中國哲學由內在而超越的思路相互交談。
此外,利瑪竇追隨聖多瑪斯,視上帝為最高實體,是第一實體,是純粹的精神,這對於中國人的吸引力不大;雖然這對西方學術而言,有其重要意義。這一從亞里斯多德的實體形上學發展出來的上帝觀,曾在中世紀賦予了宇宙秩序以一理性的最後基礎。這暗示近代科學發展的根本精神來自中世紀的根源,因為宇宙所以可以讓人不斷探討而認識其法則,對整個宇宙給出一個徹底的解釋,除了宇宙中含藏理性結構之外,應該還有一個最終根源,其本身就是理性的。但是,這樣的想法對於當時中國士人的心態,與中國人由內心的道德感動出發,由內在而超越,並不相應。另一方面,上帝是實體,是第一實體,如同利瑪竇他們所論證的,是因為只有實體才能夠創造萬物,這種實體觀使早期來華耶穌會士們無法深入了解儒、釋、道不執著於實體的思想與信仰,以至實體的上帝關與中華傳統哲學格格不入,甚致衝突。
然而,中國人卻一直採取非實體,或者不執泥於實體,的形上學。對於亞里斯多德而言,終極實在是「思想思想其自身」(noesis noeseos)的純粹實體,也就是全面自覺的思想實體。但對於中國人而言,朱熹的「理」是非實體的;老子的「道」也不是有位格的實體;佛家的「空」或「一心」也不是實體;儒家的「天」也是非實體的,或許會思、會想、會體察民意、同情老百姓的痛苦,但並不代表祂一定是個有位格的實體神。以上都是非位格的終極實在,中國人在設想終極真實的時候往往不願將它定位為實體。
(二)天主為實體與朱熹的「理」、道家的「無」、佛家的「空」
首先,關於「實體」與「無」
在這種「存有‧實體‧神‧學」的思想想架構下,利瑪竇及其他耶穌會士很難體會道家或佛教所講的「無」或「空」的概念。首先比較「實體」與道家的「無」。簡單說起來,第一,在《老子》形上學、存有論裡面,「無」與「有」是「道」開顯的兩個環節。按照我的閱讀,「道」先開顯為奧妙無盡的可能性,稱之為「無」;在所有可能性裡面只有一小部份實現為「有」。所以,奧妙無窮的可能性優先於有物。在形上學上面,無限奧妙的可能性不能以實體視之。可惜,利瑪竇等人沒有了解到這一點。
第二,「無」也代表內心的自由,如老子曰「故常無,欲以觀其妙」,「有之以為利,無之以為用」,其中的「無」,意為內心的自由,不被「有」所限制。對照起來,「有」是實現,是充實,是實在。故曰「有之以觀其徼」,常有之、實現之,才可以看出的實現的痕跡與限制。唯有透過「常無,以觀其妙」,看到奧妙的可能性,內心才會自由。這兩者是互動的,並不是說重無輕有,它只說人一生中常要作「有」的行動,以感到生命的充實和界限;但在其中也常要觀想「無」的可能性,使內心得到自由。可見,「無」是有關於奧妙的可能性和內心的自由,然而利瑪竇及其他耶穌會士在實體形上學的架構下看不見這一點,只看到最低的形器層面。
在第三層面,也就是形器層面的有與無,在或不在,呈現或不呈現。就此而言,利瑪竇等人要問:不呈現、不在、非實體的東西怎能成為萬物的原因呢?由於這層認定與詮釋,在中、西交談的時候,就發生了困難。其實,基督宗教這一方也可以反思,所謂上帝「無中生有」(creatio ex nihilo),到底那「無」是什麼意思?是在「空無一物」的「無」中創造?還是在奧妙的可能性中創造。這也是值得在形而上學層面上再加以反省的。
其次,有關佛家的「空」。在佛教裡面,「空」一詞雖然有很多意義,基本上也可歸結為三層意思。第一層意思,是形上層面的「空」,意指「緣起性空」,所有萬物的存在都不是由於以自己為原因,使自己存在的;每一物的存在都是因為相互依賴的因果,是一種依他起的、依賴緣起、相互依存的,所以各物皆沒有自性,稱之為「空」。換言之,每一物都沒有自己的實體,沒有實在性。對比起來,在亞里斯多德來說,「實體」就是自立體,自立體就是其他附性所依賴的底基。附性雖變化,但實體依舊在。「緣起性空」並不是說「空無一物」,而是講緣起性空;講「緣起」而不講「實體」;講相互依賴而不講直線因果。
「空」的第二層,是心理層面、精神層面的意義,也就是「不執著」的意思。如《金剛經》所言「應無所住,而生其心」,也就是說心不應有所執著,不執著於喜怒哀樂這些心理現象,執之作「我」,也不執著於一個先驗的「我」。沒有我執,沒有法執,毫無所執。即使有所成就,也不執著於自己的成就,例如,不執著於自己是一個大思想家、或自己的文化有多優越;甚至連「空」這一概念都不應執著。連「空」都要「空」掉,因為你一旦執著於「空」,那就是「頑空」了。由於不執著,所以給出了徹底的精神自由,這一精神自由要比道家的「無」還要徹底,因為它連「空」都不執著。「緣起性空」和無執的自由都是「空」的要旨,但是利瑪竇他們並未體會及此,以至沒法與佛教深入交談。
「空」的第三個意義,是語言層面上的「空」,是說人所使用的所有語言,包括「身體」、「桌子」、「杯子」…等等話語,都是人建構的,在實在的世界中沒有真正的對應物。就語言哲學而言,是說所有的語言都沒有固定的指涉(reference),都只是人的「語言的建構」(linguistic construction),就連「身體也是出自人的語言建構,名不當實,實不當名。
總之,當時的耶穌會士們並沒有了解到佛教「空」的真義與深意,而佛教也未能體驗到耶穌會士對於天主的深刻的宗教經驗。換言之,他們論辯概念者多,交換經驗者少。於是,無論交談或批評就不易深入,反而招致更多彼此的批評和反對,於是彼此往往捉住對方膚淺、表面的東西來相互批評,造成更多的誤會。換言之,西方的「第一實體」和道家的「無」和佛教的「空」,都是在宗教層面對於終極真實及在各自的信仰中最為關鍵的概念。在宗教交談之時,天主的實體性與佛教之空和道家之無,無法達成相互了解。其實,在天主教來講,天主也有「隱藏的上帝」(Hidden God)的一面,舉凡人所有的言說、論述,無論科學、神學、哲學想要去論述祂,也都不能夠窮盡,換言之,隱藏的上帝,上帝本身在人的建構之外無限後退,這一層意思其實與「空」和「無」所要表達之意,可以相互溝通。
(三)夏大常對中國宗教性質的查考
在禮儀之爭前後,耶穌會動員了他們影響的中國士人,致力提供中國經典與民俗材料與詮釋,讓耶穌會士們為其文化適應路線的正確性辯護。同時,他們也重新整理了中國經典,找尋文本根據,並加以適當詮釋,來證明祭祖、祭孔不是在崇拜其他神明以代替天主,藉此也釐清了中國人祭祖、祭孔的宗教性質。禮儀之爭有一部分重要議題涉及一些中國宗教現象的了解和詮釋。這有如今天所謂的宗教學研究。夏大常對於中國禮儀相關文獻非常嫻熟,雖在戰亂之中遺失典籍,但仍能靠記憶寫出很多文章,富於中國宗教研究的學術涵義。基本上,夏大常的論述有中國經典文本支持,並賦予這些經典文本以富於宗教學意涵的詮釋,可謂中西初融時的重要中國宗教學者。
首先,針對祭祖,夏大常的基本論點是:祭祖是出自兒女對父母的孝心。子女於父母在世時要能侍養,父母去世後要能祭祀,好像仍在供養他們一樣。孝心是人最重要的天性,是應該保存的。所以,祭祖是完全出於盡孝、慎終追遠之心,並不是把父母當作神來崇拜。
其次,關於祭孔,理由也頗類似,是為了尊重聖人。孔子是中國文化思想的開創者,所以,所有的文人都要尊敬孔子。但這種尊敬並不代表把孔子當作神來崇拜,而是基於對文化、理想和人可以達到的聖人典範的推崇。所以,目的不是在求孔子的降福保佑,而是尊師重道的表現。
再次,關於其他的祭祀,譬如生祠或死後立廟,夏大常也做了很詳細的考察,認為立生祠的意義主要在於尊敬某人的功勞、功勳,崇敬他是一位人間英雄;至於死後立廟,則是紀念所做過的善事或功德,或立功、立德、立言的三不朽,而不是把某人奉為神明,更不是向他求福。
透過夏大常的書寫,我們可以瞭解到他對中國古代禮儀的理解與詮釋。初期的天主教徒中國士人,他們雖然在形而上思想、人性論、實踐論上作了某種雛形的中西融合,但他們對於中國文化的了解,基本上仍繼承中國傳統士人的詮釋理性,換言之,是立基於對中國經典的詮釋來思考。雖然他們在西學影響下,思路比較系統化,也可以說是在「詮釋中建構」。底子裡的精神還是中國哲學的精神。[25]本文特別集中在夏大常論述祭祀的性質與人天關係上。他在講解《禮記》〈禮器篇〉時又說:
君子曰,「祭祀不祈」,…乃是孔子教人奉祭之心,惟當盡道,不當求福也。得其道者,是言盡我誠敬之心也。若能盡誠敬之心,便為受福之道。…可知中國祭禮,並無求福之心矣。[26]
夏大常詮解《禮記》孔子之言,以明中國祭禮之義不在求福,而在表達孔子所說「誠敬之心」,這點可以印證《論語》中孔子所言「祭神如神在」之意。這話說出了禮儀的本質在於誠敬之心,而不是為了一種功利的交換:我向你祭祀,你賞給我福報。換言之,宗教行為之義不在於功利主義,更不在利益交換,而是出自人的宗教情感誠心的宣洩,包含對自己尊崇的人、或對自己的親人的一種懷念。人若不如此做,是不會安心的。
夏大常進一步引〈祭義篇〉說:「君子生則敬養,死則敬饗,思終身弗辱也。」指出中國禮儀中祭拜祖先的性質只是一個不忍忘親之念。所以,他解孟子言「大孝終身慕父母」之意說:
終身云者,非終父母之身,乃終孝子之身也。生則敬養者,尚未欲以我之愛親者,而求親之愛我。惟於死則敬饗之日,親既不能顯愛於我,而我獨能愛親於不忘焉。斯為大孝終身慕父母矣。[27]
很有意思的是,夏大常這一詮釋,雖指出「生則敬養」,「死則敬饗」都出於孝愛之情,在愛父母上都是相同的,但是「生則敬養」還有「求親之愛我」的相互性的意思;然而,「死則敬饗」則是再無相互性之意,因為父母過世了,再也不能因我之愛他而愛我,是完全超越了相互性之愛的表現。在此,夏大常很了不起地指出了中國宗教情操與禮儀有其超越相互性、甚至超越功利性、交換性的層面,而純屬愛的表現。更有意思的是,他在如此講完「斯為大孝終身慕父母矣」之後補上一句:「此與未見天主而信天主者,約相同矣」,以對父母純粹愛的表現來講對天主的信仰。請注意:「約相同矣」一句,初稿原來寫作「同此心矣」,後來大概意識到「終身慕父母」與信天主只有類比的關係,同中仍有不同,所以其後改為「約相同矣」。
以上,夏大常大體講出了中國祭祀禮儀的意義。他在探討中國宗教現象時引經據典,加以詮釋,以回答耶穌會士們的詢問,同時也順便把中國人自己的禮儀分析清楚,這中間已經有針對中西溝通、天學與儒學關係的探討。同時,這也是最早在跨文化視野下,提出的中國宗教研究,惜僅止於雛形。更可惜的是,爾後由於中國人自己的忽視,未能繼續發展,倒是西方學者成為中國宗教研究的領航者。
最後,夏大常也討論中國禮儀與天主教義有否不相容關係的問題。夏大常基本上是從中國所謂「立教」之意,指出其與西方「宗教」有不同而實相通。夏大常認為:中國是以禮「立教」,是為了讓人們發揮其「人性」,使生活有所依循;至於宗教則是為了發揮人的「超性」,以侍奉天地萬物的主宰天主。必須先通人性,否則安能通於超性?中國人以禮立教,不能因為禮會有被濫用的弊端,就禁了禮本身。夏大常說:
祭禮亦猶是也。若禁祭禮,中國人心必疑聖教中人,來亂教法矣。故立教者,惟當去其毒害人心之實,不必改此空疏無用之名。求福之祭當禁矣。追養繼孝之祭,不當禁也。土神之祭,當禁矣。視死如生之祭,不當禁也。猶之生子者,惟當禁邪淫,不可盡其生子,以絕人類也。[28]
換言之,如果祭祀裡有迷信求福等不當之處,可以改之,但不必因噎廢食,禁掉全部祭祀之禮。中國以禮立教,在五禮當中以祭為先。祭的不同種類,各有其意義。祭祖先是為了奉饗,安孝子之心,顯示誠意,秉告祖先,不敢自專等等,有這許多合乎人性的意義,因而不可廢祭之名。他說:「求福之祭當禁」,表明如果是為了求福之祭,是一種功利式的、交換式的祭祀,是應該禁。但若是追養盡孝之祭,則不當禁。若是塑造土神模型,當作神明來膜拜,這當禁。若是視死如生之祭,像祭孔子這樣的聖人,不當禁。就像人要結婚,有男女之事,要生小孩,可以禁止人邪淫,禁人到處拈花惹草,宣洩情慾,可是人總要延續後代,總要生小孩,這是不能禁的。所以,祭不能禁,就像人要生小孩不能禁一般。換言之,中國以禮立教之意,是出於人性的需要。所以夏大常在辨明中國宗教的意義之後,進一步表示祭祀不能禁。他進一步說明,祭祖之禮並不與天主教的誡命有實質上的衝突。他說:
中國立祭之心,原相合于天主教人孝順父母之誠矣,唯此一祭之名,特恐有礙於欽崇一天主之義,然亦只是此名相礙,並無傷礙之實。奉祭天主者,奉其為天地萬物之大父母。奉祭祖先者,不過奉其為一家一身之小父母而已耳。[29]
夏大常指出,祭祖之禮合乎天主教規十誡中第四誡「孝順父母」;然而他也意識到,用祭祀來表達孝心,按天主教這邊的覺識,有可能會妨礙到第一誡「欽崇一天主於萬有之上」。然而,他也指出這種衝突,只是由於「祭祀」此一名義的相似性,因為天主教所獻於天主的彌撒,也稱做「祭獻」。然而,夏大常認為,這只是名目上的,並無實際上的任何傷礙。可見,他區分「名義上的衝突」(nominalist conflict)與「實質上的衝突」(substantial conflict),認為祭祖只是和彌撒有表面上的、名義上的衝突,實質上毫無衝突。他這一分辨,以及對中國宗教的定性,重點放在其內在實質的意義,認為不能只停留於表面,甚至望文生義。換言之,他不贊成唯名論的宗教閱讀。他的主張,是在實際上天主教的第四誡不會與第一誡相衝突;就中國而言,第四誡孝順父母,其實是與第一誡孝順天地的大父母是一致而延續的。他說,「奉祭天主者,奉其為天地萬物之大父母。奉祭祖先者,不過奉其為一家一身之小父母而已耳。」[30]
這一想法試圖把中國人與父母的關係、甚至家庭的概念,擴張到理解天主教會,理解人與天主的關係。這是一般中國人比較容易接受的關係性思惟:天主是創造天地萬物的大父母,天主教會是由天地大父母與眾子女形成的大家庭,這樣的想法使得天主教顯得頗有親和性。其實,孝敬父母、祭拜父母,跟彌撒祭拜天主,並不相衝突。一個是祭祀天地大父母,一個是祭祀一個家庭裡的小父母。就此一家庭之愛而言,他認為在父母、愛等名相上,本性與超性並不相反,卻有所契合。他說:
況乎本性中之立名者,亦多有合乎超性中之名者矣,言超性者,曰愛天主也;言本性者,亦曰愛父母矣。言超性者曰,敬天主也;言本性者亦曰,敬父母矣。言超性者曰孝天主也,言本性者亦曰,孝父母矣…。[31]
夏大常透過擴大化的「家庭關係」、「父母」、「孝、愛、敬」等概念來看,認為即使在名義上其實也無衝突可言,從祭父母一直到祭天主,在名義上也不相反。表面上,膚淺看,好像名義相反;事實上,本性的立名者,像孝順父母、愛父母這些名稱,也都合乎超性的孝順天主、愛天主。所以他主張:超性和本性可以相合。他用這一倫理論證來講儒家發揮了人本性之義,而天主教進一步發展了超性之義。不應該以超性廢本性,因為本性也是由超性所造;也不該只停留在本性而忽視人有其超性根源。就此而言,夏大常已經訂定了一個天主教與儒家融合的良好理論基礎。他說:
超性不能相通於本性者,亦非真為超性者也,西洋言超性者,即為中國所言天道矣,天道人道其理一也。謂超性之奧,無過三位一體,然有粗像可比也。論天主全能全知全善,真為人世無可比擬之處。然而朝廷之威莫測,聖人之出類超羣,可比也。超性固當反本報始于天主,本性亦當反本報始于父母矣。[32]
在此他將西學所講的超性與中國所講的天道相比擬。在中國哲學言,天道與人道是相通而連續的,不是相背反的、相壓制的。他也認知到天主教三位一體的道理最為深奧,「謂超性之奧,無過三位一體。」可見,夏大常是個深於教理的天主教徒。關於三位一體,這是天主教的一個基本教義,極其玄奧難懂。不過,夏大常認為,天主聖三雖奧妙難明,然也有聖三畫像,雖然畫像粗糙,也粗可獲得類比的了解;對於天主的全知全能,人世雖無可比擬,然亦可在朝廷之威與聖人之超凡獲得類比的理解。類比(analogy)之哲學意義曾在聖多瑪斯那裡獲得深入的發揮;夏大常在此則用於他的倫理論證,並使用類比的方式來理解本性與超性的關係。「超性固當反本報始於天主,本性亦當反本報始於父母矣」。對於夏大常來講,中國經典和書籍是聖人之教。聖人體察人的本性而能夠任萬物的面貌睹現,因此知道人應如何發展本性,不但不相反超性,而且可進一步銜接超性。也因此他另外寫了《性說》,綜合了中西人性論,其中銜接了人性與超性,助耶穌會士們發揚超性之理於中國。這其中有一貫串的道理,那就是「追本溯源」,正如同人的生命是來自父母、祖先;天地萬物也可追溯到最初來自天主的創造。夏大常用以連接本性與超性的「報本返始」概念,仍有其深刻的啟發。
六、結論
平心而論,當時耶穌會如果多談一些自己對終極真實的體驗,少談那些抽象的天主存在證明;不但引進亞里斯多德和多瑪斯的理性論,也引進拉丁教父、希臘教父,或像艾卡特大師(Meister Eckhart, 1260-1328)等人的密契論,一定可以獲得同樣關心終極真實的儒釋道各教的共鳴。換言之,如果當時耶穌會士,除了引進西方科學與理性論以濟補中華文化的不足之外,而且更能與中國士人分享他們對終極真實的體驗與感懷,他們對隱藏的天主的體會、宗教奧秘的體會,還有基督宗教所講的自由與關係的想法等等,進一步邀請彼此來相互體會,再發為相互可懂、設身處地為對方著想的言論,或許天主教能和道家、佛家有更為深入的交流。
總之,在明末首先譯介並引進亞里斯多德,有好也有壞。好的是,在邏輯與科學方面有很大的貢獻;不好的是,無法碰觸到中國士人的心底。我有時會想,如果當時引進的是希臘教父或拉丁教父或中世紀的密契論大師的著作,他們的文采好,關心人內心的體驗,而且心懷對奧妙的驚異,甚至論及對天主的愛,更有密契論的深度,或許更能親近中國的思想家。或許,當時應該在這方面多從事翻譯工作。可惜當時耶穌會為了表現他們的思想體系與教育體系的科學性、邏輯性與理性,以及自我認識的重要性,而這已經觸及文藝復興時期重視理性與主體的近代性精神,因而作出的外推抉擇,以致在內心體驗、心懷奧妙與密契論深度方面,沒有多加發揮,殊甚可惜。
Matteo Ricci and His Method of Cultural Accommodation
Hu Yeping*
Abstract:I would like to borrow Tang Yijie’s analyses on the three principles of cultural communication and integration and on four aspects of Matteo Ricci in working with Confucian literati to illustrate the possibility of dialogue and cooperation of different cultural traditions and religious faiths and the significance of Ricci’s implementation of the method of cultural accommodation between Christianity, particularly, Catholicism, and Confucianism in the Ming Dynasty for our complex global world today.
Key words:method of cultural accommodation adaptation Catholicism Confucianism
Matteo Ricci begins his book On Friendship with the following words:
I, Matteo, from the Far West, have sailed across the sea and entered China
with respect for the learned virtue of the Son of Heaven of the Great Ming
dynasty as well as for the teachings bequeathed by the ancient Kings….I
crossed the mountains, sailed down the river, and arrived in Jinling, where
I beheld the glory of the capital of the kingdom, which filled me with
happiness, and I thought that it was not in vain that I had made this
voyage.[33]
Indeed, how could Matteo Ricci, a Western missionary from Italy, spend almost 4 months on the sea in order to come to China despite many difficulties, not only language, food, climate, away from family, friends and familiar environment, but also risk to his own life? How could he eventually settle down in Peking, the capital of the ‘mid-kingdom’ of the Ming Dynasty China and make many friends, particularly the Confucian literati and influential officials? Why did so many officials and intellectuals at that time like to have conversations with him? What method did Ricci employ in his endeavor to communicate from his own cultural tradition and religious faith to the people and the country that he did not know at all at beginning and where he stayed till his death in the country’s capital? What are the contribution and the significance of Ricci’s unique way of understanding the other culture, people and civilization? What can we learn from his method and experience in understanding, respecting and communicating among different peoples, cultures and civilizations for these complex and global times?
In this paper, I would like to borrow Tang Yijie’s analyses on the three principles of cultural communication and integration and on four aspects of Matteo Ricci in working with Confucian literati to illustrate the possibility of dialogue and cooperation of different cultural traditions and religious faiths and the significance of Ricci’s implementation of the method of cultural accommodation between Christianity, particularly, Catholicism, and Confucianism in the Ming Dynasty for our complex global world today. Of course, there are still a number of issues or debates on Ricci’s method of cultural accommodation, particularly on the use of terminology and the understanding of rites and customs of the local culture. This paper will not go into these other inquiries but the one mentioned above.
In his bookConfucianism, Buddhism, Daoism, Christianity and Chinese Culture, Tang Yijie, whose father, Tang Yongtong, was the President of Peking University in earlier 20th century and a great scholar on Buddhism, argues that the issue of the introduction and integration of a foreign ideology, philosophy, religion or culture into a local existing one is rather complicated and difficult. Many factors can be considered in the process to determine the success and the failure. For instance, the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a local culture or civilization is not a matter of daily event, but rather a cumulative effort of decades or centuries. Thus, as the process goes it has been deeply rooted in its own socio-political, economic and cultural soil, characterized with its own particularities and records its own history. Tang Yijie notes that according to the success of Indian Buddhism assimilated and eventually embedded into Chinese cultural tradition, there are three major principles which could be suggestive: (1) adaptation to the local cultural tradition, (2) enrichment and intensification of the local cultural tradition, and (3) advancement and real contribution to the local cultural tradition.[34]
According to Tang Yijie, the foreign culture should first be grafted upon the body of the local culture, and then gradually develop its own specification and begin to have its own influence on the local culture and make valuable contributions. Through the process of growth, both cultures can be enriched. These three principles can be applied to Matteo Ricci in his development of the method of cultural accommodation during his stay in China in the 16thcentury.
Tang Yijie notes that Ricci knew well Chinese thought and culture, particularly those of Confucianism and highly appreciated Confucian ideas and its moral teachings. He made every effort to “link Oriental and Occidental cultures” through such methods as“Linking Catholicism with Confucianism (heru和儒)”,“Concordance with Confucianism (furu符儒)”, “Complementing Confucianism (buru补儒)”, and“Transcending Confucianism (chaoru超儒)”.[35]Joseph Sebes also points out three components in Ricci’s method: “life-style with the Confucian socio-ethical system on which it was based; terminology with underlying ideas and conceptions; and rites and customs inspired by ideology”.[36]
Method of Cultural Accommodation
Matteo Ricci was the first foreigner from Europe to settle down and reside in the imperial Forbidden City and had his writings included in an imperial anthology. He has become a legendary figure who courageously forged “meaningful cultural connections between Europe and China. Even as a Christian missionary…Ricci has been admired—and also severely criticized—for his attempts to adapt or ‘accommodate’ Christian teachings to Chinese cultural expectations…”[37]
The method of cultural accommodation was pioneered by Alessandro Valignano, who belonged to the same religious community as Ricci. He came to India and Macao a few years before Ricci and was considered as his mentor for the missionary work in China. After travelling and staying in Asian countries, he was convinced that in order to be integrated successfully with the local culture the outsiders should learn the local language, adapt its customs, and respect its traditions and ways of life. “…in all things compatible with dogma and evangelical morality the missionaries should become Indian in India, Chinese in China, and Japanese in Japan.”[38]This was quite innovative at the time.
With this innovation in mind Ricci looked for new ways to implement the method of cultural accommodation. Upon his arrival in Macao, Ricci began immediately learning Chinese language and Chinese classics. September 10, 1583 when Ricci and his colleague Michele Ruggieri, wearing long robes like Chinese Buddhist monks with limited knowledge of Chinese history, customs, language, etc., were kneeling among other Chinese in front of the Chinese official (prefect) in Zhaoqing, China, this marked“the beginning of the one of the most significant periods in the history of cultural exchange between East and West.”[39]
Throughout his long stay in China Ricci not only mastered the language both in speaking and writing, wore Chinese clothes and made friends with the local literati and imperial officials, but had deep interest, sympathy and respect for Chinese culture, particularly Chinese classics. He not only had a Chinese name, Li Madou (利玛窦), but also an honorific (hao号) as other Chinese literati, Xitai (西泰from the far West), by which names, Ricci has been remembered by the Chinese till today.
A.S. Rosso has noted, “Christianity necessarily found itself either accommodating itself to Chinese thought and life to the extent of losing its essential traits, or carrying on a struggle aimed at an evolution of the Chinese system. Ricci sought a solution in a provisional and partial accommodation.”[40]Ricci’s method of cultural accommodation is to have conversations with Chinese intellectuals discussing issues in which they were interested, such as life and death, good and evil, friendship, science, etc. Through friendly conversations, Ricci would suggest that there might be something worth knowing and learning from the West. He intended to build a liaison with this unknown country to the West on the basis of friendship and mutual understanding; and planned to establish “Chinese Christianity from within the empire on a basis of Chinese traditions and rules of conduct which were in conformity with Christian teaching.”[41]
Ricci tried to accommodate himself “in every way” where necessary and changed expressions in order to make them more acceptable to the Chinese. As Sebes claims“Ricci equated the Christian concept of love with the Confucian concept of humanness (jen仁).”[42]The essay,On Friendship(交友论), Ricci wrote in Chinese, was presented as a gift to the Prince of Jian An (Jian An Wang), a distant cousin of the emperor. The essay is a collection of maxims from the European thinkers on the theme of friendship. It is an effort to accommodate in the broadest sense and to establish a common ground for cross-cultural understanding, respect, and communication. The essay became very popular among the Chinese literati and “earned more credit” for Ricci and for the West: “other things do us credit for mechanical and artificial things of hands and tools; but this does us credit for literature, for wit, and for virtue.”[43]
Adaptation to the Chinese Cultural Tradition
In early days of Ricci’s stay in China the assimilation of Christianity to Buddhism was quite noticeable. As soon as Ricci and his colleagues came to China, they began wearing clothes like Buddhist monks. The similarities of images and status between the Madonna and Child and Guanyin in Buddhism, particularly Son-giving Guanyin, led many Chinese believers including local officials to kneel before the Madonna and Child. Since Ricci and his colleagues also came from the far West, India, they were considered as “bearers of the newest religious teaching from India”.[44]
However, as he gradually learned more about Chinese history, culture and tradition, he began to criticize Buddhism as a form of idolatry, but tried to find a linkage of Catholicism in Confucian thought. He also learned that it was important to work with Chinese officials as they were seen “like fathers and mothers” and intellectuals could someday become future officials through imperial civil examinations that were mainly about Confucian teachings.
Ricci and his colleagues learned Chinese “courtesies” and protocols in order to meet officials and to be situated in their new circumstances. In each place where he resided he tried to form friendship with local officials and influential figures, who enabled him to learn more of Chinese society and to whom he expressed his own religious doctrines. He urged Europeans to have sympathy and be patient with the Chinese people and not to lose hope in the country.
After Ricci mastered the language and the classics, he began to translate the Confucian major work Four Books into Latin and carefully studied Six Classics in order to find “material directly and genuinely related to China’s cultural heritage”.[45]He presented himself as a “Confucian scholar” and “introduced the concepts of the Catholic religion in terms of Confucian learning”.[46]As Ricci notes: many terms and phrases, for instance, “the unity of God”, “the immortality of the soul”, “the glory of the blessed”, etc., in Chinese classics are “in harmony with” Catholicism.[47]
In his major bookThe True Meaning of the Lord of Heaven(天主实录T’ien-chu Shih-i) Ricci often quoted such Chinese classics as The Book of Songs, The Book of History, The Book of Rites, The Book of Changes, and The Doctrine of the Mean in order to prove that “Catholicism corresponds to Confucianism and the ancient Chinese classics.”[48]As Ricci notes the Chinese classics provide wisdom and advice to teach people to be virtuous. The Chinese history of more than four thousand years is a history of rich records about the people’s “good deeds” for the country and for the common good. In this sense, the Chinese classics “seem to be quite the equals of our own most distinguished philosophers”.[49]
In order to fit Catholicism into Chinese society Ricci revised and adapted some of the Catholic doctrines. For instance, he showed his sympathy and respect for the offerings to Confucius and the ancestors. Although Ricci strongly criticizes the idolatry he perceived in Buddhism, he does not criticize the offerings and sacrifices to Confucius and ancestors. He noted that Confucius was considered the “Prince of Philosophers”[50]by the Chinese literati. Even the rulers paid him “the highest homage due to a mortal.”[51]“The Temple of Confucius is really the cathedral of the upper lettered and exclusive class of the Literati.” It was the center of learning. Yet the literati honor him only in the manner of honoring the dead who were dear to them. Confucius was never “venerated with religious rites” as a god.[52]Neither do they recite prayers to him, nor do they ask for favors or help from him,[53]but rather they honor Confucius for his teaching and practice of moral virtues.
The ultimate purpose and the general intention of this sect, the Literati, are
public peace and order in the kingdom. They likewise look forward the
economic security of the family and the virtuous training of the individual.
The precepts they formulate are certainly directive to such ends and quite
in conformity with the light of conscience and with Christian truth.[54]
Ricci does not criticize ancestor worship, but rather gives a detailed description of common practice from the rulers to the common people. It is a way of paying respect and honor to the dead close to them, showing the love of the living to the dead. It is also a way of teaching children how to respect and support parents who are still living. Ricci argues that such a practice of ancestor worship “seems to be beyond any charge of sacrilege” and “free from any taint of superstition”, because they do not consider their ancestors to be gods.[55]
Enrichment and Intensification of the Chinese Culture
In order to be accepted and understood by the Chinese people, Ricci intensifies some Catholic ideas with certain traditional Confucian thought in order to enrich and complement each other. Inthe True Meaning of the LordHeaven Ricci uses “the Lord of Heaven”(天主Tianzhu) to refer to the ChristianDeus, because the Chinese consider Heaven (天Tian) as the highest supremacy which creates and maintains all things. As Ricci notes the Chinese intellectuals do not believe in idol worship nor do they have idols; what they believe in is one deity who creates, governs and preserves all things on earth.[56]
In Chapter Two, Sections 103-108, Ricci quotes a number of the Chinese classics to argue that “the Lord of Heaven in my humble country is He who is calledShang-di(上帝Sovereign on High) in Chinese.”[57]The two terms are“different only in name”.[58]This can be found in many ancient Chinese writings. For instance, Ricci quotes Confucius inthe Doctrines of the Mean: “The ceremonies of sacrifices to Heaven and Earth are meant for the service of the Sovereign on High”; and hymns in the Book of Odes:“How beautiful are the wheat and the barley, Whose bright produce we shall receive! The bright and glorious Sovereign on High”; etc.
By employing Chinese classics Ricci argues that the concept of the Lord of Heaven in the West already existed in the Chinese antiquity. And through reading Chinese classics Ricci found that “by their own innate genius, they did have sufficient natural enlightenment”;[59]this could naturally serve as a constructive foundation for Christian teaching in China.
According to Ricci, God is already in the hearts of all human beings. If there is no God among all peoples, willingness to do good things would become groundless.[60]
All men who do good believe that there must exist a SUPREMELY HONORED ONE Shang-tsun) who governs this world. If this Honored One did not exist, or if He exists but does not intervene in human affairs, would this not be to shut the gate of doing good and to open the road of doing evil?[61]
In Chapter Four when discussing the spiritual being, Ricci again refers to the Chinese classics about the immortality of spiritual beings. In session 185, he uses theSpring and Autumn Annalsto illustrate how the ancient Chinese people believed human soul to be immortal. When one dies, it is only one’s body which is destroyed, but not one’s soul which will not die. Ricci also quotes theDoctrine of the Meanto assert that the spiritual being is the substance of all things.[62]In Session 206, Ricci points out that Confucius believes that spiritual beings are not constituents of matter, but rather “keep at a distance” from the categories of material things. Indeed, what Ricci is trying to do is to show “the compatibility between original Confucian thought and Christianity.”[63]
Ricci tried to prove that Catholicism and Confucianism are not against but complement each other in many ways. He added new components in the understanding and interpretation of Confucian thought. As Tang Yijie points out, Ricci “complements and revises” the Confucian concept on the issue of the retribution of good and evil. According to the Confucian tradition the “retribution of good and evil” basically refers to the outcome of a personal moral cultivation, that is to say, through moral self-cultivation one could reach the purpose of the inner moral accomplishment as a kind of “inner transcendence” as Tang Yijie argues.[64]
The Confucianism did not discuss the concept of heaven and hell, but focused more on reward and punishment during this lifetime. These rewards and punishments are not only on the loss and gain of bodily wealth and goods in this life, but especially on cultivating humanity (jen仁) which is the harmony of all right things on earth. Ricci quotes numerous Chinese classics to show that Chinese sages in antiquity used the concept of “rewards in order to induce people to do good, and punishments to make them avoid evil.”[65]
In order to explain Christian concept of reward and punishment in the afterlife, Ricci would add to the Confucian concept “the benefits of the world to come which are both supremely real and which hurt no one.”[66]He says there are three correct motives to do good things or to hold a higher standard of morality: “The lowest involves doing good in order to get to Heaven and to avoid going to Hell; the second, doing good in order to repay the Lord of Heaven for His profound favors; and the highest, doing good in order to harmonize with, and to obey, the Lord of Heaven’s sacred will.”[67]But, perfection in moral conduct does not depend on going to Heaven or to Hell, but on cultivation of humanity and righteousness, because “Heaven is nothing other than that glorious place where those of the past and present who have cultivated humanity and righteousness foregather.”[68]Virtue is founded on self-cultivation, and its fulfillment is in the service of the Sovereign on High or the Lord of Heaven. For instance, in the Chou dynasty this was considered as its prime duty.[69]
Here we see Ricci’s attempt to complement Confucianism with Christian morality and even to perfect Confucianism. According to Ricci Confucian teachings are “so far from being contrary to Christian principles, that such an institution could derive great benefit from Christianity and might be developed and perfected by it.”[70]In the process of promoting the interaction and enrichment of the two cultural traditions, Ricci does not simply impose his own belief and dogma, rather he uses Confucius as example to argue that instruction must be accommodated with the local people and culture. Thus, “when Confucius went to the State of Wei and saw the people there, he wanted first to enrich them and only then to instruct them.”[71]As Sebes points out Ricci gave Christianity a Confucian dimension, “he Confucianized Christianity or Christianized Confucianism.”[72]
Advancement and Contribution to the Chinese Culture
Joseph Needham says that “Matteo Ricci was one of the most remarkable and brilliant men in history…not only an extraordinary linguist, mastering the Chinese language to perfection, but also a scientist and mathematician of eminence.”[73]Indeed, Ricci not only learned Chinese classics and discussed important issues related to philosophy, literature, religious teachings, universe, life and death, etc., with Confucian intellectuals and officials, but also brought European science, particularly mathematics and astronomy to China.
Ricci acknowledged that the Chinese made not only considerable progress in moral philosophy but also in astronomy and in many branches of mathematics. However, through conversations with the literati Ricci found that despite the achievements made in ancient China the Chinese did not develop sciences as had Europe at that time; thus, he made efforts to teach astronomical and mathematical knowledge to the Chinese who were interested in the subjects. He taught the Chinese European cosmology and the Greek geometry ofEuclid’s Elements. He taught lessons about the prediction of lunar and solar eclipses, and about the earth as round which was unknown in China and the structure of the universe. He made various astronomical instruments as well as the first Western style map in a Chinese version with China positioned in the center.
He also brought clocks of European style as gifts and the skill of craftsmanship to China. He put up a mechanical clock outside of his residence. This was the first public clock of European style appeared in China.[74]In fact, because of the clock as a gift to the Ming emperor, Ricci was released from prison in Nanking and was able to go to the Forbidden City in Peking.[75]
The advanced knowledge in mathematics, astronomy and mechanical technology which Ricci displayed to the Chinese enabled him to make friends with both literati and ruling officials and opened a path for his implementation of cultural interchange and interaction between East and West. Nevertheless, science and mathematics are only instruments which lead to ethics and religion. “Between lessons in cosmology and geometry, Master Ricci discoursed little by little on Christian doctrines.”[76]
According to James C.P. Fan, Ricci made such contributions to the Chinese modernization as map, astronomy, mathematics, dissemination of Chinese philosophy, the influence on learning the Western style of clock, musical instruments and paintings.[77]His amiable personality and profound knowledge attracted many influential officials, such as Li Zhizao, Yang Tianjun, Xu Guangqi, etc. Only four or five years in Peking, Ricci already had more than 200 “disciples” to follow him. “What the Chinese people particularly admire in the scientific work of Matteo Ricci in China is his humble, honest, disinterested attitude, not inspired by ulterior motives and free from bonds with any type of foreign, economic or military power.”[78]
Conclusion
In sum, as Yang Young-ching argues, “he who wants to guide the Chinese must start by understanding them. He who wants to teach the Chinese must first learn what they have already been taught. The beginning of an understanding of the problem of evangelization and the discovery of the best method of giving Christianity to China lies in a careful survey of her spiritual heritage and religious background and a discerning appraisal of its true worth and value.”[79]
Indeed, cultural barriers and situational limitations make cultural accommodation not an option but an imperative, not only for Ricci’s time, but for ours. The success of the Ricci’s method of cultural accommodation in the 16thcentury provides us with some good lessons.
It is possible to have peaceful and meaningful integration and interaction of different religious faiths, cultures and civilizations. This does not presuppose a homogenization in a universal whole, but rather relating each other on the basis of one’s own cultural identity and uniqueness. This can create a unity that is much richer, broader, and inclusive.
As Pope John Paul II stresses, Ricci’s experience with the Chinese people manifests that Christianity “would not bring any damage to Chinese culture, but would enrich it and perfect it….the Christian faith does not in fact imply abandoning one’s culture, nor does it mean diminishing loyalty to one’s own country and its traditions, but rather, that the faith permits them to offer a richer and more qualified service to their country.”[80]
However, there is also a tendency for civilizations to clash in hostility, hatred, and chaos, and a possibility that cultures could constitute walls dividing us in isolation, alienation and confrontation, like the Berlin Wall in the past and the wall between Israel and Palestine at present. If we transform that danger of clash and confrontation into dialogue or cooperation, and if we break the wall into a greater openness, we will have new and positive possibilities for families, societies and civilizations. This grounds a hope for the future of peoples, nations and the globe. A common humanity needs a humane approach with unique experiences and rich resources of each one’s own cultural tradition.
In order to co-exist with each other in a complex world, we need to learn wisdom from exemplary cases past and present. Wisdom is something “classical” which contains the profound meaning of “a consciousness of something enduring, of significance that cannot be lost and is independent of all the circumstances of time,” or “a kind of timeless present that is contemporaneous with every other age.”[81]In order to have a good understanding of the past one needs to create a “fusion of horizons” between now and then, and different religions, cultures and civilizations of many peoples. One must reflect critically upon the pre-judgments and gain critical distance from the prejudices so as to be ready to open for new encounter or new understanding for the future readings and applications, for understanding cultural tradition is an open-ended and progressive“hermeneutical spiral”. Hence, wisdom enables us to read our cultural traditions hermeneutically, rather than in a closed fundamentalist manner.
From the above example of the integration of the two cultures East and West, we have learned that it is possible to co-exist peacefully among peoples who have different cultures, beliefs and convictions, on the one hand; we have also understood that when a foreign culture comes to reside in a new place with a different culture, (1) it should come as a guest rather than a host, and hence should follow certain rules, patterns, customs and traditions of the existing culture so as to prepare itself for the gradual and graceful integration with the existing culture; (2) it should come with humility, sincerity, concern and charitable love in order to share its own gift with the existing culture for the goal of mutual enrichment and complementarity; and (3) it should come with a spirit of discovery to find out and learn from the existing culture its unique way of manifesting the true, the good and the beautiful, and, in turn, to be rediscovered in its own culture, for each culture has its own way of living and expressing the spirit, precisely because we all live under “Heaven.”
略谈西方对“理”的三种解释
——从利玛窦、莱布尼茨到李约瑟
桑靖宇 程悦*
内容提要:利玛窦由于宗教偏见而将理学的“理”误读为“原初物质”,从而使基督教与理学处于对立之中。莱布尼茨从理性神学出发,将“理”等同于基督教的上帝,试图为中西文化的积极交流奠定基础,却难免削足适履。李约瑟抛弃了西方传统的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在西方有机论哲学与理学之间展开了富有成效的对话,为中西文化的融合探索了一条希望之路。
关键词:理 原初物质 单子 有机论
利玛窦等耶稣会士于十六世纪来华传教、积极解释中国文化典籍展开了中西文化对话与交流的波澜壮阔的画面,一直延续至今。然而中西文化具有重大的异质性,相互理解与对话殊非易事。本文试图考察西方对理学的三种重要且有广泛影响的解释,这是由利玛窦开端、由莱布尼茨所深化,最后由李约瑟所达到高峰。这表明,中西文化间的互相理解尽管障碍重重,但经过认真的努力,是可以不断深入且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利玛窦:物质主义的解读
众所周知,利玛窦在华的传教策略是排斥以理学为代表的新儒,而认同于古儒。在《天主实义》第二篇“解释世人何以错认天主”中,利玛窦批评宋明理学的理、太极不能成为“物之主宰”、“万物之原”,其理由可简单地归结为以下几点。
其一,利玛窦从理不能离气独存出发,认为理比物等级要低,不可能为万物之原。他说道:“若太极者,止解之以所谓理,则不能为天地万物之原矣,盖理亦依赖之类,自不能立,曷立他物哉?中国文人学士讲论理者,只谓有二端,或在人心,或在事物。……据此两端,则理固依赖,奚得为物原乎?二者皆物后,而后岂先者之原?”[82]利玛窦从亚里士多德主义的“实体—属性”思维模式出发,认为前者能自立,后者则依附于前者。而太极、理作为不能自立的依赖者,属于“属性”范畴,不可能成为万物的本源,否则将导致重重矛盾:“且其初无一物之先,渠言必有理存焉。夫理在何处?依属何物乎?依赖之情,不能自立。故无自立者以为之托,则依赖者了无矣。”[83]即在他看来,理作为属性尚且不能独存,怎么可能成为万物之源呢?[84]
其二,利玛窦从“理无动静”出发,否认理能产生万物。他说道:“试问盘古之前,既有理在,何故闲空不动而生物乎?其后谁从激之使动?况理本无动静。况自动乎?”[85]即创造属动,无动静之理何以能创造呢?
其三,利玛窦从“理无灵觉”、不“明义”出发,否认理能创造含灵之物。“又问,理者灵觉否?明义否?如灵觉、明义,则属鬼神之类,何谓之太极、谓之理也?如否,则上帝、鬼神、夫人之灵觉由谁得之乎?彼理者,以己之所无,不得施之于物以为之有也。理无灵觉,则不能生灵生觉。”[86]在利玛窦看来,理既然没有知觉(“无灵觉”)、没有思维能力(不“明义”),就意味着它只是混沌、低级之物,不可能产生出高级的生命。
利玛窦在1604年致耶稣会总会长的信中总结说:“我认为这(指太极)完全是我们的哲学家们所说的第一性物质,因为这根本不是一种实体”[87]。所谓“第一性物质”(prime matter)一般译为原初物质,在亚里士多德哲学中(利玛窦的思想背景是亚里士多德—阿奎那主义),是指纯粹被动性的纯质料。太极、天理作为理学的最高价值、终极实在居然被利玛窦解读为消极的原初物质,不能不说这是莫大的误解。
利玛窦之所以产生这种误解的原因显然在于他不能够跳出西方有神论的模式来客观地理解理学,这主要可归结为以下两点:
其一,他的有神论使他不能理解终极实在何以能够“无动静”、“无灵觉”,即在他看来,终极实在只可能是人格神。而传统基督教的上帝是宰治一切而不受影响的绝对力量,这使他无法接受理学崇尚“人能弘道,非道弘人”的“气强理弱”的观念,理学的人本主义宗教观与他的神本主义信仰是难以调和的。
其二,基督教的纯粹外在于世界的上帝观使他不能理解理学乃至中国思想的既超越又内在的特征。当朱熹说“理气不离不杂”时,他强调的正是终极实在的这种二重性。而利玛窦对此无法理解,而只能接受“理不离气”,并因此把太极、天理想象成原初物质。中国思想自古以来就崇尚神圣与世界不可分离的整体主义,理学将作为事物的秩序与价值的“理”设想为凌驾于气之上的终极实在时固然带有某种二元论倾向,从而受到其他学派的批评,但“理气不离”的思想很大程度上仍然保留了中国思想的整体主义的特质。
二、莱布尼茨:唯心论的解读
利玛窦继承者龙华民一方面认同他对对理学的物质主义解读,另一方面则否认古代儒学中存在类似基督教上帝的人格神,从而使儒学成了彻底的唯物主义无神论。这对当时的欧洲思想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马勒布朗士等因此而批评儒学的唯物论,反对儒耶融通,自由思想家们却因儒学的无神论而备受鼓舞。莱布尼茨却另辟蹊径,对理学做了唯心论的解释,认为其与基督教神学是相通的,以期在自然神学的基础上把中国与欧洲联合起来,促进人类的和平与繁盛。
莱布尼茨晚年的《论中国人的自然神学》(1716)一书是他解读以理学为代表的中国思想的经典著作,该书是对龙华民、利安当等人的把中国思想视为是无神论的反通融主义(anti-accommodationism)一个批判性的回应。龙华民、利安当等人认为中国思想中缺乏作为人格神的上帝,“理”、“太极”虽貌似基督教的上帝,但实质上只是原初物质(prime matter)而已,中国人根本就没有精神实体的概念。但莱布尼茨却从他们关于中国思想的引文中看到了类似于他的上帝观念的东西。
莱布尼茨对把“理”视为是原初物质的观点进行了批驳:“据中国人所言,‘理’或‘太极’是最卓越的一(the One par excellence),是无任何杂质的纯善,是最纯粹而美好的存在,是产生天地的法则;它是最高真理,是最强大的自在之力,但又不局限于自身;它为了表现自身而创造万物。它是纯洁、美德和博爱之源。创造万物是它固有的能力,所有的完善都源于它的本质和本性……中国人不可能不陷入自相矛盾之中,如果他们把如此伟大的性质赋予它而又认为它是无能力、无生命、无理智和无智慧。”[88]。 即“理”作为创造、主宰万物的能动性的纯善与经院哲学的纯被动性的原始物质恰恰是截然相反的,倒是类似于基督教的上帝。
莱布尼茨进而指出:“如果中国古典作者否认理或第一原则具有生命、知识和力量,他们无疑是指存在于受造物中的人类特性而言。他们所说的生命是指感官的活力,知识是指通过推理或经验所获得的东西,力量是指君主或官员仅依赖敬畏和期待来管辖下属。”[89]按照他的解释,中国人之所以否认“理”具有生命或力量,是反对将最高实在拟人化,这一思想与伪狄奥尼索斯的“否定神学”是一致的,这并不表示“理”不是能动的精神实体。
反通融主义者的另一个重要理由是,“理”产生万物并不出于意志或计划,而是表现为自然律,万物依照这自然规律而产生、运动,无需外在的干预。例如培尔(Bayle)和马勒布朗士等深受笛卡尔哲学影响的神学意志主义者(theological voluntarianist)认为,如果自然规律是由神的理性所规定的,那么自然就有了某种独立性,神的万能也就受到损害。从而,他们认为,自然界并没有自在的规律,一切都处于神的意志的掌握之中。也正因此,崇尚客观秩序的中国理学思想被培尔、马勒布朗士、龙华民等神学意志主义者视为是斯宾诺莎主义、即无神论的典型。
莱布尼茨宗教哲学崇尚神学理性主义,主张神的意志行为服从于神的理性,极力反对将神的意志凌驾于理性之上的神学意志主义,他认为当时流行的形形色色的神学意志主义只会造成宗教与科学间的对立、加剧教派间的冲突并最终导致欧洲的混乱。他很自然地把“理”通过自然规律产生万物的理学思想引为同道,认为“理”正是他所理解的不干涉的、作为理性秩序的上帝。莱布尼茨是用“可能世界”的理论来调和神的万能与客观的自然规律、神的意志与其理智之间的张力,同样,他也用这种“可能世界”的学说来解释理学思想:“我相信用不着扭曲中国人的古老观念就可以说,理出于自身完善本性的驱动,而从多种可能性中选择了最佳者;由此它创造了具有如此性质的气或物质,以致所有其他一切都从气的自然倾向中衍生出来……因此中国人的事物因其自然倾向和前定和谐而产生的观念,非但不应受谴责反而值得赞扬。”[90]
理学思想中引起莱布尼茨强烈共鸣的不仅仅是通过理性秩序来统御世界的“理”,还有世界的有机性。实际上,早在与来华传教士白晋的通信中(1697-1698),白晋就指出莱布尼茨的物质本质是力的有机论哲学与中国思想有着显著的类似[91]。在《论中国人的自然神学》中,莱布尼茨则直接用他的单子-物质模式来解释理学的理气关系。
在该书第14条莱布尼茨说道:“这位作者[朱熹]很聪明地指出,鬼神不仅仅是气,而是气之力。如果孔子对他的一个学生说鬼神仅仅是气,他指的是有活力的气,并且是因为这位学生的理智能力不能理解精神实体,才因此而因材施教。对希腊人、拉丁人来说,Pneuma和Spiritus意味着空气,那是一种微妙的、有穿透力的物质,被创造的精神实体实则被其所覆盖。同一作者(指朱熹)还提到鬼神即理”[92]。
在此莱布尼茨尽管对理学思想存在着误解——如将理与鬼神等同起来,并将它们都视为是精神实体,但难能可贵的是,他不但反对龙华民、利安当将“理”视为是惰性的原始物质的谬误,而且还进一步觉察到气也非僵死的原始物质,而是“微妙的、有穿透力的”、生机勃勃的东西,类似古代西方人所说的有活力的空气。莱布尼茨之所以能够达到这种理解显然与其自身的有机论哲学观密不可分。在他看来,物质的本质既非是广延,也非是不可分的原子,而是能动的力,物质的力源于与其结合在一起的能动的精神实体——单子。
莱布尼茨认为朱熹的理是类似单子的能动的精神实体,它赋予了气以活力和生机。“(朱熹还认为),事物除了精粗,厚薄之外,并无其他差别。他想说的,显然并非理或鬼神是物质性的,而是这些物质为鬼神所赋予生机,那些与不那么粗糙、不那么厚重的物质结合在一起的(理或精神实体)就更为完善了。……个别的理是那伟大的理的(比照着他们躯体的)不同完美程度的散射(emanation)。因而事物的不同与他们物质的微妙性与粗重程度成比例,因为理本身与它们(指理所依附的物质)相对应”[93]。莱布尼茨从朱熹的理气不离以及事物因气的清浊、厚薄不同而不同中再次看到了他自己的哲学。莱氏认为,除了作为最高单子的上帝之外,任何被创造的单子都因不同程度的模糊的知觉而与相应的物质躯体相伴随,越高级的单子的物质躯体越精细。正是这种心物不离的有机论哲学观使得莱布尼茨得以克服笛卡尔的心物二元论及其僵死的物质观,使得物质得以分享了精神的活力和生机。
值得一提的是,莱布尼茨认为中国思想与西方基督教(他的哲学是其最高典范)的汇通使中国与欧洲可以结成伟大的文化共同体,他热情地指出:“人类最伟大的文明与最高雅的文化今天终于汇集在了我们大陆的两端,即欧洲和位于地球另一端的——如同‘东方欧洲’的中国。我认为这是命运之神独一无二的决定。也许天意注定如此安排,其目的就是当这两个文明程度最高和相隔最远的民族携起手来的时候,也会把它们之间的所有民族都带入一种更合乎理性的生活”[94]。莱布尼茨尤其对中国的道德伦理和政治哲学推崇备至,他说道:“鉴于我们目前面对的空前的道德没落状况,似乎有必要请中国的传教士到欧洲给我们传授如何应用和实践自然神学,就像我们的传教士向他们传授启示神学一样”[95]。
莱布尼茨对理学的唯心主义解释显然比利玛窦、龙华民等人的物质主义解释深入得多,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莱布尼茨的宗教哲学推崇理性精神淡化宗教信仰,与儒学确有不少相似之处。他的理性神学反对意志主义的随时干涉世界的人格神,主张理性秩序统御一切,这与理学的永恒天理确实具有相通性。他的不干涉的上帝在创世之初赋予自然万物以自发性和完善性,使万物依据自身的内在原则不断地活动、发展,相比于传统基督教思想,这更接近理学的世界观。
但莱布尼茨并未能摆脱传统基督教的外在超越的实体主义上帝观,这使他不能接受“理在气中”的整体主义(例如,他极力反对把“理”解释为世界灵魂)。他的单子论试图克服笛卡尔的心物二元论,但在单子与物质之间仍存在着实在与现象的鸿沟,这种精神与物质的两层化使他在与理学认同时误读了理学的心物连续性。
三、李约瑟:有机论的解读
对于理学利玛窦和莱布尼茨提出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解释:唯物论与唯心论。它们固然不乏自身的理由,但都具有浓厚的“格义”色彩,具有强烈的把西方思想植入儒学文本的意味,从而扭曲了其本义。对于习惯于西方传统思维的人而言,唯物论与唯心论似乎穷尽了哲学思维,理学要么就是唯物论,要么就是唯心论,深受西方思维影响的现代中国人在解释理学时也很容易陷入这种非此即彼的解释模式中。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其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二卷中则根据他所信奉的怀特海整合心物的有机论哲学(或过程哲学),富有创意地提出了解释理学的第三种模式。
李约瑟以辉煌巨著《中国科技史》闻名于世,他精深的哲学素养和极富创造性的跨文化视野却往往为人所忽视,这是很遗憾的。他之所以放弃前程似锦的生物化学研究而转向中国科技史这片充满荆棘的处女地,这与他独特的哲学理念密不可分。在《四海之内》一书中他对西方传统世界观进行了无情批判,并力图在中国思想中寻求治疗:“自其思想历史发端以来,欧洲人的世界观就经常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而很少能够综合起来。一方面是为天使、幽灵、造物主们(demiurges)、隐得来希之类的超自然的群体所簇拥的上帝和众神,另一方面则是原子和虚空。神学唯灵主义和机械唯物主义进行着永恒的战争……在莱布尼茨之前尚无任何严肃的尝试来调和这种对立,只有到了当代这种尝试才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中国文明从未介入到这种思想的分裂。有机的自然主义是中国的永恒哲学。从根本而言,任何形式的超自然的东西对于无论是儒家还是道家都从未有过任何用处,但原子的机械的交互作用也不为他们所欣赏……当中国思想在12世纪的理学中得到最完美的表现的时候,其表现形式与现代科学的普遍的世界观有着惊人的类似。对于宇宙的构建而言,除了物质-能量和(有着无数级别的复杂性的)组织之外,无需更多。”[96]即西方文化饱受灵肉对立、唯灵论与机械论的斗争之苦,直到以怀特海集大成的有机论哲学才较好地克服了这一症结。而以有机自然主义为特征的中国思想则从未陷入这种困境之中,朱熹理学则是中国有机论思想的最好的体现。
李约瑟明锐地觉察到,在中国并未发生西方那种心与物、神圣与世俗的二元对立,世界被感受为一个生机盎然的整体,其中每一个体都与整体密切关联,彼此间自发地和谐呼应:“它是这样一个宇宙,其中这一组织之所以产生,既不是因为有一个最高的创造者-立法者所颁发的、由侍从天使们所实施的而一切事物都必须遵守的命令;也不是因为无数弹子球的物理碰撞,其中一个球的运动是推动另一个球的物理原因。它是一种没有命令者的各种意志的有秩序的和谐;它就像乡村舞蹈的舞者们的自发而有序的(在有模式的这种意义上)的活动一样,他们当中没有人是受律法的支配去做他们所做的,也不是被后面的人所推挤而动,而是在一种自愿的意志和谐中进行合作。”[97]
在这种中国有机论思想的大框架之下,李约瑟对朱熹的“理气”观念进行了深入的阐释。首先他反对了流行的把理气等同于心灵、物质的解读(莱布尼茨是发端者),因为朱熹本人明确把心视为是精微的气,而西方的物质则类似于他所说的“质”,即粗糙的气或气之渣滓。李约瑟把“气”解释为“物质-能量”[98],这种物质-能量在其高级状态中表现为心灵。西方的那种心物对立的观念完全不适合朱熹理学的有机论哲学。
另一种流行的解释是把理气等同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形式-质料,这实际上是前一种解释的变种。李约瑟指出:
“固然形式是个体化的要素,使有机体产生了统一性和目的,理也是如此。但相同点也就到此为止。身体的形式是灵魂,但中国哲学的伟大传统却没有灵魂的位置……理的特殊重要性在于它本质上并非类似灵魂或有生气。再者,亚里士多德的形式实际上赋予事物以实体性,……但气却非理所产生,理只具有逻辑上的优先性。气在任何方面都不依赖于理。形式是事物的‘本质’或‘首要实体’,但理自身却非实质性的(substantial),也不是任何种类的气。理并不比气更真实,但也并非是虚幻或主观的,气也并非是潜在的理,就如质料是潜在的形式。尽管理通常被称作‘形而上’,但我并不认为它像柏拉图的理念或亚里士多德的形式那样,具有严格意义上的形而上性质,不如说它是存在于自然界所有层面的不可见的组织场或组织力量(organising fields or forces)。纯粹的形式和纯粹的现实是神,但在理气的世界里没有任何的主宰。”[99]
在他看来,理作为组织或组织原则是作为有机体的世界的秩序或模式,这与西方的法则(Law)是不同的,西方的法则总是预设了外在的立法者,而理却是事物自发的和谐秩序,就像乡村舞蹈一样彼此呼应。作为秩序的理源于个体(部分)与整体的密不可分的有机关系以及由此而来的个体间的相互协调。“部分最重要的事情是它们需要与其他部分一起在由其构成的整个有机体中精确地各居其位,而没有如陈淳(朱熹弟子,著有《北溪字义》)所说的最微小的过度和不足。”(p.567)西方传统有神论认为秩序和法则源于外在的人格神,物质主义的机械论则把法则归结为原子盲目碰撞所表现出的统计结果,这两者实际上都预设了一个僵死的、孤立的世界,而中国思想则把世界视为是生机盎然的、密切关联的有机整体,它的各层面的活生生的关联和秩序就是理。这与西方的主流观念是大异其趣的。
李约瑟对朱熹理学的解释排除了理学与西方传统的外在超越的有神论的类比,但这并不意味着朱熹理学中没有宗教色彩,这可以从消极和积极的两方面进行了说明。消极地说,理曾被佛教华严宗用来指称“真如”或终极实在,朱熹并没有完全摆脱华严宗的这种把理实在化、绝对化的作法,从而存在着传统实体主义宗教形而上学的残余。[100]另外,李约瑟对朱熹的理相对于气的逻辑在先的观念颇为不满,认为理气二元论具有通向外在有神论的可能性。[101]显然,李约瑟更赞同王夫之、戴震的离气无理的一元论思想。
积极地说,朱熹理学整体上看是排斥西方传统那种外在超越的有神论的,但却肯定某种内在的神圣性,李约瑟引用了朱熹的下面这句话来加以简要提示:“神也者,妙万物而言者也。盈天地间皆神。”即世界作为生机盎然的有机体本身就具有某种神圣性,而无需外在超越的人格神。
值得说明的是,李约瑟本人虽然不信仰传统基督教的超自然的人格神,却具有着强烈的宗教情操,信奉博爱、社会进步的道德宗教,以求克服人世间的种种罪恶和苦难。这也是朱熹理学引起他强烈共鸣的原因吧。正是在这种博大的宗教精神推动下,李约瑟以惊人的毅力和创造性主持写作了卷幅浩瀚的《中国科学技术史》这一伟大工作,为中西文化交流建立了丰碑。
结语
利玛窦的理学解读虽然开风气之先,使西方世界首次接触到了遥远中国的理学思想,却因强烈的宗教偏见而将“理”误解为“原初物质”;莱布尼茨则从博大的和谐精神出发,将理学与他的唯心论哲学融为一炉,虽然失之偏颇,却初步架起了中西文化互相理解、对话的桥梁,因而影响甚大;李约瑟则深入把握了中西文化的差异,依托西方新兴的有机论哲学对朱熹理学进行了前所未有的深刻阐发。尽管他的解释并非完美,却打开了理学与西方思想对话的新视角,为中西文化对话与交流开辟了崭新的道路,具有重大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利玛窦的抉择
方永[102]
内容提要:耶稣会士利玛窦抱着使中国基督教化的理想来到中国,基于所面对的现实,选择了合理的传教策略:一是和平传教,而非武力传教;二是在服装上,依据对中国宗教状况与社会状况的判断,最先选择的是僧服,而后改易儒服,最后决定穿术士服;三是在中国活动的身份,也由僧而儒,最后以术士安身,而没有展示其传教士的身份;四是在宣教对象的选择上,没有采纳直接向上层文化人士直接宣教的方略,而是选择了在当时社会中处于边缘的人,或是贫无立锥之地之人,或是无依无靠的病人,或是经历坎坷的商人、武夫与士绅。这样的选择是明智的,因为它真实地反映了当时西来的基督宗教在中国可能的生存之道:唯有适应,在适应中调整待变。
关键词:利玛窦 基督教 传教策略 术士 边缘人
耶稣会传教士来到中国,其根本目的在于让中国人信仰天主教,使中国基督教化或福音化。这个根本目的,就是其理想;而理想的实现,却必须诉诸合适的手段,而何谓合适的手段,则不仅取决于理想,而且取决于现实的形势,而且后者的重要性一点也不亚于前者。
耶稣会士到中国来传教,属于外方传教。对于外方传教,耶稣会的创立者罗耀拉特别强调“老练谨慎”即“高明的灵活”。他写道:“‘老练谨慎加上一点纯洁’比‘尽善尽美的纯属洁加上不高明的灵活’要好得多!”[103]何谓灵活,则完全取决于形势;而体现这种灵活的,则是在关键问题上所作的抉择。罗耀拉看到其他修会借助军事暴力传教所导致的失败,指示其弟子在传教中应“适应当地的习俗”,这便是著名的“适应”策略。
作为耶稣会士来到中国的利玛窦,遵守中国政府的管理,对基于中国传统而以儒家礼仪表现出来的祭祖祀孔的习俗所取的宽容态度,后来被康熙称之为“利玛窦规矩”,成为康熙之后直到鸦片战争这段时间来华传教士欲合法留居中国就必须遵守的原则,这在相当程度上说明了他的传教策略,就使天主教进入中国而言是基本成功的。笔者在此无意对“利玛窦规矩”加以分析,而只想说明利玛窦在中国传教策略之所以就使天主教进入中国而言是基本成功的,是因为他在面对中国的形势时,基于他自己的观察,在几个关键的问题上作出的抉择,不但现实,而且富有针对性,效果还相当好,因而是极为正确的。它们,构成了“利玛窦规矩”的真正基础。
一、是和平传教,还是武力传教?
1582年,耶稣会会士利玛窦来到澳门。此时,西班牙已经把邻近中国的菲律宾群岛变成自己的殖民地。在菲律宾的耶稣会士,在西班牙殖民当局的支持下,在当地以武力的手段强行传播天主教。就在这一年,从马尼拉辗转到澳门的西班牙籍的教耶稣会士桑切斯(Alonso Sanchez)极力主张以武力征服中国来传播天主教。据说,罗明坚和利玛窦起初很想与桑切斯合作,但遭到葡萄牙人的反对而作罢。[104]
葡萄牙人为什么反对在中国武力传教呢?原因很简单,因为当时的葡萄牙人根本没有力量在军事上与中国抗衡。中国人与倭寇的战斗中显示出来的战斗力,是葡萄牙人不得不考虑的。而且,葡萄牙殖民者与明朝水师在东南沿海进行的三次战斗,均以惨败告终,这使他们认识到中国力量的不可小视。1556年,葡萄牙人通过行贿获得在澳门的居留权,并于1572年开始公开向中国政府交纳地租,获得有限的自治权。这有限的自治权是以接受中国地方官员的管辖和交纳地租为前提,而且,对在澳门的华人没有管辖权。面对桑彻斯的征服中国的叫嚣,葡萄牙人深知其难成,一旦付诸实施,好不容易获得的在澳门的居留权也会丧失。这是葡萄牙人所不愿意看到的。而罗明坚和利玛窦所属的耶稣会分会的支持者是葡萄牙。所以,由于桑切斯坚持武力传教,罗明坚和利玛窦只好完全避开他。
因此,从内心里讲,罗明坚和利玛窦其实并不拒绝武力传教,只是不接受对中国武力传教。他们之所以不接受对中国武力传教,首先在于他们的分会的资助者是葡萄牙人,而葡萄牙人是深知当时中国力量的强大的。而且,葡萄牙国小力弱,不希望西班牙人染指自己的事业,尤其是干损害其利益的事情。面对这样的现实,以葡萄牙人为资助者的罗明坚和利玛窦拒绝了耶稣会内部、特别是西班牙籍耶稣会士“一手拿剑,一手拿十字架”的武力传教呼声。葡萄牙人的现实主义,决定了为他们所资助的那部分耶稣会士的对中国传教的策略选择上的现实主义,使他们像葡萄牙人获得留居澳门的权利一样,采取和平渗透的策略,而没有采用武力征服的策略。
事实证明,西班牙籍耶稣会士桑切斯的对中国武力传教的策略是难以成功实施的。桑切斯1586年作为西班牙在菲利宾的殖民当局的全权代表怀揣一份题为《论征服中国》的备忘录回到马德里呈交给国王菲利浦二世,正式推出“征服中国”的新十字军方案;但是,由于欧洲新教国家与天主教国家之间的斗争,1588年西班牙倾尽国力而建造的“无敌舰队”被英国海军全歼,尼德兰革命也使西班牙焦头烂额,这一方案终究化为泡影。可是,西班牙在菲利宾的殖民当局并没有因此死心,他们组织的军队攻占明军曾设防的基隆和淡水,占据北台湾,开始其在中国土地上的武力传教。不过,他们在北台湾的活动,因为被新到的荷兰殖民者击败而告终。此后荷兰的殖民者又被郑成功击败,新教在中国武力传教的开端也被扼止。
可以说,基于对中国的了解和对自身力量的判断,罗明坚和利玛窦以及他们所依靠的葡萄牙人,拒绝接受西班牙籍耶稣会会士桑切斯的武力传教策略,这是相当明智的。这种明智,是基于葡萄牙人从1514年到1572年期间超过半个世纪与中国进行的包括军事在内的斗争中所获得的经验和教训。这些经验和教训的中心内容是:与欧洲相比,中国的国土庞大,物产丰富,文明古老而成熟,人民爱好和平但又经得起长久而残酷的战争。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是通商获利,还是传教牧灵,在当时的情况下,诉诸武力必然遭受失败,所以,应当以和平的方式,利用中国人的性格特征和制度缺陷来求得成功。
大约在1583年利玛窦入肇庆前夕,利玛窦发了终身愿,表示愿意以身殉教。对此,桑切斯认为,传教单靠劝说无济于事,由此招致猜忌而被杀是活该,因为殉教本身并不是目的,“应该借助世俗力量,使用军人的武力和其他现世的手段”。有鉴于此,利玛窦只好与他绝交。朱维铮认为,“利玛窦与桑彻斯绝交,只能表明他信守誓愿,不肯被世俗权力牵着鼻子走,依然以为信徒的虔诚必须依靠教士的殉教精神和善诱善导来培植。”[105]
笔者认为,这种看法有抬高利玛窦的品格之嫌。因为当时耶稣会的宗旨,并不是要与世俗权力脱离干系,否则耶稣会在各地传教也不会都走上层路线了。极有可能的是,利玛窦与桑切斯绝交,也是策略性的,而不是原则性的。因为在澳门,与一个鼓吹征服中国的西班牙籍耶稣会士保持交往,难免不传入在澳门的华人之耳。为了进入中国内地,利玛窦必须制造自己对华的友好形象,而制造这种形象的最好办法,就是与鼓吹与华为敌的西班牙籍耶稣会士绝交。而且,利玛窦与桑彻斯的绝交行为,就发生在他前往肇庆前夕,这种时间上的巧合,很难说是偶然的。再者,既然已经表示愿以身殉教,那么,就必然已经下了壮士一去不复返的决定,而桑彻斯是不可能前往中国内地的,因此,利玛窦动身前往肇庆之时,也便是他与桑彻斯的交往结束之时,即便不绝交,恐怕也没有机会面见了。显然,这种绝交,可能除了由于在对中国传教是用和平方式还是用武力方式上发生的分歧之外,还有实际上策略的考虑。因为毕竟他们都是耶稣会士,都必须服从总会的领导,因而他们之间的分歧,都不是原则性的,而是策略性的。而耶稣会士,为了实现目的,手段一向都是灵活的。罗明坚因为在肇庆建立居所的经费不足而于1583年12月回澳门筹款不顺时,为了解决经典问题,还与一年前接触过的西班牙籍耶稣会士桑切斯重新取得联系,呼呈西班牙人为在中国的和平传教伸出援手。这件事,从某种程度上说明,利玛窦与桑切斯绝交,不是原则性的,而是策略性的。因为作为罗明坚之助手的利玛窦与桑切斯绝交,不经过罗明坚,肯定是难以想象的。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罗明坚于1588年11月启程返回欧洲,再也没有机会回来,其中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他与桑切斯过从甚密,尤其是1584年罗明坚在澳门寻求经济援助时与桑切斯接触,相谈甚欢,而桑切斯希望在西班牙国王打算筹备的访华使团上寻求在华耶稣会士的帮助,条件是将给在华耶稣会传教团一架自鸣钟并支付所需费用,这使受到桑切斯强烈批判的耶稣会远东负责人范礼安强烈不满,于是便借筹组教皇访华使团的名义把罗明坚打回欧洲。这件事,反映出罗明坚在和平传教与武力传教的策略选择上的摇摆。利玛窦却没有这种策略选择上的摇摆,他是范礼安和平传教策略的坚定拥护者。正是因为这样,在罗明坚离开中国后,利玛窦成为耶稣会在华传教团的实际负责人,并在不久得到正式的任命。
二、僧服,儒服,还是术士服?
利玛窦在1583年9月10日,随着罗明坚进入当时广东的省城肇庆。在这里,就着装问题,他与他的直接上司罗明坚发生了分歧,其内容就是着装问题;应当身着僧服,还是身着儒服,或是其他的服饰。
利玛窦是以罗明坚的助手的身份进入广东肇庆的,当然要服从罗明坚的领导,这是耶稣会的体制所决定的。因此,在着装问题上,他依从罗明坚的旧例。这一旧例是罗明坚于1582年12月27日第一次到肇庆时所形成的。在1582年12月30日拜见当时的两广总督陈瑞时,由于罗明坚自称“天竺僧”,陈瑞便赐给他们中国和尚的信服,并把他们安排在肇庆东门外的天宁寺居住。起初,罗明坚并没有穿上中国和尚的服装,但是,在陈瑞的建议下,罗明坚及其副手巴范济穿上了中国和尚的服装,并且在致总会长的函中说了这样一名名言:“总而言之,我们扮作中国人,以便为天主赢得中国人。”着僧服的旧例就这样由罗明坚开创了。
客观地讲,罗明坚是说了谎的,因为他固然来自天竺,但天竺不是他的家乡,而只是他传教生涯中的一个落脚点。他刻意隐瞒了他在到天竺之前的来处,隐瞒了他的欧洲背景。这个谎言在罗明坚带着利玛窦到肇庆见知府王泮时,不但在重复,而且还扩大。他隐瞒了自己到中国的真实目的,说“是天竺僧,来自天竺国,因慕中华之盛,航海三四年来到中国”,“只想远离澳门的商业世界,一心供奉天主,但愿在肇庆建立一个寓所和教堂,终老此地”,“希望知府大人开恩,他们在肇庆不惹是生非,不求施舍,并将终身感恩”。这其中,除了“一生供奉天主”和“愿在肇庆建立一个寓所和教堂”之外,其他都是谎言。首先,他们不是天竺人;其次,他们不是僧;其三,他们不是因慕中华之盛而来;第四,他们根本没有也不可能切断自己与澳门商业世界的联系,根本不可能远离澳门的世俗的商业世界;第五,他们终身所感恩的,不是这位知府,而是天主。总之,为了达到立足传教的目的,什么谎言都是无关紧要的。
不过,既然已经公开声明自己是天竺僧,而且当地的官方也认为他们是天竺僧,他们便只好自己来圆谎了,尽管这带着某种不大情愿,但为了目的的实现,在策略上也只好如此了。圆谎的最好办法,便是穿上当地官员所赐给的中国和尚服。而且,罗明坚的这一做法,得到了其直接的上司范礼安的认可。1588年10月11日,范礼安在写给总会长的函中特别解释说,中国欣赏天竺国,而且他们不知也不认其他国家,所以传教士须使用“天竺僧”的名称,并特别强调:“用这种方式,只有用这种方式,他们才能进入中国。”[106]
这种方式,就是“借名”。可是,罗明坚的助手利玛窦经过细心的观察却发现,罗明坚这次借名并不高明,甚至有些愚蠢,因为他所借的名,不大受中国人尊重。
罗明坚之所以自称天竺僧,是因为他认为中国社会的本土教士是佛僧,而佛僧最初来自天竺,他以为自称为僧可以适合中国的民情,不致引起中国士大夫的反感。但是,来到肇庆不久,利玛窦便发现中国士大夫对佛僧没有一点敬意,而通过科举考试进入国家统治机构的士大夫,才是最受社会尊敬的阶层。那些从官场上退下来回到家乡的乡绅,在社会上也倍受尊重。所以,利玛窦觉得以佛僧自称是不明智的,应当尽力去接近的中国人士不是佛僧,而是读书人,尤其是进入了统治阶层的士大夫。为此,利玛窦与罗明坚发生了分歧。罗明坚认为佛教才是天主教与中国文化最有前途的结合点,对中国官员赐予的僧服从未产生过改换的念头。利玛窦认为儒学是天主教与中国文化最有前途的结合点,因此他向他和罗明坚的上司范礼安请求脱下僧服,换上儒服,并召回与他有分歧而且行动“莽撞”的罗明坚。
罗明坚在1588年11月就被召回了,而易服的批准,却足足等了六年。据宋黎明先生的研究,范礼安在1594年秋才批准在华耶稣会士易服改名,那时利玛窦在广东韶州,公开放弃和尚称谓而让随从称他为“先生”,同时他头上也戴上了一顶高帽,既非僧帽,也非东坡巾,而是方巾,这说明利玛窦试图扮演“儒士”的角色。但是,在1595年春,利玛窦出韶州的时候,他戴的不是方巾,而是东坡巾。这说明他的新身份已经是居士和术士,因为居士与术士的通常打扮就是直裰加东坡巾。这是1595年出韶州后的利玛窦,一直是穿戴直裰和东坡巾。
宋黎明先生认为,这表明,“利玛窦的易服改名实际上有两次,一次是在1594年秋,另一次是在1595年春”。[107]这两次易服改名说明,利玛窦实地上采取了佛教初到中国时所采取的策略,即在面对占统治地位的儒学时,既要与儒学接近,又要与儒学区隔,以便在儒学统治的区域中寻找不满当时儒学状况的同道。所以,正如最初进入中国内地的佛教僧人首先以术士的面目出现一样,最初进入中国内在的耶稣会传教士也首先以术士的面目出现。之所以这样,正如利玛窦在其“中国杞记”中所说,是因为中国人非常迷信,外来的宗教要想在中国立足,没有不充分利用中国人的这一突出的缺点的。
再者,着什么装,是公开表明自己身份的最好方式之一。罗明坚主张着僧装,公开表明他认同佛教,虽然他实际上并不认同;同样,利玛窦主张着儒服,公开表明他认同儒学,虽然他实际上也不真正认同。既然公开表示认同而实际上却不认同,这中间存在着一种张力和矛盾,到了一定条件下它一定会爆发出来,给实行这种公开表明认同但却实际上不认同的策略予以一种毁灭性的打击。这是明智的策略者不能不想到的。为了避免这种毁灭性打击的出现,最好的办法是寻找一种替代性的策略,这种替代性的策略必须是模糊的,便于行事者规避可能最坏的结果。利玛窦在离开韶州时,不再穿标准的儒服,而穿充满模糊性的术士和居士服,可能就有这种考量。宋黎明在《神父的新装》一书中指出:“为什么利玛窦不做儒士而做居士和术士呢?主要原因有两个。首先,如果以儒士身份出现,不但意味着彻底放弃传播天主教,而且与中国文人打交道时只能以学生自居,这对中国人将失去吸引力;相反,以道人面目出现,则给我以很大的想象空间,特别是‘数学’和方术是利玛窦对中国人最具吸引力所在。其次,和尚变成居士相对容易,变成儒士则非常困难,因为当地人不予认同。”[108]
实际上,耶稣会会士从骨子里是反儒的,这在利玛窦也不例外。对于儒学,利玛窦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采取的政策是敌视。这一点,与利玛窦有过相当交往的李贽看得很清楚,他在《与友人书》中透露,利玛窦“欲以其所学易吾周孔之学”。[109]他看出,利玛窦虽然自称“褒儒贬佛”,但其骨子里是反儒的。骨子反儒的利玛窦,在穿儒服称儒生的短短半年之后,就改穿术士和居士的服装,其中的深意是值得认真思考的。至少,在利玛窦看来,在笃信迷信的中国,术士可能是比儒生更为欢迎和尊重的人。尤其是当时的万历皇帝之下,东林党人受压,儒生的日子其实并不好过。相比之下,术士却是大行其道。聪明的利玛窦不会不注意到这一点,并善加利用的。而且,装成术士,这一模糊的身份,更有利于利玛窦游于中国的各阶层人员之间,而不受某一阶层身份的局限,这是佛僧的身份和儒生的身份都无法向他提供的,只有士术这一身份才能给他提供这样的方便。正是这种术士身份,使他从广东阶段的隔绝“中国社会之外”,一下子打入中国的主流社会。[110](李零:《中国方术续考》,第17页。)
三、术士,还是传教士?
耶稣会士进入中国,用积极的话说,是用礼物开路的;用消极的话说,是用行贿开路的;用宗教性的术语说,是用高级方术来开路的。正如李零所说:“研究利玛窦的‘业绩’,一有点值得很注意,这就是在他对儒家网开一面,专攻释、道的谋略之中,欧洲科学是起了关键作用。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科学是真宗教的直接帮手’。他最看不起的就是道教和道教方士。科学优越于方士因而能取代方士是对我们文化的致命打击。”[111]
不过,在明末,最吸引中国人的,是一种名叫黄白之术的炼丹术,也就是把水银变成白银。《儒林外史》中就描述了这种狂热。当初,耶稣会传教士到肇庆时,既不接受中国官方的钱物,也不接受中国民间人士的馈赠,也不华缘,却出手大方。这使一般的中国人对于他们的钱财的来源有一种非常神秘的看法,纷纷传说他们会黄白之术。这种传说,既使他们受难,也使他们受益。因为为了得到黄白之术,中国人想方设法接近他们而又逼迫他们,驱赶他们却又不允许他们离境,这其中既包括两广总督刘继文,也包括浪荡文人瞿太素。三棱镜之所以在中国得到异常的关注,就与传说中的黄白之术有关。
可以说,方术,是耶稣会士最吸引中国人的地方,也是耶稣会士送给中国人的最大礼物。
耶稣会士所用的礼物,除了真金白银,就是低端的西洋奇物以及高端的科学技术。低端的西洋奇物,是为了吸引好奇而贪婪的中国人,特别是官员,其中最典型的是三样:三棱镜、日晷、自鸣钟。高端的科学技术,是为了吸引不仅好奇而且好学求真的中国人而准备的(当然,这些人多是儒生中的“异端”),其中最典型的是记忆术、推理术(几何)、测量术以及其他实用技术(水法、铸炮法)。
客观地讲,低端的西洋奇物,名曰送礼,其实是用来行贿,以求官员开方便之门。比如,利玛窦认为,两广总督陈瑞之所以颁发文书允许罗明坚在中国内地安家落书,就与罗明坚答应日后见面时将送给陈瑞一架自鸣钟有关。利玛窦将陈瑞描述成一个残酷而贪财的人,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因为陈瑞对罗明坚答应日后见面送给他的自鸣钟表现出强烈的兴趣,因而写信希望罗明坚尽快前去,并将颁文允准罗明坚在中国内地安家落户。而在陈瑞离任后的接任者郭应聘之所以与澳门当局交往,其主要动机是为京城采购宫廷所需西洋物品;允许耶稣会士定居肇庆,在相当程度上是要总督府旁边设立一个澳门采购办事处。两广总督采办宫廷所需西洋物品,其中有相当部分是澳门的葡萄牙商人为保住这块居留地以及到广州进行贸易而赠送的,而且,其中不少进了官员的私囊。耶稣会士非常巧妙地利用了这个机会,而使这样的机会得以紧紧抓住的东西,便是他们献上的西洋奇物。肇庆知府王泮因为孟三德赠给他梦寐以求的三棱镜而改变注意,私下同意孟三德居留肇庆。而最终使利玛窦得以进入北京并得以居留北京的,就是他以贡品的名义献给万历皇帝的自鸣钟。
三棱镜和自鸣钟固然是神奇的,但背后的道理则是更为神奇的。前者的神奇,吸引的是爱好器物的官员和皇帝,利玛窦对这些人的基本评价是贪;后者的神奇,吸引的是爱好道理的好学之士,利玛窦对他们的基本评价是智。对于前一种人,利玛窦的基本态度是纯粹利用,当然也不排除诱之以利的劝诱皈依;对于后一种人,利玛窦的基本态度是劝诱皈依,主要是诱之以理,当然也不排除把他们当成工具来使用,因为在基督徒的眼中,每一基督徒都是基督的肢体,都是基督的器皿。
但是,无论是诱之以利,还是诱之以理,利玛窦在中国的传教实践,都基本上以方术的形式出现,至少在中国人看来是这样。
孙尚扬教授在《利玛窦与徐光启》一书中指出:“初来中国时,利玛窦发现最能引起中国人兴趣的并非基教的‘福音书’,而是西方科学技术。1594年11月4日,在写给罗马耶稣会总长的信中,利玛窦列举了中国人访问其住所的五个原因:其一,他是从欧洲来的外国人;其二,他有惊人的记忆力;其三,瞿太素到处宣扬他是位大数学家;其四,他带来了一些东西,如棱镜、地球仪、浑天仪、世界地图;其五,最后的原因才是想听教会的道理,并与之交换意见,但因这个原因拜访他的人最少。可见其中实质性的原因乃是利氏向中人展示的西方科学技术。”[112]而在当时的中国人的观念中,科学技术之类的东西,都是方术,而且,最能体现它们的是道教的方术出现的民间方术以及以星象历数之学出现的官方的方术。
利玛窦最初使中国人震惊的,是他展示的世界地图。在中国人看来,如果没有相当的法力,人很难看清世界到底有多大。中国人的惊异,就在于利玛窦能够展示出这样的东西,这说明他是具有相当的神通的,深知中国人心理和习俗的利玛窦也以此自况,因为这能够赢得中国人的尊重。在与中国人的日常交往中,利玛窦经常以手制日昝作为礼物送人,这同样说明他有相当高的技能,尤其是在观察天象方面,而中国人对于能够观察天象的人,也是相当敬重的,这样的人同样也属于术士,术士所具有的种种能力,就是中国人所说的方术。在利玛窦的中国经历中,最具有戏剧性的因素就是他修理自鸣钟的能力。正是这种能力,使得万历皇帝默许他居留北京,使得他日后成为中国钟表业的祖师爷,被中国的钟表匠人尊称为“利玛窦菩萨”。
利玛窦1595年曾在南昌向中国人展示他的记忆法。史景迁在《利玛窦的记忆之宫:当西方遇到东方》一书中写道:“利玛窦在中国的经历表明,中国人曾臆断他的记忆法源于魔力。1596年10月13日,利玛窦在南昌给罗马的耶稣会会长阿夸维瓦写了一封信。在信中,他先是叙述了为获准定居南昌和购买住所而展开的艰辛谈判,随后又描述了蜂拥到他房间以表祝贺的知名中国文人的情况。他罗列了这些中国人造访的三个主要动机:相信耶稣会士能将水银变为纯银;渴望学习西方数学;急于了解他的记忆法体系。”[113]在笔者看来,这三个主要的动机,其基本内容都是寻求真术。显然,来访者主要是把利玛窦当成高明的术士来对待的。而且,利玛窦对此也心领神会,非常充分地加以利用。
当然,最使利玛窦上心的,还是那些被中国学人认为是实学而加以接受的“天学”。当然,在利玛窦看来,“天学”的主要内容是至公至真的天主教义,而在亲近利玛窦的中国士大夫看来,“天学”的主要内容,一是道德说教,二是可以用经经世致用的科学技术。但由于在对佛教和道教的批判上,利玛窦与倡导实学的中国士大夫站在同一条战线上,用儒家的语词来表达自己的思想,故使得其中的部分士大夫以为利玛窦的“天学”为实学并为之辩护。其实,在“天学”中,真正令中国士大夫动心的,既不是至公至真的天主教义,也不是其中的道德说教,而是其中的科学技术,即当时中国人眼中的方术。尽管利玛窦只是把科学技术当成传教的工具,但是,这工具是十分有效的。肇庆知府因为利玛窦挂在墙上的有外文标注的世界地图产生极大兴趣而给其提供了极大方便,曾自制过地图的李之藻因为在北京见到由利玛窦出版的中文版的世界地图而接受其中的历史观并成为以他为代表的耶稣会传教士的密切朋友并最终受洗入教。徐光启也是因为1595年在韶州见到利玛窦的世界地图而产生要会见利玛窦这位异域奇人的冲动,并于1600年在南京与利玛窦相见,为利玛窦学识所折服,并于1603年在南京中那座由利玛窦建立起来的教堂中受洗入教。虽然“入教事天可能在获得历算奇器等科学知识方面得到便利”,不是徐光启受洗入教的唯一动机,但至少这是其中的主要动机之一。[114]
不过,在骨子里,利玛窦是不想让中国人把他看成一个术士的。他真正想要的,是中国人把他当成神学家。因为,利玛窦明白自己的真正身份是传教士,其主要任务是传播天主教,科学技术只是其传教的工具。在这种工具已经实现所要达到的目的时,这工具便可以被弃置一旁了。这典型地表现在他与徐光启合作翻译《几何原本》这一著作的态度上。《几何原本》的翻译,始于1605年,利玛窦说,这是项“乍看起来与传教并没有直接关系,但实际上对传教非常有利的工作”。[115]经过一年的努力,译完前六卷,徐光启想一口气把后面的六卷一并翻译完,但利玛窦认为不必急。他对徐光启说:“止,请先传此,请同志者习之,果以为用也,而后计其余。”而真实的原因则是:利玛窦认为已经达到了目的,当然可以不竟而止了。孙尚扬认为,“这目的大约是以数学真理向中国人表明天主教是‘理性的宗教’,即是在逻辑推理的基础上建立的宗教。”[116]这说明,科学在利玛窦的传教活动中只是策略性的。而且,利玛窦在实用这一策略时,曾与其上司发生分歧,被批评在传播科学上走得太远,有以手段为目的之嫌。利玛窦之所以在翻译《几何原本》不竟而止,与他受到的这种批评不无关系。我们应当明白,在这种批评的背后,隐涵着一种意见:利玛窦可能过于在乎自己以术士的形象出现所获得的尊重,而忘记或忽视了自己的真正任务。
可见,在术士还是传教士上,利玛窦的选择,是想更有效地利用科学这一传教工具,因而非常愿意向中国人展示一种术士的形象,但传教士这一根本身份,使他在展示术士这一形象时有相当保留,在向中国士大夫表明天主教是一种理性的宗教这一观念因而值得信仰之后,便开始转换,用新的方式来作为传播天主教的主要手段。
四、在边缘人群中建立教会
天主教不仅仅只是一种思想和文化,而是一种宗教;而宗教不仅仅是一种个体现象,而且也是一种群体现象。因此,耶稣会来华传教士,每到一个地方,都想在那里建立居所和教堂,并成立自己的教会。要成立教会,首先就得有人受洗入教。于是,选择什么人,让其受洗入教,便成为一个重要问题。
天主教作为一种外来宗教,正如当初佛教进入中国一样,所选择的人,基本上都属于边缘人群。这些边缘人群,既有在社会中贫无立锥之地者,也有郁郁不得志的士绅,还有经历十分坎坷的人。
利玛窦在华施洗入教的天主教徒,分为三大类。一是病危之人,这是社会上最边缘的群体,因为他们很快就要归天了,基本上就要被整个社会抛弃了。这类人之所以愿意受洗入教,有病急乱投医的意味,起死回生之术在其中占了相当的地位。其中最为典型的是李之藻,他在病危时才同意休妾入教,虽然他病愈后又活了很多年。二是追求他的黄白之术以及祈祷生子。鬼星驱魔等“异术”的人。他们的兴趣在中国古代典型的“方术”。这些人虽然在中国各阶层都行得开,但却不是主流。其中最典型的是瞿太素,以及而南雄的郭生、南京的成纪无以及北京的李应试。第三类是向往其“天学”的儒者,其中最典型的是徐光启。这三类人,在明末的中国,都属于边缘人,虽然其中有人居于社会的上层。
利玛窦在中国传教,虽然走的基本路线是上层路线,但是,他始终没有见到皇帝,至多得到一些高官的支持。而这些高官,在整个官僚体制中的地位,实际上并不高,而且处在被排斥的边缘地位,在官场中郁郁不得志,没有什么实权。其中最典型的就是被称为明末天主教三柱石的徐光启、李之藻和杨廷筠。当然,这些在官场中郁郁不得志的官员,在其家乡的场望却不低,因为他们能够脱颖而出,进入官场,本身就是光宗耀祖的事情,往往被视为整个宗族的典范。他们的受洗入教,在整个宗族中具有相当的示范效应。这种示范效应,既是传教士所乐意善加利用的,同时也是这些人向传教士展示自己的价值的契机。因此,在明末的中国天主教中,便出现了家族式或宗族式的天主教会,其中的领头者是有功名的士绅,而其大部分成员却是平头百姓。就整个社会而言,这样的天主教会是处在边缘的,尽管它在某个村或镇是主导性的。
在利玛窦的中国传教生活中,朱维铮注意到一个有趣的现象:利玛窦的进京之路,与王阳明的心学从萌芽到流布的路线,有惊人的相似性。在利玛窦感到自己如鱼得水的南昌和南京以及江左地带,正是阳明学最为流行的地方。[117]利玛窦对朱子理学的批判,与阳明学派对理学的批判,有着极为相似的地方。而与利玛窦交往最为密切的士大夫,多有阳明学派的影子。其中包括把罗明坚和利玛窦引入肇庆的郭应聘,使利玛窦被郭应聘的继任者赶出肇庆后得以在韶州居留的南雄同知王应麟以及江右王门章本清的弟子瞿太素,还有被称为明末中国天主教三柱石之一的徐光启。徐光启曾师事黄体仁,因而深受阳明心学的影响。他的恩师,也就是他中举人的那次乡试的主考官焦竑,则是晚明心学的殿军。而朱熹理学,是明朝的官方之学,阳明心学在其面前是“异端”,这一学派的弟子在官场中鲜有得志者。
利玛窦在传教中,为了适应中国,首先采取的策略是“附儒”,这典型地表现在他在韶州改穿儒服称儒生的行为中。利玛窦出韶州时,由于对儒学的认识的加深,他再一次改服易名,以术士的身份出现,并加入到对朱熹理学的批判之中,这时,他采取的策略是“补儒”。利玛窦在南京站稳脚跟之后,特别是在有徐光启这样的有举人功名的人受洗入教之后,虽然他在与士大夫的交往中不断地声称自己是要“补儒”,但是,实际上他已经不再满足于“补儒”,而开始实施“超儒”的策略了。利玛窦的“超儒”策略,实际上有三个方面:一是强调天主教在道德上超儒,二是强调天主教在方术(科学技术)上超儒,三是强调天主教在共同体上超儒,因为信徒最后是要进天国的,而这是儒学所不能提供的。其中的第三个方面,其具体的体现,就是建立教会,在中国正统的三教之外,形成一种独特的宗教共同体,即天主教徒共同体。这个共同体,最初是由受洗的那些处在边缘的“异端“儒士以及其他的边缘人士构成的,虽然与中国的宗族制度相结合,实际上在当时的中国也处于边缘地位。但是,利玛窦坚信,它最终会成为主流。
五、结语
利玛窦到中国传教,选择和平手段而弃用武力征服手段,是基于对中国当时的国力之现实考虑;利玛窦之易服改名,先穿儒服称儒生,后穿术士服而称有道之士,是基于儒学雷锋是中国的主流文化以及中国人相信迷信的心理习惯的观察而作出的合理选择;而他以中国人眼中的高级方术即科学技术来传教的方法,正是对那一心理习惯的巧妙利用。鉴于他所要传播的宗教对中国人来说是外来宗教,所以,正如当初基督教在古希腊和古罗罗马的世界中首先是向处在社会边缘的各种人士传播一样,在利玛窦的领导下耶稣会在中国领洗入教的信徒也是在中国由于种种的原因而处在社会边缘的人,尽管这些人中不乏徐光启、李之藻和杨廷筠这样的精英人士,但其发展的信徒,大部分还是一般的处在社会边缘的人,包括那些身为精英人士的信徒在内。不过,这些身为精英人士的信徒是利玛窦所发展的信徒的榜样和领头羊。随着礼仪之争问题的发展,这些教会逐渐地由“精英”领导的教会变为一般中下层百姓所领导的教会,并且在民间化和地方化的轨道上发展,直到鸦片战争后才转移到新的轨道。
最后,有两点需要特别注意。
其一,利玛窦虽然以术士的身份成功地使天主教重新进入中国,但是,他以他的方术来诱人,但从来不以他的方术来骗人或害人,更不以其方术来挑战中国的任何一级的政府或任何一条法律,即便是在受到逼迫的情况下也是如此。这样,至少在道德上讲,他是无恶意的。这使他既迥然不同于中国声名狼藉的一般方术之士,也迥然不同于清朝中后期潜行入华的各路传教士。康熙之要求来华传教士遵守“利玛窦规矩”,其意不出此两个方面。也正是因为以南怀仁为代表的传教士遵守利玛窦规矩,在康熙与教廷特使争执之前的1687年,当南怀仁请求驰禁教之令时,康熙皇帝下谕称:“天主教应行禁止,部议极当。但见地方官禁止条约内‘将天主教等于白莲教谋叛’字样,此言太过,著删去。”[118]这说明,尽管由于以利玛窦为代表的在华传教士的表现,天主教没有被等于邪教,但是,“利玛窦规矩”要求在华传教士在遵守中国风俗和法律的前提下在华修道,并没有允许在华自由传教。因为包括佛教和道教在内的中国所有宗教在历史上都被置于政府的管理之下,都不曾被允许自由传教,所以,不允许自由传教,并不是只针对天主教的。
其二,利玛窦1609年2月15日在写给巴济范的信中指出,万历皇帝可能因为两件事情而明确反对耶稣会士,一是与外国人打交道并从外国得到资助,二是在中国传播新的宗教。[119]这两个忧虑,非常富于前瞻性,因为中国人是非常强调政治上的独立自主和思想上的正统的,犯此二者无一不遭受强烈的反对。康熙皇帝所言的“利玛窦规矩”虽然没有明确地说出这两点,但却实际上隐涵这两点,因为康熙皇帝眼中领票的传教士在中国是视同“国人”,为官当差而领取奉禄的。所以,康熙皇帝的“利玛窦规矩”与其禁止天主教的政策,并不冲突,因为后者是前者的应有之义。
文化“丝绸之路”上的利玛窦
王利民*
内容提要:利玛窦是明朝末年来到中国的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他在传教过程中尊重中国本土文化,并且能够入乡随俗。他的传教特点包括,偏重于把神学与自然科学有机的结合;结合中国文化来宣传教义,提出中国经典中本有的“上帝”这个至高核心;认同儒家和道家中“神”的范畴。 总之,利玛窦对中西文化的互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关键词:利玛窦 本土精神 上帝 儒家 自然科学
一、利玛窦到中国前的简历
利玛窦(Matteo Ricci)神父,字“西泰,”号“西江,” 1552年10月6日出生在意大利马尔凯省马赛莱塔市(Macerata)。其父亲、若翰·利启是梵蒂冈的市长和省长(罗光,1959,4页),也是一名药剂师。他很希望自己八男、四女中排行老大的利玛窦能继承自己的官职。玛窦的母亲、若翰娜性情温和、敬主虔诚、常对他的事业给以鼓励和支持。玛窦幼年的启蒙老师是尼各老·白启完(Nicolo Bencivegni),后来这位私塾老师进了耶稣会,玛窦9岁时进了本市的耶稣会学校。16岁中学毕业后被父亲送往罗马,父亲想让他读法律将来做官,但玛窦以自己独特的性格在罗马大学(Collegio Romano现在的额我略大学)读完了自己喜欢的各科自然知识、人文和神学课程。大学毕业后,玛窦于1571年8月15日在罗马的桂里纳小岗(Quirinale)加入耶稣会,并于1580年7月25日在印度的交趾(Cochin)被晋升为司铎,因为1577年5月18日玛窦被总会长派往印度传教,那年他才25岁,因交通原因、直到1578年3月24日,利玛窦、罗明坚(Michele Ruggieri,1543-1607)等十四名耶稣会士才从葡萄牙的里斯本动身乘坐“圣路易”船只去卧亚(卧亚在印度半岛西,时属葡萄牙人的领土)。
1582年4月15日耶稣会视察员范礼安(Alexandre Valignani)应当时在中国肇庆的罗明坚神父的邀请,便调遣博学多才的利玛窦神父从卧亚到澳门当助手,于是利玛窦于1582年8月7日到达澳门,那时他已经28岁。在澳门期间,他住在圣玛尔定经院,努力学习中文并希望早日把福音传入中国,但需等待时机。一天、终于等到了广东肇庆知府王泮的许可证并差人来澳门邀请以前拿到护照(当时称为“路照”)的罗明坚神父去肇庆工作,因而1583年9月利玛窦与罗明坚神父怀着既渴望、又迷茫、既喜悦、又惆怅的复杂心情来到了梦寐以求的中国肇庆。
二、利玛窦的本土化精神
“丝绸之路”上的人们,无论走到哪里都应该首先学会入乡随俗,利玛窦也并不例外,从他的传教生涯可以看出,他的入乡随俗精神非常突出,如:穿儒服,向皇上奉献贡品,见士大夫们用中国礼数作揖等等都体现了他的本土化精神。但从信仰的角度去提倡本土化,其主要体现在从本土中找出信仰,并把这一信仰提升。2001年若望·保罗二世称利玛窦的最大贡献在于他的“文化交融”,他在中国的传教方法可以和早期教父们在天主教与希腊和罗马文明相遇时所起到的融合创新精神相比,因为当时的教父们没有丢掉具有巨大影响力的希腊哲学于不顾,而是运用了让希腊的哲学与神学相结合的原则,是为了能让基督宗教信仰便于从理性上被理解,如奥力振把柏拉图的“灵魂流出说”与灵魂再回归到“太一”说有机地与天主教的神学相结合,让灵魂的产生与归回更加明朗化,当然这一理论后来被教会进一步发展了。哲学为神学之仆女并当很好地为神学服务,在此变得更具有说服力。教父们最终让神学与希腊思想有机的结合起来,并为此做出了突出贡献,从此神学也可在不同的文化背景里落地生根了,并使之带有很强的生命力。
利玛窦偏重于把神学与自然科学有机的结合,这样不但证明自然科学与宗教是相辅相成的,也说明科学离开宗教是瞎子,宗教离开科学是瘸子的真实写照。利玛窦想把信仰与科学结合起来一并送给国人,这种态度对旧中国那些不能把宗教与科学好好相结合的人是一个提醒,更对那些不懂科学用迷信活动充当宗教礼仪到处行骗的人是一个学习的榜样,真宗教不是迷信更不反对科学。如果人能够理解到这一点,也算利玛窦在中国二十七年的辛勤耕耘为今后基督宗教的传播做了很好的铺垫,也为国人发现并提升本土的宗教信仰打好了基础。其意思是说,中国也有自己宗教信仰的根基,我们需要去发现它,并提升它到纯真信仰之境地,因为在很多时段,人们把信仰经营的面目全非,甚至把许多骗术与信仰结合起来,把迷信与信仰混淆起来,让商业把信仰利用起来,使许多善男信女们不知如何度自己的信仰生活!所以朴素的信仰需要与真正的信仰相遇,让朴素的信仰在真正的信仰里被净化之后,再放回社会里由众子民享用和侍奉,这样才能有益于社会和国家。
利玛窦的本土化精神还体现在翻译造物主的名字时,他首先从中国本土信仰的位置里去寻找中国文化里的造物主、或者说近似于基督宗教里造物主的合适词汇。造物主的拉丁文是“Deus”,意大利文是“Dio”,法文是“Dieu”,英文是“God”,这位造物主的内涵是“自有永有,创造宇宙的主宰。”在他们的语言里其意义都很一致,这个词在中国语言里很难找到完全相等的概念。最终利玛窦在中国经典中发现了“天主”、“上帝”这些概念,利玛窦认为这两个概念几乎可以与拉丁文的“Deus”对应,可以用“上帝”这个中国概念来直接翻译拉丁概念“Deus”。这要比公元635年(唐朝贞观九年),天主教的异端派景教(涅斯托里)传教士进入中国后,称造物主为“妙身无元真主阿罗诃”要好得多,因为这种翻译靠近佛教概念,也不能充分表达其内涵和外延。“上帝”本是中国儒家经典《诗经》、《尚书》、《礼记》及二十四史中至上神的概念。从“至上神”这一点,意义就很接近,古代中国人与古代犹太人一样,认识到宇宙万物之上有一个至高无上的创造和主宰的力量。如《诗经》上说,“文王之灵在天上,闪耀在天上”,“文王上上下下,都在上帝的左右”。《商颂》中也说:“商王敬畏上帝之德,日日在提高,光明的德行长久不变,一心敬奉上帝。”可查的是利玛窦于1595年编写的《交友论》中开始使用“上帝”这个概念来指称造物主。在1599年编写的《二十五言》中,利玛窦再次使用“上帝”概念,他说:“仁的开端,就在于恭敬爱戴上帝。上帝,是生育万物的原始本原,是万物之主宰。”儒家讲“仁”,而利玛窦则强调所谓的“仁”,就在于敬畏、热爱上帝,听从上帝,上帝是万物萌生之本原,是万物之主宰。这就是所谓的要知天命、顺天命而行。所以他从中华文化里找到了造物主并进一步丰富了祂的内涵。
利玛窦重新提醒中国经典中本有的“上帝”这个至高核心。在《天主实义》中,利玛窦除继续使用“上帝”概念外,更多使用了与“上帝”相当的“天主”的概念。“天主”是他从中国经典中借用来的,例如《史记》中记载秦始皇所祭的最高神,就是“天主”。原句这样说:“天神,一曰天主,祠天齐。天齐渊水,居临淄南郊山下者”。同时也是根据中国古典和儒家“最高莫若天,最尊莫若主”之句而称自己所信仰的神为“天主”,取意为“天地真主,主神主人亦主万物。”慢慢地“天主”就成了称呼造物主的专用词。利玛窦对“天主”与“上帝”的关系在《天主实义》中解释到:我说的天主,就是中国古代经书中所说的上帝。
在这一点上利玛窦的做法非常值得我们钦佩,他帮助中国人找到了所丧失的上帝信仰,中国人该当以敬畏之心重新接纳我们祖先的信仰,如果丧失这一信仰,就等于丧失了领悟中国传统思想的能力。上帝、天主在中国经典中留下了清晰的信息,例如中国最早出现的文字——甲骨文,其所记载的都是占卜、问天的事情,可见神明在我们祖先心目中的地位,这些信息都是中国精神的宝藏。
利玛窦在寻找华夏祖先所敬拜的神明过程中,认同了儒家和道家中“神”的范畴,唯独不认同佛教中“神”的范畴,因为佛教的轮回理念与造物主的范畴差别太大。一个是自修成佛、成神,一个是说“神”是自立体,是无始无终的永存者,是万物的创作者。这也就有了利玛窦所写的《復虞淳熙》及李之澡、马相伯、英华和陈垣所写的文章对虞淳熙和莲池和尚不断攻击天主教信仰加以辩护。这就是后来徐光启所说的“驱佛正儒”或者说“补儒易佛”,不同的宗教对神的概念认定、肯定会有出入,但应本着互敬互爱的态度互相探讨,或者说以哲学的思辨能力作为对信仰的辅助理解,不应当以固执的机械形式攻击他人信仰。《梵二文献》也曾这样教育我们“各民族原是一个团体、同出一源,因为天主曾使全人类居住在世界各地。他们也同有一个最后归宿,就是天主,他的照顾、慈善的证实,以及救援的计划,普及于所有的人,直到被选的人集合在圣城,就是天主的荣耀将要照亮的圣城,各民族都将在祂的光明中行走。”[120]因此如果我是利玛窦神父,或许不与莲池和尚辩护,因为1)对一个固执己见的人很难使其改变。2)对于一个恶意攻击的人就更不需要耗费实力。3)他根本没有基督宗教神的概念,再加上性情冲动,不开放,这样的人就很难与之明礼。与这样的人相争简直降低身价,例如在北京的和尚达观等人曾散布谣言说:“利子(利神父)勾通澳门西番,存心不良,将为祸中国。”他们后来因疑案(妖书事件)有的被处死,有的被放逐。(罗光,1959,161页)
利玛窦神父的生活方式和态度则显得温和、善良,据有基督博爱精神。在《奇人十篇》中他曾向十几名明代大夫们的提问耐心作答并针对其个人的困惑与烦恼寻找答案。例如明朝万历年间(1601年)的礼部尚书冯大宗伯,曾被世俗比作《周礼》的春官宗伯,他曾感叹人生之乐反不及禽兽自在,因而利玛窦给他讲述“原罪”的概念并举出许多西方圣贤对人生苦海的描述,最终阐明天堂才是我们的真正家乡。(朱维铮2001,439页)面对中国人怕死亡的事,他在《常念死候备死后审》中用欧洲古哲人的话劝导徐光启说:“常想死亡有五利:“力避过尖、克别私欲、轻视名利、慎防骄傲、死于安乐。”也曾提醒郭敦华“算命看相为迷信”等等。他都在很具体地根据人们的生活需要做出相应的解释和服务。(朱维铮,2001年,441页)他所写的《西国记法》更是把自己美好记忆术的秘密介绍给当时以背诵《五经四书》为主来参加考试的人们。也有人说利玛窦是把西方的神经学传入了中国,因为书中记载:“记含内室,有脑囊,盖颅卤后枕骨下,为记含之室。”(曹赠友,1999年,347页)在当时中国人认为心主使着记忆。在文化“丝绸之路”上的利玛窦,来到中国虽然其核心思想是要传播基督信仰,但他没有忘记发现和挖掘中国的本土信仰,他认为中国人不但应该重新生活于对祖先上帝(天主)的崇拜,更应该了解,真正的上帝、天主是宇宙的主宰,他派遣他的儿子来到我们中间,并把真理启示给我们。《道德经》第四章记载:“吾不知谁之子,象帝之先.”这句话的意识是说,我不知道“道”是谁的儿子,他存在于盘古(万象)之前。这样说来在中国的信仰里,距《圣经》中的造物主概念并不远。《道德经》中多处有对宇宙根源、至高神的描述,如开头第一句:“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及十四章的“视之不见,名曰“夷”;听之不闻,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此三者不可致诘,故混而为一.”黑格尔曾解释说,这里所提到的“夷”、“希”、“微”就是《旧约》所说的“雅威”(天主)。所以在中国文化中发现信仰并帮助其提升至更加纯真的境地是非常重要的。
三、文化“丝绸之路”上的利玛窦对中西文化的互通
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首先当提的是他所翻译的涉及到几何、地理、宇宙论、音乐、化学、及艺术等方面的重要著作。利玛窦和徐光启共同翻译了当时在欧洲非常受欢迎的欧几里得(Euclid,约330-275B.C)的《几何原本》,它是在12世纪初被欧洲天主教学者在阿拉伯世界发现并译成拉丁文,很快在文艺复兴时期成为欧洲的重要学科。利玛窦和徐光启共同从拉丁文翻译了六卷,这些拉丁文内容来自于利玛窦的罗马大学老师克拉维乌斯(Clavius, 1537-1612A.D)的手稿。《几何原本》的刊发成为使从明末到清初一些数学家热衷研究的显学,无论采用的基本概念和专门术语还是构造的演绎系统或解题方法都把利玛窦和徐光启译本当作原创的出发点和基础。这对当时的中国在数学上的补充是多么重要!因为那时的中国在几何学上是一片空白,利玛窦在数学上对中国的贡献太大了,可以说无与伦比。不过有一些人对他没有及时译出后九卷略有说词,其实大家应当明白,利玛窦是一位传教士,他本当把传教作为第一要务,但他没有把一生献给科学,而是把一生献给了天主,献给了传教事业,如果中国人不顾忌她的感受,不理睬他来华的真正目的和思想,只对他手里的《几何原本》感兴趣,难道这不是一种自私和利用吗?利玛窦的书扎里这样写道:“愿天主矜怜这片地上数以百万计的人们,通过各种方式开启自由宣讲基督信仰的大门。”(1596年10月13日写给他的总会长克劳迪奥·阿夸维瓦(Claudo Acquaviva)神父,罗马)。还有一次他写给自己的会友的信中说:“我们非常高兴,并希望从此以后凭借新的帮助和支持可以在这里更多的宣讲基督信仰。”(1581年12月1日至会士吉安·皮耶特罗·马费尹【Gim Pietro Mffei】神父-葡萄牙里斯本)。科学与宗教本来就不矛盾,通过利玛窦的事迹同时也在提醒我们当跳出自己历史和文化的局限性,更不要动不动就用政治的观点看待一切。我们当走入利玛窦的内心,去更多了解他这颗基督徒的心,把信仰与科学相结合的心,这一颗爱中国的心。
当想一想利玛窦在明朝末期交通和通讯都极度落后的情况下,他远离家乡、漂洋过海来到我们闭关自守而又落后的国家,整个心为我们国家燃烧,为我们的国家奉献一生,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究竟是为了什么?我们正确把握了吗?
利玛窦神父入乡随俗,任劳任怨最终是要把基督的博爱精神和救灵大业撒播在中华大地上,同时他也要把西方的先进科学知识传播到中国人的心中,希望中国人能在信仰上和科学知识上双丰收。难道接近他的人就不能抱着开放的态度想一下,他对科学这样尊重,且又把终身献给传教事业,这说明了什么?说明救灵魂的事业是至关重要的。耶稣曾经说过“你即便赚得了全世界若丧失了灵魂对你有什么益处呢?” 如果说他要给于国人的伟大信仰不能得到国人的尊重或明白,那么他宁愿用自然科学为工具来敲醒国人,首先使之具有对人生和宇宙的科学认识,然后希望把人类生命的尊严提高到信仰的至高点并重心找回祖先对造物主的敬畏之心。在利玛窦心中信仰比科学知识大,因为信仰能送给人们科学知识所不能送给的幸福、快乐、善良、宽恕、忏悔和救赎。利玛窦丝毫没有贬低自然科学的意思,科学与信仰都在为人类服务,他们应该像一对孪生兄弟。利玛窦懂得科学,但没有利用科学害人,他具有坚固的信仰,也不会利用信仰害人。我们可以看到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在他内得到统一,他也铁了心要把这两种文明送给中国,而国人直到现在还在反省和回味,或者说徘徊。请大家冷静地想一下生活在没有信仰的环境下其精神生活究竟如何呢?是互相欺骗么?是失去诚信么?是为了物质利益而伤害别人么?其答案应该很清楚,所以对祖先所经营的信仰需要大家重心审视。在这里还想多说一句的是,在鸦片战争之后,李善兰(1811-1882)同英国传教士伟烈亚力(AlexanderWlylie1815-1887)合作译出欧几里得《原本》后九卷。
在利玛窦的影响下,体现出中西文化交融的成果,还有李之澡从中国传统数学中选取的一些数学知识,如方程、开方、一次方程和二次方程的数值解法及高次开方法等(曹赠友,1999年,98页)加入到了利氏的老师克拉维乌斯的《实用算术概念》中,后来又补进了程大位《算法统容》中的一些难题和徐光启的《勾股文》与《测量法义》中的一些相关内容。如此的中西方算数会合,对国人是何等的实用、鼓舞和启发。后来利玛窦口授并让李之澡笔录《圜容较义》,其中包括十八个命题,讲述三角形、圆和球体的表面积等。李之澡还在他的《圜容较义序》中说:“自造物主以大寰天包小寰地,而万行万象错落其中,亲上亲下,削成寰体”(朱维铮,2001年,580页)。在1613年他们又共同翻译并刊发了《同文算指》,讲十进位、百进位、千进位等,用阿拉伯数字的加、减、乘、除,还有验算法和分数记法,分母置于分线之上,分子置于分线之下。现在通过改造把分母放下边,分子放上边(曹赠友,1999年,97页)。《同文算指》还有一个好处那就是可以用笔和纸对事物进行计算,这样就打破了中国用珠算进行计算地麻烦。在《同文算指》前的《同文算指统编》介绍了对应用题的解析方法,大大提高了利用杠杆原理对应用题的计算方法。利玛窦很重视把几何学用在军事上,因为国人对火药缺乏化学研究,因此中国火药的纯度不高,威力也不大。《明史·徐光启传》中说:“光启从利玛窦学天文、兵器,尽其术...…。”(曹增友,2000年,183页)利玛窦介绍的西洋炮就是被后人称颂的“红夷炮”,在17世纪上半叶因着中国政治角逐的多极化曾被各集团势力使用,在中国历史上发挥过不同寻常的作用。在1863年美国北长老会传教士狄考文(1836-1908)所写的《心算数学》又收录了一万两千条数学《术语词汇》,这又大大丰富了国人的数学领域。所以传教士们对中国的贡献有目共睹。
利玛窦在科学上的贡献还有其翻译的《测量法义》是一部应用几何学著作。其中讲述了对地和天的测量,测量所需要的器具必须符合测量对象的原理。同时讲到对仪器的制造及所测对象的投影技术等等。在书中还列了十五道应用题。如“月行三日,得三十七度,问九日行几何度?其运算结果是一百一十一度”等等。利玛窦所翻译的《乾坤体义》分上中下三卷。上卷讲的是论地球和天体构造,中卷讲的是地球与日月五星关系的原理,下卷讲的是十八道几何题。书中有很多图形和实测运动规则的几何学原理和方法,这些原理有助于中国人破除天体运行的神秘感,有助于把中国的历法天文学和应用几何学推到一个新的高度。所以清修《四库全书》的馆臣们对利玛窦所讲对“天学”及这部著作都非常敬重,对利玛窦也非常尊重。(朱维铮,2001年,516页)
由利玛窦口授和李之澡笔录的《浑盖通憲图说》介绍了克拉维乌斯制作日晷的各种方法,及如何用铁片制作星盘,这在中国古代也有类似制作,如果汲取了这些科学知识会使我们的天文知识和技术变得更加科学和据有操作性。其中的《经天该》部分是以民间的《步天歌》形式所写,读起来朗朗上口且便于记忆。
还有一部使我们不能忘却的科学专著就是《理发器撮要》共分三卷。第一卷被称为“理卷”,共十三篇,论述的是宇宙结构,第二卷被称作“法卷”,共三篇,所讲的是测量天体运行的几何学方法。第三卷被称作“器卷”,共十二篇,分别讲述测量天体仪器的用途和天体形象。很明显在第一卷的“理卷”,从一开始都在批评中国传统的三种宇宙论,这是在为后边要讲述的亚里斯多德和托勒密的同心水晶球式的世界图像做准备。例如“所谓天了无质,仰望无极,譬之远望黄山皆青,俯视深谷皆黑,日月星辰浮于太虚,无所根系,此汉郄萌之记,所谓宣夜也。其说甚诞。”接着利玛窦简单介绍了托勒密体系的宇宙论:如“浑天言如鸟卵,天包地外如卵白,地在天中如卵黄,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半在地上,半在地下,南北有枢机旋转,斜倚地中;北极出地三十六度半,南极入地三十六度半;两极之中处为赤道,如带系天之中,日月星辰俱斜转上下为昼夜,出入赤道为冬夏,大略如是。”这些知识都非常有助于我国的天文学发展,很多的天文图像以现代人的天文知识和眼光来看都还很有用。又如,1601年由利玛窦手绘并进程给明神宗的《万国图志》后来被李之澡改名为《坤舆万国全图》曾多次被宫廷内监临摹,因为其中讲述了日蚀、月蚀及日大于地的诸多宇宙知识。此图文刊出后,曾有很多名人学士为之写“跋”和“序”。所以在文化“丝绸之路”上的利玛窦从西方给我们带来了很多有用并且非常先进的科学文化知识。关于那部《理发器撮要》有研究者建议是利玛窦的未刊发稿,和后人对利玛窦已刊译著的摘要和明末传抄利玛窦的著作中后人填补的新知识的综合本。无论如何这部重要著作与利玛窦不无关系。我们还是要感谢他的“东西交融”精神和行动。
那么在文化“丝绸之路”上的利玛窦又把我们中国的哪些精华带到了西方世界呢?1593年利玛窦按照耶稣会远东教务观察员范礼安的指示,开始将朱熹的《四书》翻译成拉丁文。这对当时的意大利和后来的欧洲了解中华文化是一项很强的推进剂和非常据有代表性的著作。
另一点想要提及的是,中国的汉字对于外国人来说就是一幅画,只有图像而不知如何发音,可是传统的汉字拼音,如“ㄅㄉㄓㄚㄞㄢㄦㄆㄊㄍㄐㄔㄗㄧㄛㄟㄣㄇㄋㄎㄑㄕㄘㄨㄜㄠㄤㄈㄏㄒㄖㄙㄩㄝㄡㄥ”等,也有类似的特点,利玛窦神父则据有创造性地用拉丁文拼写汉字。明万历三十三年(1606年初)利玛窦用拉丁文拼写汉字的著作《西字奇迹》问世,方豪则把利玛窦和罗明坚合编的注有罗马拼音的《平常问答词意》称之为“第一步中西文字典”。他还说,明末的程大约所刻的书画集《墨苑》收入利玛窦所赠宗教画四幅,每幅都有拉丁文注音的汉子,后边附带有三百八十七个著有拉丁文拼音的汉字来解释这四幅圣像,这些拼音中包含“二十六个声母,四十三个韵母,四个次音和五个声调符号。”(方豪,1983年,948页)利玛窦创造性的用拉丁文给汉字注音,为我们今后汉语拼音的发展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在1958年2月11日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批准了用拉丁字母作为汉语拼音的符号,以便于国际间的交流与合作,并于1982年成为国际标准ISO7098(中文罗马字母拼写法)。中文罗马字母拼写法的发明,为西方人了解中国提供了一个重要平台,为西方人学习汉字提供了一个不可替代的工具。
另一件当提的事是文艺交流方面,因为利玛窦在1601年向明神宗进献的礼品中有一张西洋琴,当时还有他向皇帝进献的包含有八章歌谱和歌词的《西琴曲意》一本。其歌词大意都是天主拯救世人的道理,并且大部分都取材于《旧约。达味圣咏》,如“牧童游山”和“悔老无德”等等。我们都知道音乐是沟通人们情感的重要工具,特别是对语言不通的人们。再者,西洋琴也补充了中国的传统音乐在这方面的缺陷,就如中国音乐的传统唱名只有五个,即:角、徴、宫、商、羽,后来又加进了由教会四线谱的额我略调发展出来的五线谱,这样就大大丰富了中华音乐的曲调内涵。
我们最后还是要回到利玛窦的《天主实义》上,这本书因在不同年代里刊发的版本很多,所以我们以1603年得到耶稣会上司准印并被收录在徐光启《天学初函》的年限为准。此书以问答题形式写出了天主教的基本教义,类似于1583年罗明坚神父翻译的一本普世天主教通用的解释天主教基本信仰的《要理问答》。在写作方法上无庸置疑利玛窦神父受到这本《要理问答》的影响无论是拉丁本或是中文本,因为作为一名天主教教友,从小都被要求背诵这本《要理问答》,正如利玛窦书札中所说,“我们的确费了一番功夫,才把这本迫切需要的《天主实义》译成中文,我们进行了多次修改… ...补充了一些新的内容... ...创造了许多新的基督信仰专用术语… …首先是天主经,然后依次为圣母经、天主十诫、信经、十字圣号、神行善工、真福八端、七罪宗、七补赎、人体五官、灵魂三能、三超德、最后注明了七件圣事的意思。”[121]但是从写作动机上看,这是他来到我们东方的核心意图。因为在利玛窦的日常生活中曾接待很多中国文人学士,正如他自己所说:“这都是进行福传的良机,向他们介绍我们的基督信仰,指出迷信的虚假。”[122]在“明清之际,教外人有时,称天主教为‘利氏之教’;称外国教士为‘利氏之徒’。(方豪,2007,53页)利玛窦在他的书札中也提到自己与所在耶稣会弟兄的关系是“诚恳”、“听命”、“共融”等等。与天主的关系是“爱”、“谦逊”、“参与基督的苦难”等等。他曾说:“我努力寻找各种机会为爱天主而做更多的事。”[123]
郑安德在编辑《天主实义》时写到:“明末清初在中国发生的天主教和中国本土哲学、宗教思想之间的对话,其历时之久、规模之大、涉及问题之多、论辩之激烈、影响之深远,在中国文化史、学术史和宗教思想史上,都是空前绝后的,在迄今为止的人类思想文化史上,也蔚为大观… …客观、公正的研究中国基督宗教思想... …对进一步促进中西文化学术交流,都具有重要意义... ...为寻求天主的“道”和中国文化的契机,也会在人生问题上做许多有意义的和开创性的探索… …对未来世界的中西文化交流,都将具有深远的意义。”[124]
利玛窦的本土化战略与祖上祭祀的现代意义
(韩)严震泽*
内容提要:17世纪初,为了在中国实现基督教的本土化, 以利玛窦以及以他为中心的耶稣会的传教士们,以“上帝即天主”的理论写了“天主实义”并完成了补儒论和适应主义战略, 向中国的学者和一部分官僚传播天主教并施以洗礼,以此开始了东西文化的融合。他引进的西学和“天主实义”在朝鲜使节团来往中国时同其他一些西方的书籍一起传入了朝鲜,朝鲜官僚和学者中所谓星湖左派的南人学者们自发地开始研究西方的学术文化,其中有些人不仅吸收了西方的科学思想,还接受了天主教思想,甚至独自建立了天主教会。1790,朝鲜收到的“祖先祭祀禁止”命令 不仅否定了曾经在中国活跃着的耶稣会的本土化传教事业,产生了珍山事件,辛酉迫害等无数无辜的人为此付出了流血的代价,而且让欧洲中心主义·封闭性的世界观在中国和朝鲜扩大开来,还留下了很多需要治愈的伤痕。首先,通过宗教哲学性的“祖先祭祀制度的现代性再解释”来进行正确的“祖先制度的确立”是十分必要的,为了解决这些问题,要求教皇厅为1790年施行了“祖先祭祀禁止”令而道歉是有一定道理。祖上祭祀问题让我们得到一个历史教训,应当了解到地区教会和该民族才应成为福音本土化的主体。
关键词:补儒论 适应主义 本土化 朝鲜 祖先祭祀
社会学家阿诺德·汤因比曾这样说,“纵观人类历史,人类文明的出现及发展进程大抵取决于本民族在经历内忧外患之时所采取的应对态度。在经历大灾难,大挑战时,如果能够英勇,理智地面对,则会对本民族文明的发生和发展大有裨益;反之,如果不能积极、勇敢地面对,本民族文化的发展则会处于落后,最终沦为惨遭淘汰的局面。”
18世纪开始,韩国社会中可以认识到的西学发展趋势大致上可以从两个层面来看。第一个是在西欧世界的传统中形成的,并且达到了文化巅峰的西欧基督教思想,第二种是当时由北京传教士传入的西方科学技术文明。这个文明的内容是通过东传汉文西学书在朝鲜后期传入的,主要是由以星湖李瀷为中心的南人学者负责的,他们通过研究汉文西学书并利用相关文献才使得李朝后期社会接受西学。
韩国社会初次传入西学的时期正值李朝社会在文化和社会层面上面临大的转换。即经过17-18世纪,随着贵族官僚社会积累的矛盾显现出来,一部分制度上的改变也变的不容忽视。这时候李朝王朝创立的思想根基——性理学理论不仅沦为了社会和党派的斗争借口,也逐渐成为了社会的痼疾陋习,在这样的状况下,社会上出现了一股对程朱子学的哲学,政体和思想进行全面反省和批判的风气。
在这样的状况下,对以性理学为基础的政治和社会的矛盾极度敏感的南人学者[125]们率先从学问的角度研究西学所含有的哲学和其思想理论,甚至渐渐认识并吸收了宗教性的思想。
一、利玛窦的补儒论及其影响
明末清初,耶稣会会员开始将基督教传入中国社会,之后是遣使会会员。他们最开始通过和中国保持密切的接触,来努力发掘布教的途径。其中以大量汉文著作和多样化活动而著称的就是耶稣会的传教士——意大利的利玛窦(Matteo Ricci,1552-1610)。他在1601年到达北京,和他的后继者在明朝后期和清朝初期都一直在中国准备着神学的根据地。在1665年和1724年中国的基督教遭受到迫害时,这些耶稣会会员依旧被允许留在中国,因为他们的作用不仅仅局限于宗教层面上,还主要是体现在学问的传播和文化上。这样耶稣会传教士的活动不仅给中国清朝初期的朱子学带来了很大的冲击,还对欧洲造成了重要的影响。在欧洲,他们关于中国文化的知识被介绍,这对欧洲的启蒙运动产生了影响,换句话说,对欧洲文化体系中基督教的排他性也起到一定的反省作用。
利玛窦神父1552年出生于意大利,1571年加入耶稣会并成为了基督教的神父,1583年来到中国,1610年在北京逝世。他为了传播基督教而来到中国,不仅将基督教的哲学理论体系以汉文严谨地叙述了出来,还用汉文写了很多关于西方科学和天主学的著作,比如《万国图志》和《畸人十编》等书。他因为撰写了东传汉文西学书,为基督教的福音传到极东之地做出了极大的贡献。这些东传汉文西学书中最有名的著作就是《天主实义》。他研究了中国经典,从而把握了中国哲学的核心内容,即“天,上帝”,他发现中国的哲学核心和圣经的“上帝”并没有什么区别。他在见到北京的万历皇帝之前就以上帝即天主为基础写了“天主实义”,还完成了补儒论。利玛窦1595年在南京开始撰写《天主实义》,1601年在北京分为上下卷出版,之后在1604年再版。
这本书的叙述形式是以西士(利玛窦是这样称呼自己的)和中士(中国书生)的对话形式展开的,主要关于教理和基督教核心教义的对话和讨论。这本著述的主要内容是关于天主的與性及人间的本性,灵魂不灭和赏善罚恶等宗教教理,以及对亲儒斥佛论的见解。
利玛窦的《天主实义》不仅对明末清初中国思想界造成不小的挑战和轰动,还对朝鲜后期的思想史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在《天主实义》中他阐释了补儒论历史理由,即因为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古代儒学的很多书籍都消失了,后代的宋儒根据自己的想法错误地解释古代儒书的意义并加上注释,使真儒的思想陷入了谬误,因此他主张通过基督教的天主思想和世界观来找到真儒的正确意义。
二、利玛窦的适应主义
(一)适应主义生活
利玛窦被认为是适应主义方法论的创始人,1583年他和同僚Michele Rugger[126]从在兆京时就开始试图接受中国的传统和文化。他们学习中文和佛儒教的经典,他们并不执著于欧洲式的名字,而是用中文名字利玛窦及罗明坚,并采取了佛教式的服装。利玛窦到了1594年在得到范礼安的允许之后开始采取儒学者的装扮并养长了胡须和头发。他无法改变自己的瞳色和大鼻子,曾开玩笑说自己为此感到十分遗憾,由此可以知道利玛窦为了想同中国文化一致做出了很多努力,就如他自己所说的“成为中国人”。
利玛窦为了不给人留下基督教是欧洲的印象而努力着,以儒学者和基督教祭司对话为形式写成的《天主实义》就是在这样的观点下写成的。通过这本书利玛窦表述了基督教的福音不是欧洲文化,而是可以完成中国传统文化的。然而问题是虽然传达了基督教的福音,仍然是披着欧洲文化的外衣传播的,和欧洲文化一起传入的基督教福音在中国如何脱去欧洲文化的外衣并披上中国文化的外衣就是利玛窦平生研究的课题。
利玛窦尊重中国的文化和宗教,他在中国的传统中发现了智慧,并从基督教立场上肯定并接受。直到在约350年后的第二届梵蒂冈公议会上才发布“关于他宗教的宣言”[127](Nostra aetate)的教导,但是利玛窦却早就已经开始做了。
(二) 适应即传教
利玛窦首先想向中国人介绍基督教的文化,为了这样的目标,开始需要的就是“让传教对象适应传教的主体”(Anpassung des Missionssubjekts an das Missionsobjekt),即让传教对象变化前需要使进行传教的传教士首先改变。用Karl Rahner[128]的神学思考方式来表达的话,就是“传教主体对传教地的适应是使传教对象接受福音的可能性条件”。因此为了让中国人接受福音首先需要的是传教士接受中国人的生活方式。这样的方法论教导了耶稣会成员按照自己传教的地区及传教对象的生活方式和水准来生活,这也是和伊格纳西奥[129]的灵性相符合的,具体来看是和方济·沙勿略和范礼安[130]的传教方法一脉相通。利玛窦以这样的精神和神学概念为基础的适应主义传教与中国人的精神,生活条件以及文化状况相适应,因而得以实现。
利玛窦想要践行与中国状况相适应的传教活动,然而不管如何,小心谨慎的接触方式是十分必要的。这就是外部适应和内部适应的区分,外部的适应是关于传教士的活动方式的,内部的适应是指传教士活动方式的理论方面。最重要的是如果中国人对外国传教士抱有关心态度的话,首先关注的焦点就是传教士的外表及生活方式,以此为基础,传教士想要表达的自己的生活方式究竟是怎样的。利玛窦的外部适应过程从他自己给欧洲朋友寄去的书信中很好地表现了出来,即“通过我们的服装,我们的外貌,以及生活方式,从所有这些外部的事物来使我们成为中国人。”[131]
(三) 宗教和文化
根据对基督教的理解,信仰就是在某种文化背景中的人成为了传教的对象。福音传播要在具体的时间和空间中进行,因此福音要与其传播地的时代状况维持密切的关系才能传达。如果把基督教的信仰理解成欧洲文化的话,就将基督教信仰绝对化了,同时也有将欧洲文化绝对化的危险。这样来看非欧洲圈的文化会觉得要依照基督教信仰及欧洲文化做出改变。另一种模式是基督教信仰虽然披上了文化的外衣,但却不是和文化统一,在这种形式下是要关注福音传播地的状况,目的是将地区文化基督教化。前一种类型是从绝对主义的立场出发,不认同地域文化的价值,而后一种传教类型则是认同地域文化的价值,并将其理解为福音化过程中的伙伴。从前一种传教类型中可以看到欧洲中心主义的傲慢,而后一种类型则存在着福音在文化上还原的危险。
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宗教与文化并不是相同的。宗教是文化的媒介,具有具体而独立的形态。如果没有文化的媒介,宗教从内部就无法存在。但是文化常常被宗教影响,根据宗教的引导随着时代而发生着变化。变化着的文化又重新以其他的形态成为宗教的媒介,即宗教给文化以影响,接受了宗教影响的文化随着时代而变化并传播着宗教。因此文化随着时代不断以新的样子向人类传播着宗教。
(四) 从文化理解福音及从福音批判文化的辩证法
上帝将自己的爱通过历史这一具体媒介传达给人类,所以如果说在2000多年前天主就成为了人,并以此来显示自己的爱的话,那这个就是通过当时的巴勒斯坦宗教文化传统表达出来的。换句话说,脱离了巴勒斯坦的宗教文化传统,就无法理解通过耶稣来表达的上帝的爱。即文化是让人们理解福音的媒介,但是与此同时必须要考虑的是巴勒斯坦的宗教文化是通过耶稣而完成的。虽然福音是以接受被传播人的实际状况来显示自己的,但福音也为了配合人的实际状况将其作为救赎对象的。即福音虽然有将有关地域的文化选为伙伴的必要性,但是这并不是因为福音把文化作为完全的东西,而是因为文化本身成为了福音化的对象。福音发挥着类似现象作用的同时,也将质以现象的状态表现出来。通过福音这样的文化批判功能,就可以避开福音文化主义上的回归。
利玛窦虽然接受着中国文化,但也不是丧失了批判的精神,对他而言重要的并不是单纯地肯定并接受中国文化。中国文化不仅仅是发挥着传播福音的作用,同时也是福音的对象。因此对于可以矫正的事情,利玛窦并不吝于发挥他的批判精神。他为了观察基督教的神论,毫不犹疑地批判泛神论与无神论观点是众所周知的事实。[132]
(五)对适应主义传教的神学评价
让利玛窦迈开第一步的适应主义传教方式促使我们有一个发展中的理解。所谓适应主义并不是单纯地在不变的神学中附上变化着的文化要素,如果是的话,那这样的结合也不过是表面上的结合而已,这样的适应主义传教也只是为了教会扩张而采取的单方面战略性的措施。以文化为主,围绕着人类的所有情况不是指人类生活的附带,反而是成为具体赋予人类思考及生活形态的人类实际构成要素。人类的实际情况从历史性来看虽然不能称为永恒的,但是人类的实际存在却也是不可或缺的。如果可以说天主成为了人,这就意味着不可以无视人类的情况而只接受人性。天主的降生就是意味着成为人,同时也指接受了围绕人类发生的所有情况。因此天主并不是将人类隔离了历史,社会,政治,文化而成为人,而是救赎人类本身及全体,这就是指救赎包含人类的所有东西,即与人类相关的所有东西。因此说到现在的传教,就是不断与人类新发生的情况相呼应来进行的。在中国这个新的文化圈中,利玛窦在适应主义观点下是不进行传教。他并不是无条件地强调对耶稣的信仰,也没有建立和当时状况无关的教会。他的传教方法论更明显地反映了他的创造论观点和神论观点。[133]他试图在存在于世间的所有事物上发现天主,也有人认为利玛窦对于神学的忠实性抱有过分疑问态度,但是如果他不忠实于自己的神学世界的话,中国人也就不会有厌恶的批判声音了。
他对于朱子学、道教和佛教过分批判的态度在今天也受到着批判,但是如果从当时他的神学立场来看,对利玛窦而言,这些宗教都不是以被肯定的面貌展现出来的。[134]
三、朝鲜天主教会建立与珍山事件
(一)天主教会的建立与祖先祭祀禁令
韩民族第一次接触到基督教可以追溯到16世纪,但这只是从个人层面上或是因特殊事件而接触到的,即到16世纪末,壬辰倭乱时接触到的和倭军一起来到朝鲜的西洋传教士,以及在17世纪中叶丙子胡乱时被抓为俘虏的昭显世子和J. Adam Schall von Bell(1582-1666)接触并在之后将各种书籍和圣物带回朝鲜等事件。但是形成一个团体并以教会来表明基督的信仰是自1784年李承熏在北京接受洗礼并回到朝鲜之后开始的。[135]在朝鲜接受和信奉天主教是从18世纪末叶应时代的要求而开始的,主要由星湖学派的实学者们主导的。[136]但是将没有外国传教士介入的西学当做学问来研究之后,最终开始将天主教当做信仰来信奉,在朝鲜打下天主教基础的天主教会的创立者,即西人学者们因为想要将天主教教理和儒教教训结合起来,所以采取了补儒论或合理论立场。其中的代表人物有李檗,丁若钟,丁若镛等人,他们的补儒论或是合理主义态度从理论上说服了当时的学者并使他们入教。他们确信天主教对那些儒教没有明确提出的人生问题,像是对人格神的信仰,灵魂不灭,死后来世等问题都提出了明白的教导。[137]
对他们而言在涉及到信仰实践问题上还有很多没有解决的问题。因此他们为了寻求弥补他们不足之处的帮助,在1790年8月为了迎接清高宗乾隆帝八旬节的使节团中,去探访北京教会的尹有一从北京的汤士选(Alexander de Gouvea)主教那里得到了派遣传教士到朝鲜的约定,并得到了北京主教关于典礼的答书后于10月份左右回国。在这样的状况下北京的汤士选主教在给朝鲜信徒的答书中是这样传达祭祀禁令的。
“1790年朝鲜教会对我提出的问题中有‘供奉祖先的牌位或已经供着的牌位可以保存下来吗’这一条,我根据教皇本笃14世的会规‘Ex quo singulan’和克莱孟11世的会规‘Ex illa die’中提到的关于教皇厅的明确决定给与了否定的答复。[138]
(二)珍山事件与朝鲜天主教镇压
为了遵守祖先祭祀禁令,在全罗道珍山生活的尹持忠和权尚然停止了对祖先的祭祀,并烧毁牌位将其埋入地下,而且1791年5月尹持忠的母亲权氏去世,虽然他们都维持了所有的礼仪并在8月操办了葬礼,但当时并没有制作牌位,也没有进行祭祀。结果参加葬礼的亲族和乡亲们认为他是隐藏人类自然情感和不孝的人,并向国王举报他是叛逆者。[139]不仅如此,这件事最终成为了全国性的问题,下至馆学儒生,上至大臣宰相,当时的知识阶层通过上疏和通文表达了自己的认识,即天主教是无父无君,悖论乱常的邪学,理应连根铲除。
正祖[140]虽然不愿让事态进一步扩大,但是也不能将违反国策的人置之不理,更何况认为其是大逆罪人的上疏也接二连三,在对天主教怀着善意的左相蔡济恭也同意处以严刑之后,正祖下了处于死刑的命令。他们在同年的12月被执行死刑,珍山郡被降级为县,权日身和李承熏等其他信徒也受到审问,并对天主教下禁止令,以及将所有与西学有关书籍都焚毁的命令。特别是西学书籍的焚毁令直接阻挡了士大夫阶层接触西学书籍的途径,与其说是对天主教进行合理和理论性的批判,不如说是成为了对那些被视为异端书籍直接采取压制和处理的强制政策的借口。
这个祭祀禁令是在勉强天主教徒在孝道或尊敬天主,不孝或叛教,现世的生活和死后的天堂中做出必选其一的选择。因为这个禁令发生了珍山事件和辛酉迫害[141]等,充当教会中枢的人们也因为对废祭令的排斥而离开了教会。
(三)天主教与儒教的冲突
天主教和儒教之间的关系从对理想和伦理的讨论转到了对生死的论争,天主教徒也开始被当做社会和国家的非国民。但是在珍山事件之前,儒学家们对天主教的批判是立足在理想和伦理方面的,天主教徒也采取了补儒论的立场,所以理想的对话和理解是有可能实现的。但是天主教会的祭祀禁令使天主教徒被打上了悖论乱常的烙印,使得天主教被禁止,西学书籍也被焚毁。另一方面在天主教会内部,支持补儒论的学者信徒们脱离了教会,与处于支配阶层的庶民大众对话的道路也被阻挡,儒教和天主教只剩下了你死我活的对决和争斗。
焚主废祭[142]使得天主教徒被看做是反社会反国家的危险势力,周文谟神父的入境,柳恒俭兄弟的西洋船舶进入,以及黄嗣永帛书事件更加深了民族的危机意识。[143]在这样的状况下,对天主教的禁止不管怎么看都是自然而然的处置,因此持续了一个世纪的惨事被正当化了,也给其提供了充分的借口。
四、教皇厅对祭祀禁令的放宽及传道本土化的确定
(一)有关中国仪式的教令
如上文所说,2百年间被严格禁止的祖上祭祀问题使中国和朝鲜的天主教本土化基础成为泡影,同样断绝了东西方文化的交流道路,此后进入20世纪才迎来了迟来的解冻期。对于祭祀问题的第一个挑战是1933年在满洲国发生的。这个新生国家想要实现民族的团结,便将对孔子的崇拜义务化,因此天主教徒遭到了信仰的危机。慌张的教会当局向政府质疑孔子崇拜的性质,政府回答其并不是宗教性的,只是国家和社会的仪式。以此把本土化的政策定为传教基本方向的教皇庇护11世在1935年允许尊孔仪式,接着1936年日本的神社参拜也因日本政府辨明其只是单纯的社会国民性仪式而得到许可。
教皇庇护12世在1939年12月8日通过关于中国仪式的教令全面许可尊孔仪式,虽然对祖上祭祀并没有全面许可,但已经采取了相当宽容的措施。即“在尸体,死者葬礼及在单纯记有名字的牌位前磕头,以及表示其他民间礼貌都是合理的”,也废除了传教士对中国仪式的书面规定。[144]但是也有这样的说法,即“教皇本笃14世的规定中禁止关于中国仪式的论争,并在最近的规定不变更其他内容,仍具有效力”。[145]
遵循前例韩国主教团关于祖先祭祀所采取的比较具体的方针。[146]
(二)第二次梵蒂冈公议会
对于祖上祭祀禁令的放宽如果没有实现神学上的辨明和福音的本土化是没有什么大意义的。1939年发表的教皇厅文献和关于此的韩国主教团的教书没有什么大的差异,也不是对祭祀的公认。与此相反,第二次梵蒂冈公议会和典礼宪章特别宣布了对祭祀的公认,承认了其具有实效。这个宪章关于祭礼只允许了采用什么方法或类型,对于这个允许的界限却没有提及,这也是为了不违背信仰教理或是反对正确的敬神礼而鼓励积极地研究和活用各个民族的文化和风俗。
(三) 教皇厅最新的传道战略
2010年为了迎接利玛窦逝世400周年,教皇本笃16世给利玛窦诞生地——Macerata的主教Claudio Giulidori寄了如下信件:
1522年10月6日诞生的耶稣会会员利玛窦是一位有着坚定信仰并学识渊博的人。他在自己的生涯中一段很长的时间都在致力于东西方的有效对话,并为了开辟两者之间的道路而献身。同时他明知在中国人的文化中宣扬福音不是易事却仍旧坚持,他的模范作用在今日西方与中国的文化交流中仍发挥着影响。回顾他集中大量的文化活动,只能为他特别的革新力感到惊奇,他十分尊重中国文化,并大量集中地接触了中国的传统。他可以说是实现了文化上的方法论及教会战略的人。一方面基于对中国优秀习惯的尊重。中国人能够接受基督教的信仰,也并没有让这一类新的基督徒抛弃他们文化的必要。另一方面,另一方面,这是基于他得到的启示,源于他对这些传统习惯的高度评价和补充意识,就是由于这样的确信,利玛窦在福音和希腊-罗马文化的相遇之中实现了教父们应该做的。在中国,利玛窦进行的基督教本土化事业是十分有先见之明的而且他还一直追求着与中国贤者之间的探讨。[147]
依据上面的书信,利玛窦卓越的功绩在今天依旧发挥着很好的模范作用,教皇本笃16世认为利玛窦的基督教本土化事业可以与初代教会的教父们相媲美。就如同教父们为了把福音的种子播撒到希腊-罗马文化的根基中而努力一样,利玛窦也为了把基督教的福音播撒到中国文化传统中而努力着。即利玛窦所做的是忠实于教会传统的。[148]
(四) 要求教皇厅为祖先祭祀禁令道歉
从2012年10月15日到18日为止,在首尔方济各的教育会馆中韩国殉教福者圣职首都会所属的殉教精神研究所主办了关于“殉教”的国学术大会。在这里Shim sang-tai Monsignor[149](심상태몬시뇰,Christ 思想研究所长,1940~)主张教皇厅应该为1790年发布的“祖先祭祀禁令”道歉。根据他的主张,欧洲帝国用炮舰侵略亚洲等第三世界时天主教传入亚洲,那时候教皇厅颁布的“祖上祭祀禁令”是文化和宗教层面上的帝国主义,还要求教皇厅应承认自己的错误。
他指出对造成韩国教会创立者大量殉教的“祖上祭祀禁令”,“从教会当局没有听到任何神学或教会的辨明”。他认为对父母及祖先的尊敬和对天主尊敬并不是需要“二者选其一”的事,因为“对父母及祖先的至诚尊敬可以看做是对顺应天命的天主尊敬的真正表征”。而且他批判,韩国教会的创立者们“因为努力在朝鲜建立教会而面临死亡”,但是因为无法高度认同在教会的欧洲文化氛围中形成的教理精神,或者是不遵守充满着欧洲优越主义气息的祖上祭祀禁令,就被认为污蔑为“叛教”,并将其从施福施圣的名单中去除。
五、对祖上祭祀的现代再解释
(一) 祖上祭祀的现代意义
现在的韩国社会在现代产业化的过程中,农本主义的社会体系和大家族制度解体,以工商业为主的社会体制和小家庭制度逐渐形成。传统的价值体系崩溃,在新的价值体系还没有完全建立的时候,社会处于混乱和变革的漩涡之中。在这样的混乱漩涡之中很多人连自己的生命以及存在的价值都无法意识到,没有归属感和根源意识的彷徨,与父母之间的羁绊被断绝,人们陷入了只致力于追求个人幸福的个人主义幻想之中。没有深刻的根源意识,让人们意识到自己生命的尊严感变得困难,也更难认识到其他人生命的珍贵之处。因此忘记给与生命的父母和祖先,不对父母感到感谢并报答父母的人是看不到生命根源的,对人类的父母——上帝也不会真心侍奉,也决不会对他人和社会真诚地奉献。在这样的现实之中要让人深刻认识到同生命根源相一致的生命的尊严感,祖先祭祀具有让人报答父母之恩和加强亲族纽带的重要意义。
(二) 朝鲜传统祭祀的意义
韩民族从古时起,就有将死者送葬的传统,不仅如此还要穿丧服服孝期,以及祭祀祖先等习俗。生者和死者在死后仍旧维持着和死者生前的一样的关系,这种风俗是源自于家族共同体意识。[150]之后以仁孝思想为根本的儒教典礼使韩国固有的丧葬仪式更为体系化,也使得丧葬仪式所包含的意义更为深远。到了朝鲜时代,儒教成为朝鲜信奉的国教,《朱子家礼》中记载的儒教式丧葬仪式,不仅仅是士大夫,连普通庶民都引为标准。通过这种丧葬仪式,儒教思想也在韩国留下了更为深远的思想印记。
儒教中孝的根本精神是报本和报恩,这是对于无条件给了我们最珍贵生命的父母和祖先的报答,是对他们无限的爱与恩惠的感谢。而源自于这份报本与报恩之心的孝具体表现为三种孝道的实践形式。[151]
第一种就是以恭敬之心好好保护自己的身体。[152]
第二种是不仅要让父母的衣食住行没有不便,同时还要以愉悦的心情来奉养父母,以真诚来实践父母的意愿。[153]
第三种是要立身行道,扬名于天下,使父母得以荣耀。[154]
这样的报本和报恩不仅是在父母生前,在父母死后也依然通过丧葬仪式来表达对死者的奉养,就如同生前一样。
(三)祖上祭祀和天主教的圣像崇拜
在当时对祖上祭祀的理解和视角,天主教会和儒教人士之间还是存在着相当大的差异。儒教人士们认为祭祀的根本意义相比较是神灵的歆享,更确切地说是子孙的报本和报恩,是“事死如事生”的继孝,而反面,天主教会则将神灵的歆享认作是儒教祭祀的目的,并依据固有的生死观和来世观判断死后的灵魂是无法歆享祭祀的而将祭祀废除。
所谓的祭祀是指只对上帝进行的仪式,把对祖先进行祭祀的行为视作异端来判刑是因为受到了西欧基督教中文化优越主义的影响,西欧基督教受到旧约伊斯兰的祭祀观的影响,对祭祀定义的要求也扩大到了其他文化圈当中。这既是一种封闭的态度,也可以说是非天主教的态度。但是如果在天主教礼典中有机地吸收儒教祖上祭祀的话,不仅对弥撒圣祭和基督信仰的纯洁性无害,反而有利于丰富其意义。
在天主教中侍奉尊敬圣像不是将其当做神或者圣人来尊敬,而是在实际的信仰生活中,在面对着圣像的每时每刻都能够轻易联想在我们身边存在着的基督或是天上的圣母,圣人圣女们,这样我们的恭敬和诚意也能够更有效地表达出来。因此牌位的作用也不是指其中有着神灵的魂魄,只是通过牌位来重新帮助我们记忆联想而已,认识到这个并且将其和迷信正确区分开来的话,我们就能够充分地应用这种方法。
祖上祭祀的根本精神是报本和报恩,这也就是对上帝信仰的根本。信仰的理由就在于要感谢和报答给与了我们珍贵生命以及无限爱的上帝。祝福,心灵的平静,以及死后天堂等都不是直接的目的,这些都是随着报本和报恩而来的结果,是礼物也是祝福。在这样的意义下,祖上祭祀所包含的报本和报恩的精神就是基督教信仰生活的根本,是对上帝的感谢和报答的最好的生活上的反映,同样的,报本和报恩的精神对基督教徒而言是帮助他们克服诱惑的,使他们免于陷入求福和祈福的信仰生活。
结论
17世纪初,为了在中国实现基督教的本土化,以利玛窦为中心,耶稣会的传教士们通过艰苦卓绝的努力完成補儒论和适应主义战略,向中国的学者和一部分官僚传播天主教并施以洗礼,以此开始了东西文化的融合。利玛窦死后,他的补儒论神学态度因其文化上的理解差异在耶稣会内部以及其他的传教团体中和适应主义路线一起遭到了批判,教皇厅对于东洋民族的利玛窦式本地化宣教战略也随之改变了。
1790,朝鲜收到的“祖先祭祀禁止”命令并不是单纯地只对禁止祖上祭祀产生了影响,就像珍山事件,辛酉迫害等无数无辜的人为此付出了流血的代价,我们要关注的是朝鲜的基督教会在此后100多年间所面临的极端迫害,以及基督教会和朝鲜末期社会断绝了关系这一事实。众所周知,由此教会和国家之间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无法维持正常的关系,而且由于长时间的迫害,在教会建立初期所形成的哲学性·神学性·宗教学的氛围被打破,为此需要注意的是,今天我们的教会只是西欧教会的变形。不仅如此,“祖上祭祀禁令”不仅否定了曾经在中国活跃着的耶稣会的传教事业,也让欧洲中心主义·封闭性的世界观在中国和朝鲜扩大开来,还留下了很多需要治愈的伤痕。
首先,通过宗教哲学性的“祖先祭祀制度的现代性再解释”来进行正确的“祖先制度的确立”是十分必要的,在造成流血的各种迫害中,因为祖先祭祀问题而不得不背教的人员,他们位置的再确立,以及儒教和基督教的调解等问题,为了解决这些问题,Shim sang-tai Monsignor(심상태몬시뇰)要求教皇厅为1790年施行了“祖先祭祀禁止”令而道歉是有一定道理的,教皇厅的道歉也将给亚洲福音的本土化带来新的契机。
祖上祭祀问题让我们得到一个历史教训,即对教皇厅和传教士而言,正确理解传教地文化是一件重要且困难的事,并且应当了解地区教会和该民族才是应成为福音本土化的主体。
(翻译:王慧,南京大学韩语系硕士研究生。)
比较方法论
止观与坐忘与居敬
——三教的身心技法
(日)三浦国雄[155]
内容提要:本文站在收心法的层面上,通贯儒释道三教考察了敬•止观•坐忘三种身心修养工夫的关系及其异同。首先在智顗的天台止观中,止(定)是指向心之内境的沉静意识,观(慧)则是朝向外境的观察意识。其次在司马承祯的坐忘论里,虽受天台止观的影响,但将观与心之收敛(止)合一了。最后朱子学中的居敬•穷理说在心理构造上与天台止•观说相通,止观中的坐禅也成了道学家的静坐法。但理气二元论的立场决定了道学中必须将养生法与收心法区分开来。
关键词:止观 坐忘 居敬 三教 身心技法
一、止观
首先,我们分别列举出敬•止观•坐忘之三法来作为代表儒•佛•道的收心之法,对此不会有异议吧。居敬指在朱子学中与穷理并列场合下的居敬,止观是指智顗天台止观中的止观,坐忘虽有种种,这里是指司马承祯的《坐忘论》中所表明的坐忘。这些虽然已有个别的论述,但站在收心•安心法的层面上,通贯三法来考察的可说几乎还没有吧。此三法虽说都是站在如何处理心的这一共同问题意识之下,但由于三教思想内容不同,一般的看法是认为此三法当然不可能是同一性质的吧。然而它们果真相差那么悬殊吗,难道完全没有相互关联吗,上述诸点都必须超越宗派来重新予以追问。从成立时代来看,居敬是宋代的,止观是隋代的,坐忘则是唐代的,因此按时代顺序首先从止观开始讨论。
因为笔者在佛学方面是一个门外汉,所以决定首先依据手头的佛教辞典来把握止观的大体梗概。
止观 止是梵语samatha(奢摩他)的翻译,观是梵语vipasyana(毘鉢舎那)的翻译,是指停止种种思绪而将心思贯注(止)于一个对象上,从而生起正确的智慧以观察(观)对象。即是定•慧之二法,又称为寂照、明静等。此二者与戒一起被作为佛教徒的重要实践,以阿含为首的诸经论中讲得很多。止与观相互使对方得以成立,以使佛道得以完成,因此处于不离的关系之中。[156]
要补充一点的是,宗密的《禅源诸诠集都序》的开头,在关于“禅”的解说中,与“定慧”一起还列举有“禅那”(音译)、“思惟修”“静虑”等。
这样,从其对应的梵文存在也可得知,止观是印度传来的修养法,即使在汉译佛典中,不仅在长•中•增一等《阿含经》、《瑜珈师地论》《大乘起信论》《净土论注》等里面频繁出现,而且僧稠这里也有《止观法门》的著述等,似乎是中国佛教史的常识。天台智顗(538-597)在“止观”二字的基础上重编了从前小乘系的禅法,将其体系化为大乘圆教的实践方法。这也是众所周知的。[157]正如《天台小止观》[158]的序中,
夫泥洹之法,入乃多途。论其急要,不出止观二法。
一语道破的那样,在天台这里,“所谓止观是佛法的总称,即是其全部”。[159]
据说智顗从其师南岳慧思(515-577)那里得以传授了渐次、不定、圆顿三止观,在其晚年讲述圆顿止观的《摩诃止观》中,可以看到由相待止观向着绝待止观的展开。然而在本文中不可能祖述智顗如此复杂宏伟的止观法门体系,而且那也不是本文的目的。这里首先最简要地概括介绍一下有明确解释的《天台小止观》正修行第六,然后从《摩诃止观》等那里补其不足,只是提示出智顗止观说的框架。
智顗在本章的开头,把修止观的场合,大致区分为〔Ⅰ〕坐中(坐禅)与〔Ⅱ〕“历缘对境”、即日常的行住坐卧场合。不仅坐禅的静里,日常的动里也作为修行的场合,这在中国思想史上是值得注意的吧。如后面所述,这种朝向动里的视点,无疑给予了“贯动静”的道学——朱子学修养法的居敬以某种程度的影响。
首先关于〔Ⅰ〕,在把问题整理成以下五项之后,再来具体说明与其各自相对应止观之六法。
(一)对治初学者的心之粗杂与混乱的止观。
(二)对治心之沉浮的止观。
(三)随方便权宜而修之止观。
(四)以禅定中的微妙心为对象的止观。
(五)为保持定与慧之平衡而修之止观。
对于上文之(一),提示了以下的三种止法与二种观法。首先,三种止法:
①系缘守境止。心系留于鼻端或脐间等特定部位,使其不至于散漫。
②制心止。随心之动,立即制御使其不至于驰散。
③体真止。一切诸法皆是随心所念时产生的虚妄之物。制止心执着于此种无自性的空物则妄念消灭。
其次二种观法:
①对治观。诸如依据不净观(将人体想象成不净之物的方法)来对治淫乱之心种种。
②正观。即一切诸法皆是心所造成之物,而心之念也是对此诸法而起之物。现在向后观察那种心自身的话(反观),则可知心是无生无灭无所把捉之物。明白那个的话,则身心皆寂然而得正定。
其次关于(二)。在坐禅中若其心模糊闭塞的话,则修观以照心。其心浮躁时则修止以止之。
其次关于(三)。虽已修观而心仍不能明净的话则用止,虽修止而仍旧不行之时则用观(这里把心视作一种黑匣子)。
其次(四)。扰乱之心安稳平息,进入禅定境界的话,觉身之空寂,感到快乐。此时,知那禅定之心亦是虚妄之物,则修止以使不生爱执着于它。然如修止而心之执着仍不止的话,接着就以观来观察禅定中的微妙之心。
其次(五)。禅定之中,如观慧的作用欠缺的话,则成“痴定”而不能切断烦恼。又即使心豁然开朗而智慧分明,若定微少则心散漫,就如同风中的灯火一样照物不明。只有得定心,方能如密室中的灯火一样破除黑暗而照物明了。
其次关于〔Ⅱ〕的日常场合里的止观。
端身常坐(坐禅)虽是入道的最好方法,但既然人在现实场合里结成各种关系而活着,如果不随“缘”对“境”修习止观的话,则心之修行里产生间隙而一有什么事烦恼就会起来。这就是之所以一切时间中都不断修行定与慧不能懈怠的原因。
“历缘”修止观这种场合的“缘”有以下六种。一行、二住、三坐、四卧、五作作、六言语。“对境”修止观这种场合的“境”是指六尘境,指如下的六种:一、作为眼之对境的色,二、作为耳之对境的声,三、作为鼻之对境的香,四、作为舌之对境的味,五、作为身之对境的触,六、作为意之对境的法。
例如,所谓言语中修止就是这样的事。即如今因为我这样说,一切善恶等法生出,然而其中能够把握的一个也没有——如此理解的话则妄念亦不起。将其称之为修止。所谓言语中修观就是这样的事。即心之活动鼓动气息,它冲击鼓动喉、舌、牙龈而表现为声音或言语,从此生出一切的善恶等法。然试着“反观”其言语之心,不能看见其样子。因此当知言语所说及一切法毕竟是空寂。此所谓修观。
又如所谓身受触时修止,指身虽受种种感触,即知其为无实体的幻化,对其对象不起贪著或嗔恼。即知道身是由四大和合而来的无实体之物,则知感触就其本性也是虚假之物,这就是在感触中修观。
以上是《小止观》正修行第六的概要,根据以上情况,进而参考《摩诃止观》等,姑且简明扼要地归纳智顗的止观如下:
一、没有比止观更好的安心之法,此是达至涅槃的正当途径。
二、止观不只是坐禅中的修行之法,也应当是随心起念而完备具足的一切时间中之修行法。
三、止是定是寂是断,是使浮动之心静止的心之作用。观是慧是照是智,是观察对象而看穿其空无性的心之作用。[160]
四、如前所示,止以一心澄静为目标指向,是设法使心不至驰散于万境的修行之法。因此说束缚心设法使其不动不是止的本意。[161]
五、止的对象是自己的心,而观的对象则跨越内•外两境,有时定中之心其自身也成为对象。省察自己的心之动就叫做“反观”。[162]
六、止观虽是不同的二法,也是相互补足、相辅相成的二法。修行者不可偏执于任何一法。例如,定中之观,就如果密室中不摇曳的灯火一样照物了然。[163]
七、止观不仅是安心之法,作为治病法也发挥着很大的效力。止观作为全体,不论是比喻意义上还是实质意义上都是针对身与心之病的治疗法系统。[164]
为了下章以后进行比较的方便,试着将以上所述更简约化为一个模型吧。止观,将其抽象为心之二种作用的场合下,用图来说的话可以用横T字型的模型来表示吧。P是止,向下的箭头是指向零点以表示心之沉静化的矢量。姑且称其为“沉静意识”。Q是观,左右的箭头表示观的视线方向。左是内境,即自己的心,右随外境有各种朝向。姑且称之为“观察意识”。[16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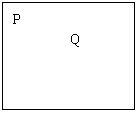
|
二、坐忘
比智顗晚约百年,唐代司马承祯(647—735)出来并著有《坐忘论》。司马承祯,字子微,法号道隐,自号天台白云子,谥号贞一。系于陶弘景——王远知——潘师正——司马承祯的这一道教谱系,是上清派第十三代宗师(依据《天隐子》),作为被玄宗皇帝授予法箓的人物享有盛名。遍历嵩山、衡山、王屋山等众多的名山,特别要留意的是他与天台山的关系很深。[166]
探讨司马的坐忘与智顗的止观之异同及影响关系是本章的目的,然而在它前面按顺序先提及一下庄子以来的坐忘吧。[167]众所周知,《庄子》里面虽然记述有心斋或丧我这些瞑想体验,但这里应当作为问题的是大宗师篇中假托于孔子•颜回的坐忘问答。在那里,从仁义或礼乐这些儒教的•世俗的价值中解放出来的状态首先表现为“忘”之一字,由此更进一步,从自己肉体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达到自由,知性的作用也终归熄灭,“同于大通”的境界被称为坐忘。
将其与上述的止观合而观之的话,使意识从仁义礼乐或者自己的肉体这种所谓“境”中脱离出来,进而将“聪明”或“知”空无化的状态与上述图P(止)的矢量要说相似的确相似。作为理想的身心状态,“形(肉体)如槁木心如死灰”的表现在《庄子》中频繁出现。然而这种坐忘的场合,设定有与境相反的一极“大通”(道),讲其与道之同化的地方,作为悟道之结构与止观相比略微性质不同。此外有决定性的不同在于,Q(观)的否定乃至不存在。[168]现在看来,在《庄子》这里知的作用被空无化了。若是智顗的话会批判其为“昏”吧。而颜回对于孔子将自己的境遇予以对象化来叙说这件事,则是因为残留了Q的视点,这种讨论也许能够得以成立,然而颜回的场合,不像在智顗这里作为意识的另一种存在形态被自觉地提起,毋宁说其自觉在于“去知”的这一否定方向上。
与坐忘很相似的道家乃至道教的收心之法中有所谓“守一”。《老子》第十章中所云“抱一”(“载营魄,抱一,能无离乎”),在《庄子》在宥篇中被转述成“守一”,并作为长生术而方法化了。即广成子与黄帝之间的那段有名的问答,广成子在所谓“空同之诫”中说“我守其一以处其和。故我修身千二百岁矣,吾形未常衰”,向黄帝传授秘诀。因为其方法是不耗费自己的精神,不仅将视觉•听觉甚至连知觉•认识的作用都予以封闭而使意识集中于“一”上,从而断绝与外界的联系,因此在实质上与前述大宗师篇的坐忘处于共同的基础之上。
后来此种守一法经过《太平经》等与存思法(想像体内神的方法)相交错,在茅山派道教中作为长生术而集大成。[169]“一”本来就应该意味着道,在《老子想尔注》中已经与道同时被象征为太上老君。[170]在极口称赏作为长生术之守一法的《抱朴子》地真篇中,“一”完全被神化了,从其名称到服色、体内的居住场所等都描述地很细致。《抱朴子》进而接着叙述说,由于体内的神数量过多,因而将其全部舍弃,只要将心思集中在“一”这一神上的话则万事了结,从而提倡一种简便的存思法。
将此大宗师篇的坐忘与在宥篇的守一,再加上道教的守一从意识的操作这一观点来进行比较的话,可说坐忘是意识的空无化,道教的守一是意识的一点化,而在宥篇的守一则兼含它们双方的方法吧。
此守一法不是作为长生术而是作为收心之法为佛教所吸收。[171]“守一不移”作为四祖道信的禅风而闻名,[172]《楞伽师资记》道信条中说明如下:
守一不移者,以此净眼,眼住意看一物,无问昼夜时,专精常不动。其心欲驰散,急手还摄来,以绳系鸟足,欲飞还掣取,终日看不已,泯然心自定。[173]
在这里,“一”不是道,当然也不是体内的神,只不过是作为使意识集中以作为入禅定的手段之“一物”罢了。同书弘忍条中也叙述了坐禅的方法,如云“尽空际远看一字”,“若初心人攀缘多。且向心中看一字”等,道信的“看一物”就是弘忍一流的工夫吧。
禅的守一与道教的守一,其所指向如收心与长生之不同,因而在方法上也存在差异。但是将这些放入意识的矢量里进行比较时,毋宁说显露出共通点来。即双方不管是体内或是体外,都是通过设定一个对象使意识集中于它,以谋求心之收敛。将其与止观相比较的话,在守一这里所见(观)同时成为心之收敛(止),非如止观那样成为一个意识(观)看另一个意识(止)这种构造。将此用模型图表示的话,如下所示P • Q应该成为一条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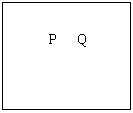
|
那么在以上前提的基础上,试着探讨一下司马承祯的《坐忘论》[174]吧。《坐忘论》分为以下七篇:
序
1 信敬
2 断缘
3 收心
4 简事
5 真观
6 泰定
7 得道
上面的顺序自然就成为修行的阶梯,至7之“得道”则坐忘的修行得以完成。这就是说到达终点为止共设置有六个路标,因此对于修行者来说可说是亲切的向导书。然而现在看来,与具备同样内容的《天隐子》(司马承祯序)等相比决不那么容易读,因此以下首先归纳一下各章的大概要旨吧。
序 人之所贵在于生,生之所贵在于道。生与道相保,二者不相离方能保证长生。故寿命之长短不在天亦不在他人,系于归道之自身修行如何。
1信敬 信与敬为道德之根蒂,是得道的入口。庄子所云坐忘是忘掉一切。内不觉其一身,外不知乎宇宙(以上沿袭郭象注)。与道冥一,万虑皆遗,同化于“大道”。惑者闻而不信,怀宝求宝,是向外求其宝。
2断缘 所谓断缘,是断绝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或者为了出人头地的操劳等有为俗事的关系。只有这样才能无事安闲,方可修道。
3收心 心是一身之主百神之帅,静则生慧,动则昏浊。故在学道的初期阶段,安坐收心,离心于境,住于无所有,不执着于一物,则心自然入于虚无而与道合一。心不执着于物而得不动是达至真定的正确基础。这样与道合一,安在于道之中就叫做归根,守根不离就叫做静定。静定长久持续的话,则到达知常的境界。知则无所不明,常则出离生死。
然不可执着于空。此空已经不是无所,仍堕于有所。又非完全止灭心之动与永远断绝知觉。若任心生起,无所收制的话,则与凡人无别。熄灭心之乱而不消灭照之作用,虽守静而不执着于空,则自得真见。
又不可左思右想,邪见与妄想当随觉而除。不使世俗的杂音入耳就叫做虚心,心不追逐世俗的世界就叫做安心。心安而虚的话,则道自然来止于吾心中。又心有病则难以进入定之门。爱见与思虑是心之荆棘,若不除去则定慧不生。
心原来依存于境,未习惯于独立自存。若离境而分开的话,心失所依赖而难以安心。因此随心生起而制御之。不问昼夜,不问行住坐卧,即使应事之时,常须有意识地使心安定。(七篇之中最长的一篇)。
4简事 “简”为断简或者简择,是选取事物。人即然活着就必然要经营于事物。因为不能与数以万计的事物全体相纠缠,所以必须按照自己的本分进行取舍。应该珍惜道德与性命,谢绝地位•名誉•财产这此在生命中无益的东西。
5真观 只有进行收心与简事,日损有为,方能观见真理。然而外物之中衣与食是营生中不可欠缺之物,因此应该虚心以接受它们,明目以应付它们。即使利用也没有得失之心,心便能安泰。
难以去除的心病,且依法观之。色病重者,色(女色)不过是想罢了,将想作为空来观。色对于身心来说何止不是切要的东西,简直就是损伤性命的仇敌。又见他人为恶,将其像自身之病一样承受,不使陷入自我嫌恶。又将贫贱观为谁的原因都不是而是我自己的业与天命,力图达到不怨人的乐天知命境界。如果生病,则观此病因我有身而生,如无身则病无所依附。而其次观心,知道心中无真的主宰者,种种裁夺是从妄心生出。如此身如枯木心如死灰的话,包括心病的万病全部消灭。
憎恶死的人作如下观吧。吾身是神之舍,此身今老病,气力衰微。如果屋子朽坏的话,人自然会离开旧屋别求住所吧。身死而神移向它处也是同样的道理。如果过于留恋于生而憎恶死亡拒绝此变化的话,则神识错乱自失正业,我的后身也将托生变成下愚贪鄙之人吧。
爱憎之心生于妄心,成为道的妨碍。从心中舍弃诸种欲望,然后返观曾经痴爱之物的话,对其自然生出嫌恶之情。如果以与境合一之心来观境的话,终生不会感到恶的存在。只有以欲离境之心观境,方能清楚看见是非。(本篇是次于3收心的长文)。
6泰定 所谓定,是形如枯木心如死灰、无感无求的寂静之极致。再连定也不执着的话,无论何时何地均可实现定。《庄子》所云“宇,泰定者发乎天光”(庚桑楚篇)中的“宇”即是心,“天光”则是慧。心虚静至极的话,则道止于心而智慧生。智慧出于本性,与其说生出智慧难,毋宁说想不使用它为难。
《庄子》中这样说:“古之修道者,以恬养智。智生而无以智为也,谓之以智养恬。智与恬交相养,而和理出其性”(缮性篇)。这里所说的“恬”“智”即是定•慧,“和理”即是道德。虽有智(慧)而不用它,以安其恬(定),养而久之,自然能成就道德。
达到定有种种方法,若成就得定的话,白刃生死名利都不能够动心。因此就如同“用志不分,乃凝于神”(《庄子》达生篇)所说。心是如此灵妙之物,其调御之难非马或鹿可比。
7得道 神异之道宿于人时,由其强大的影响力而身心起变化。形得道则纯化而与神(精神、气之灵妙者)合一,此时道•形•神成为一体。于是身成为真身,灵智作用得越来越深远,六根(六种感官)得以敏锐。将此种存在称为神人。神人超越生死,即使蹈水火也不受伤害。不过得道有深浅的差别,深者及于身而成为神人,浅者仅及于心而止于得慧觉,而身不免于死。因为慧是心的作用,多用的话则神气外泄不能达到长生。[175]近来的修行者(指佛教徒)即使听到舍形之道也不知此种即身之妙。拿他没别的办法不得不叫做愚。
以上是《坐忘论》七篇的概略。虽说是以老庄为样本,用《西升经》《妙真经》《定志经》《灵宝经》(《生神经》)这此道教经典加以润饰,但正如《郡斋读书志》中有“子微之所谓坐忘,即释氏之言宴坐也”那样,佛教的影响也不应该掩盖。李远国也指出了这一点,[176]《坐忘论》从佛教导入心乃至心理的方法以谋求道教的新生,开拓了走向下一代内丹的道路。然而在表面上却主张搬出佛教不谈的身体性夸耀“不死”,认为相对于佛教处于优越地位。
关于其与我们的课题天台止观之间的关系,似乎从宋代开始两者的共通性已被觉察出来了。例如,“平生坐忘论,字字欲铭膺”[177]般地讴歌并爱读司马承祯《坐忘论》的南宋陆游就留有如下诗句:
司马遗书有坐忘
顗翁止观略相当[178]
又以下是蒙文通《坐忘论考》已经引用的资料,司马承祯《坐忘论》的定慧的观点与天台止观“相表里”,南宋的叶梦得《玉涧杂书》中也指出此点。[179]北宋的张耒也就“守一”说“智者得之为止观,司马子微得之为坐忘,皆一道也”,[180]一边又颇为偏爱道家•道教,并提及守一•止观•坐忘的连续性。
关于其连续性的内容,注(11)(译者按:指全文的第11条注释)所引神塚淑子的论文中也进行了考察,实际上大略望去的话也能发现不少共通点。例如,《坐忘论》第二断缘章中所论述的与《摩诃止观》卷四下所云“息诸缘务”(大正46—42下)相对应,前引《坐忘论》第三收心章的“盲定”与前述止观的归纳四相对应,同样收心章所云“守静而不著空”,即不要坐入空里不走的观点,所谓作为空假中的论理都在《摩诃止观》里随处予以表明。还有收心章所云“(心)随起随制”几乎原样见于《天台小止观》正修行第六(岩波文库本94页)等等,不胜枚举。
这样来看的话,正如神塚论文中所云,虽可推测其是觉悟《天台小止观》而作,但作为其最根本的影响,笔者想列举天台的“止”与“观”。这些形成了《坐忘论》的框架,从第三收心章、第五真观章、第六泰定章这种结构布置也大致能察觉吧。虽然只有“止”这一语没使用到,但构成《坐忘论》之核心的这三章中论述的主题,正如章题所暗示的是“定”(止)与“观”。即第三收心章中处理“定”,第五真观章中论述“观”,第六泰定章中不仅论及“定”,而且还讨论了“定”与“慧”(观)的关系。
如前所见,在传统的坐忘法中,虽有“定”却无“观”或“慧”的观点,毋宁说它被视为妨碍“定”的东西了。司马承祯的坐忘法中导入“观”[181]或“慧”是受佛教定慧或者天台止观的影响吧。这种观点无疑使司马承祯从《庄子》中发掘出“慧”。令人想起司马承祯分别以“天光”对应“慧”,以“恬”对应“定”,以“智”对应“慧”(第六泰定章)。
然而,也是重要的一点,在司马的《坐忘论》中“慧”的力量被压制得很微弱。如前面所讨论过的,对“慧”的过多使用予以了告戒,甚至有将其与“定”对立起来理解的章节(泰定•得道章)。如前而已经引用的,应当说是《坐忘论》附录的《坐忘枢翼》[182]中有如下一节:
勿于定中急急求慧,求慧则伤定,伤定则无慧。定不求慧而慧自生,此真慧也。
尽管尚未到达“慧”的否定,然而《坐忘论》中很难找到如同天台止观中那种“止”与“观”的互补亲和力。此外,譬如说观察意识的意识,内观“定”的“慧”之观点也没有。《坐忘论》第五真观章中,虽有能死盯着自己的欲望或种种病的眼,却没有注视着定中之吾心的眼之深度。司马承祯的《坐忘论》虽然受佛教的定慧(止观)的影响,但从根本上依然固守着庄子一流的坐忘法传统不放。将其用我们的模型图来表现的话,可以描绘如下吧。虚线表示力量的微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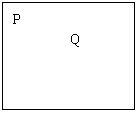
|
三、居敬
关于如何控制难以制御之心,在儒家中也早已引起关注,心之调御法占据了其教义的重要领域。《孟子》的求放心说、存夜气说、《大学》的诚意说等,作为与心性论相应的实践论的收心之法也有不少。但是在儒教史上,要求具体的收心之法,回应它而配备指南的,不管怎么说都始于道学勃兴的宋代。
经历唐末的变革而被推上时代前台的士大夫,自觉到其对于皇帝与人民及社会的责任。应时代的要求重新激活了“修己治人”这一儒教的纲领。关于收心之法虽然已经在佛教这边积累了高度的技术窍门,但在士大夫看来,它们只不过是断绝与人类或社会之间合作关系的自闭之物罢了。一边要保持与外物之间的关系,一边又要确立自己不动摇的主体性(用当时的用语来说即“主”)的话该怎么办好呢——这是生活在这个时代真诚的士大夫们迫切关心的事情。其代表人选之一的程伊川如下指出:
学者患心虑纷乱,不能宁静。此则天下公病。学者只要立个心,此上头尽有商量。(《程氏遗书》[183]第十五、47页)
这里举出为“天下公病”的“心虑纷乱”所烦恼的一个人物的轶事吧。即记载在《程氏遗书》中司马光的故事。
君实(司马光之字)尝患思虑纷乱,有时中夜而作,达旦不寐,可谓良自苦。人都来[184]多少血气。若此,则几何而不摧残以尽也。其后告人曰,近得一术,常以中为念。
程子附上了对司马光的此种收心法的评论,批判说无形无影的“中”怎么念得它,这样反而让心被“中”扰乱了。于是程子给司马光一串数珠告诫他用之代替“中”,但据说司马光并不想接受。(《程氏遗书》[185]第二上、25页)。
虽然将具备敏锐的异端感知嗅觉的道学家与数珠相配很有趣,但他们决不是承认佛教的收心法。程子对于吸引当时许多士大夫的坐禅入定如下批判道:
学者以屏知见,息思虑为道,不失于绝圣弃智,必流于坐禅入定。夫鉴之至明,则万物毕照,鉴之常也。而奚为使之不照乎。不能不与万物接,则有感必应。知见不可屏,而思虑不可息也。欲无外诱之患,惟内有主而后可。主心者,主敬也。主敬者,主一也。(《程氏粹言》第一、1191页)
对于后半部分的“主敬”留待后述,前述庄子的收心法“槁木死灰”也依据同样的道理而被定罪。即心本来是“活泼泼地”东西,为了切断“思虑纷扰”而最终狂突进入“槁木死灭”的话,便与矫正牛角却把牛杀了一样,因为这意味着作为“活物”的人类存在的死亡。[186]
虽说现存的资料中虽然找不出道学派提到天台止观,但对于司马承祯的《坐忘论》,则有程子虽然简短的批判言论残留了下来。如下面两段文字即是:
司马子微尝作坐忘论。是所谓坐驰也。(微一作綦。)(《程氏遗书》第二上、46页)
未有不能体道而能无思者。故坐忘即是坐驰。有忘之心乃思也。(《程氏遗书》[187]第三、65页)
前者是程子兄弟中谁的话没有明示,由于后者是程伊川的话,前者作为伊川的话大概也是可以的吧。总之程子是将坐忘视作“坐驰”来批判的。“坐驰”也是出自《庄子》人间世篇之语,是说心无着落四处奔走的样子,[188]这便成了用《庄子》的话来批判《庄子》这种嘲讽式的批判。南宋的罗大经论及程伊川奖励学者静坐时,说表面看起来似乎静,其实里面也有“未免胶扰者”,这正是所谓“坐驰”。(《鹤林玉露》人集卷三“静坐”)。
那么,为什么把坐忘视为“坐驰”呢。其回答在上述程子后面的话里表示了出来。在预设了“未有不能体道而能无思者”这一前提下,做不到那样的不成熟的普通人即使实行坐忘,却因为在坐忘中如果没有想要忘掉的念头——意识的作用的话就不能够达成,所以修行者不断地附着纠缠于“思”而不能达到“忘”——总之,作为修行法的坐忘在构造上可以说是自相矛盾着的。[189]
再稍微检讨一下程子的这个《坐忘论》批判吧。下面所引程子的话[190]虽然不是直接提及《坐忘论》,但其内在的关联性则难以否定。
今志于义理而心不安乐者,何也。此则正是剩一个助之长(《孟子》公孙丑上)。虽则心操之则存,舍之则亡(《孟子》告子下),然而持之太甚,便是必有事焉而正之(公孙丑上)也。(《程氏遗书》第二上、42页)
这里援引《孟子》有名的“揠苗助长”的故事说明心之“存亡”的问题。想要收心也不可过分在意(助长),话虽如此,完全把修养不放在心上(忘)当然也不好。因此就成为所谓“‘勿忘’‘勿助长’之间,正当处也”(《程氏遗书》[191]第三、62页)。关于其间的情况,楠本正继氏的以下解说非常恰当。
所谓勿忘是指不要忘记功夫,勿助长是指避免意图安排。因此这是不放弃功夫,而且还超越它,来保持其自然性的,[192]极其微妙的境界,即易所谓“神”的境界。
(《二程子论》)[193]
为明确起见来说的话,这里所说的“忘”与坐忘的“忘”内容不同。一方是说不要忘记,另一方则是所谓要忘记的其“忘”的对象,前者如前楠本氏的文中也指出的是“功夫”,与之相对,后者则是“境”吧。
那么,要说道学家自身思考的是怎样的修养法的话,首先可以举出道学的开创者周濂溪的主静主义或无欲主义。周子对于它们的具体方法没有留下任何记载,又作为修养法的主静主义虽然被后来的道学家认为佛教•道教也有而加以回避,[194]但它们对于道学派的收心之法带来决定的指导方向的事实是难以掩盖的。“主静”虽被“居敬”超越,但正如道学家始终也没有舍弃静坐法这一事实清楚地显示出来的,道学派修养论的基调里仍然流淌着“静”。他们嫌弃“定”的佛教气味而以《易》艮卦中所说的“止”来代替它,[195]然而我想要说“止”与“静”相隔甚远的话也是不可能的。因为那样的话夫子自己写《定性书》[196]是想说什么呢。
引子很长了,那么接下来试着检讨一下“居敬”吧。因为“居敬”与“穷理”成对,所以首先提一下“穷理”。众所周知,朱子受程伊川所谓“涵养须用敬,进学则在致知”(《程氏遗书》第十八)的纲领所引导,将儒教的修养法总括为“居敬”与“穷理”之二本,从而确立了朱子学。“居敬”不用说关系到心之涵养,“穷理”则是理的探究,还有以此来对经书的文脉进行如下二分的见解。[197]
居敬 穷理
敬以直内 义以方外(易)
约礼 博文(论语)
尊德性 道问学(中庸)
正心诚意 致知格物(大学)
存心养性 尽心知性(孟子)
这样就可以说朱子通过提炼出“居敬”与“穷理”两个整理了到其为止的儒教修养法。此种情形使人想起前面章节讨论过的智顗的“止”与“观”的树立。不仅如此,将此儒•佛的修养法放在对立的位置上来看的话,在其中注意到居敬=止、穷理=观这种对应成立吧。关于居敬与止的关系我想后面再论述,而说起穷理与观的对应的话,尽管佛教的知与儒教的知的构造与作用不能同样看待,但在明确对象以观的这一点上两者底层难道不是共通的吗。穷理是对内在于一事一物中之理的探究,因为其理已经森然具备于吾心之中(《孟子集注》云:“心者,人之神明,所以具众理而应万事者也”),反照吾心也成为穷理之事。朱子也称此为“反身”,[198]此语又使人想起《天台小止观》中所说的“反观”。无论如何,朱子说的穷理的矢量就是这样指向内外两境的。
朱子把居敬•穷理比喻为鸟之两翼车之两轮,这本来是《天台小止观》使用过的比喻。并且在其场合下,依此比喻来把握[199]止与观二法是很重要的。朱子就居敬与穷理是二本同时也是紧密不离的一本工夫,不断唤起门人的注意。例如:
主敬、穷理虽二端,其实一本。(《语类》卷九、239頁)
学者若不穷理,又见不得道理。然去穷理,不持敬,又不得。不持敬,看道理便都散,不聚在这里。(同上)
这样来看的话,居敬•穷理这种宋学的修养法,是像司马承祯的坐忘法那样在天台止观的影响下成立的——如果那样说过于武断的话,认为两者在构造上有共通点是可以的吧。然而我们对于居敬的心理构造几乎还没有加以讨论。
居敬有“主一无适”(程伊川)、“整齐严肃”(程伊川)、“常惺惺”(谢上蔡)、“其心收敛”(尹和靖)等等种种定义,实质上是以意识的高度集中为目标的存心之法。那一点上与佛教的定(止)或者道教的守一并无不同,但并非像庄子的坐忘那样让心之作用无限接近于零。
(敬)不是塊然兀坐,耳无闻,目无见,全不省事之谓。只收敛身心,整齐纯一,不恁地放纵,便是敬。(《语类》卷十二、三三一页)
这样,居敬便与庄子的坐忘不同,必须发动意识。谢上蔡的“常惺惺”即是从那个角度下的定义。
然而居敬并不限定于静坐或坐禅这些特定的身体姿势,毋宁说是贯通动•静场合的修养法,因此一切时间中行住坐卧全都成为修行居敬的场所。如前所述,在天台止观中不仅坐中这种静里,日常的动里也被设定成了修行止观的重要场所。[200]朱子将其对日常场所下遭遇事情的正•不正所作的区分也作为敬的作用,并称那种敬为“活敬”。
敬有死敬,有活敬。若只守着主一之敬,遇事不济之以义,辨其是非,则不活。若熟后,敬便有义,义便有敬。静则察其敬与不敬,动则察其义与不义。(《语类》卷十二、344页)
朱子在这里指出“居敬”中不仅包藏有“沉静意识”,也包藏有“察”,即“观察意识”。在上文的场合,“察”的对象是外在现象的义•不义(正•不正),吾心之动也成为“察”的对象,朱子用“省察”“提撕”“操”等词语来表述它。
或问:“持敬易间断,如何?”曰:“常要自省得。才省得,便在此。”或以为此事最难。曰:“患不省察尔。觉得间断,便已接续,何难之有!‘操则存,舍则亡’,只在操舍两字之间。要之,只消一个‘操’字。到紧要处,全不消许多文字言语。若此意成熟,虽‘操’字亦不须用……”[201](《语类》卷十二、342页)
这样,“省察”的观点也被包含在居敬中,这虽然应该牵涉到朱子通过居敬将静时涵养、动时省察(察识)这两条前辈的方法加以扬弃而一本化了的经过原委,总而言之认为居敬之中不仅包含“止”,也包含“观”是可以的吧。对于宋学的这种居敬,一方面也有观点认为是司马承祯《坐忘论》的主静修养法的影响。[202]但是进而举出例证的话,比如《摩诃止观》中也有“烦恼卒起即便有观”[203]一语,又“定者只一心澄静,若缚着不动是太过,若驰散万境此不及”[204]一语,与那个“勿忘勿助长之间”有相通之处,我想到底还是应该追溯至比司马承祯更前面一些。
归纳来说的话,成为如下情形吧。宋学的居敬•穷理说作为心理构造与佛教的定•慧,更进一步与天台的止•观根底相通,有以它们为模型而形成的可能性。因此,居敬(P)•穷理(Q)也与止观的心理矢量图同样可用T字型来图示吧。不仅如此,难道不可以说居敬与穷理之中有一种配套相同的PQ构造内藏于各自之中吗。姑且将其图示如下:
![]() P
P
![]() 居敬=止(定P)
居敬=止(定P)
Q
穷理=观(慧Q)
Q
四、身体技法
读天台智顗的《摩诃止观》的话,使人惊异的是为了说法而用了许多病或者药的比喻,而且它们的记载极其具体。以下任意挑选几个例子来看一下吧。
止观总持遍收诸法。何者。止能寂诸法,如炙病得穴众患皆除。观能照理,如得珠玉众宝皆获。(卷三下、大正46—29c)
神农本方,用治后人,未必并益。华他•扁鹊观时观药更立于方。所以者何。乡土有南北,人有儜健,食有咸淡。药有浓淡,病有轻重。依本方治,不能效益。随时制立仍得差愈。佛,初出世众生机熟。逗根说法,无不得悟。(卷六下、46—78b)
云何诸法共治一见。如患冷用四种药。服姜桂者去病复力。服五石者病去益色。服重娄者加寿能飞。服金丹者成大仙人。病同一种药法为异得力亦异。(卷十下、46—140a)
接触这样的文章,谁都会感觉到作者难道不是很懂得医学(特别是中医学)吗。《小止观》与《大止观》(《摩诃止观》)中为了治病特意立有一章,作者的医学知识或对疾病的关心,事实上并不是半吊子(《小止观》治病患第九、《大止观》第八上、观病患)。那么这就不是作为比喻,而是对身心两方面疾病的治愈方法所作的具体描述了,可知天台智顗这里“身”所占比重之重要了。进而应该留意的是,其治病法也系在止观的基础上建立起体系来的这一事实。这从止观方面来说的话,意味着止观不仅是安心之法,也具备作为治疗身心之病的治病法之效力。这种流动在止观底层的身体观是身与心的连续性。
在《摩诃止观》中,治病法分为(一)止、(二)气、(三)息、(四)假想、(五)观心、(六)方术。[206]而止观法门的治病法的独特之处在于全部都不用药或针灸这些手段这一点上。不用说在这里医生也没有出现,止观其本身就尽着良医的职责。而且正如《小止观》中“夫坐禅之法,若能善用心者,则四百四病自然除差”[207]所云,经常边坐禅边进行治病也是其独到之处。
其次,主要依据《小止观》介绍一些治病法吧。
在前述(一)对止法进行分类中,有这种治病法,即将心止于身体患病部位的话就可以治愈。又记载着某师之说,“脐下一寸”所在的“憂陀那”,即汉语所说的“丹田”这里,若能长时间“止心守此不散”的话,便能取得很大的治疗效果。这些是现代气功中所谓是意守法(丹田的场合是意守丹田法),其源流应当是道教的存思内观之法吧。东汉的边韶《老子铭》中,已经可以见到“存想丹田”之语,[208]同样东汉的荀悦《申鉴》俗嫌篇中也有“历藏内视”,[209]这是指“内视”内脏吧。认为各内脏中有精神作用之地位的说法早就出现在《黄帝内经素问》等古代医经中。[210]“魂”“魄”“意”“志”这些精神在道教上清派中被神化,向着体内神的存思(存想)发展开去。这种潮流反过来又给予医学以影响,被隋代孙思邈《千金要方》[211]等所吸收,结果其神化色彩又被稀释最终走向现代的意守法。
当然大小《止观》中见不到体内神或五脏神的存思(存想),但其意守法是随着道教的治病•养生法的潮流前进的吧。正因此,虽然比智顗稍迟一些,隋代巢元方《诸病源候论》(卷一、四b等)、《养性延命录》(《云笈七签》卷三二)等里面都可看到同样的意守法。[212]前引也是道士的孙思邈《千金要方》中对于五脏神又另外记载有五脏的存想法。[213]
呼吸法在天台止观中也占有重要的位置。在《摩诃止观》中,作为五事被纳入为了达到止观之助缘的二十五方便中,在《小止观》中,其五事(调食、调眠、调身、调息、调心)在调和第四中被立为一章。的确是“息为入定之门”,[214]“数息开解脱门”。[215]
关于作为治病法的呼吸,《小止观》治病患第九中记载有作为“观”之治病法的六种呼气法。据说通过伴随着六种相互不同的声音吐气,不仅可以治疗特定内脏的病,而且可以去除寒•热•痛•风•烦等方面的不舒服。此法历代修炼绵延不绝,即使在现代也作为“六字诀”广受爱好。[216]其原型也许可追溯至《老子》29章“或歔或吹”,《庄子》刻意篇“吹呴呼吸,吐故納新”,但对于呼气被整理•编纂成此六字的具体时间不是很清楚。虽也不能否定密教的影响,[217]但它的盛行是在道教世界中的这一事实是不可动摇的吧。
在《小止观》中,另外还揭示有所谓“十二息法”,[218]就个人管见所及,它作为道教文献中不常见的呼吸法,有从印度传来的可能性。
上面列举的治病法虽不过是止观全部治病法[219]中的一部分,但其中已清楚地吸收进了道教的身体技法。即使是作为例子的呼吸法,将其作为入定的权宜方法是可见于《大安般守意经》等中的小乘系技法。[220]将其用于治病的方法则是受道教的服气•行气技巧的影响吧。说起来,以“息”(气)为媒介结合心与身,将心•息•身三位一体化来把握的智顗之身体观,很难想象将其与气一元论的道教割裂开来的话还能成立。智顗的老师•慧思这里正如从“立誓愿文”中可以见到地有浓厚的道教气息,而且拥有十八洞天的第六•赤城山洞的天台山原本也是道教有名的圣地。[221]
那么,关于司马承祯的《坐忘论》,前面章节中确认了治心法中天台止观的影响。那里到底可以看到什么样的治病法或养生法呢。下个结论的话,这里完全没有写呼吸法或成长术,始终进行着专门哲学的考察,然而它本来并不意味着司马承祯这里道教的身体技法有所欠缺。只不过因为本文仅限于关于《坐忘论》的论述。但是正像蒙文通在“隋唐以后之道教诸师受佛教之影响以不生不死云长生”中一语道破的,司马承祯在此篇论议想要说的也是泰定•得道——不外乎是依据炼神•合道超越生死之形以企求长生罢了。这里当然也活跃着道教的身心连续观。
那么儒教的居敬穷理中有治病或者长生的目的吗。答案是否定的。道学——朱子学中养生或长生不可能被目的化,收心法本来虽可滑向治病法,但至少不应该公开出来。静坐虽有养生治病的一方面,事实上应该也有为了它而实行静坐的儒者,[222]但他们中的大多数都忌讳公开谈论它。朱子的《调息箴》之所以使后世头脑顽固的道学家们困惑,也是因为惧怕有养生的、肉体的要素潜入其中。[223]程子将“胎息”或“习忘”(指坐忘法吧)严格地只限定在治病或养生中,[224]以上的事例也从侧面进行了证明。在儒者这里,肉体与心——从而养生法与收心法必须是严格区分开的。
止观作为居敬穷理被改头换面,止观中的坐禅作为静坐成了道学家的方法,然而对于他们来说原则上这些方法不可能是存心•收心技法以外的任何东西。这种治心与养形(身)之严加区别的背后,正摇曳着那个理气二元论吧。
(翻译:连凡,武汉大学哲学学院讲师。)
“世界历史”与比较哲学的思想起点
——《历史的起源与目标》读后
吴根友*
内容提要:雅斯贝尔斯的《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一书以“世界历史”的视角,从人类的一体化命运来思考世界历史的起源与未来发展方向,在整体的人类历史观的思想前提下,以思辨的历史哲学形式阐述了一种人类一体化图景下的“世界历史”观念,并在此全新的“世界历史”观念下,为真正的比较哲学与比较文化研究工作提供了新的思想起点。下面将以读后感的形式叙述我对该书基本思想的理解,希望通过对此书基本思想的介绍,为当代中国比较哲学与比较文化的研究工作提供一个思想的起点。
关键词:雅斯贝尔斯 世界历史 轴心期 比较哲学 比较文化
自16世纪的地理大发现以后,东西文化就开始了真正的、实质性的接触,比较哲学与比较文化的研究工作也因之而真正开始。但在国别史的时代里,东西方的比较哲学与比较文化的研究工作基本上是在“判教”意识为主导精神下展开的。比较哲学与比较文化的真正思想起点,应当是“世界历史”的观念。但“世界历史”观念的形成却是一个比较漫长的历史过程,作为精神的自觉与观念的反映,应当是在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中首先得到系统的表达。但真正能跳出欧洲中心论,以人类的一体化命运来思考世界历史的起源与未来发展方向的,则要以雅斯贝尔斯的《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下文简称《起源与目标》)一书为标志。该书在整体的人类历史观的思想前提下,以思辨的历史哲学形式阐述了一种人类一体化图景下的“世界历史”观念,并在此全新的“世界历史”观念下,为真正的比较哲学与比较文化研究工作提供了新的思想起点。下面将以读后感的形式叙述我对该书基本思想的理解,希望通过对此书基本思想的介绍,为当代中国比较哲学与比较文化的研究工作提供一个思想的起点。
《起源与目标》一书的逻辑结构比较简明,共有三篇六章,第一编与第三编都有绪论,而第二篇没有,但第二篇的第一、二章与第三篇的第三章均有导言,而其它各章没有导言。就学术著作的篇章形式来看,并没有教科书那样的整齐划一,而体现了学术专著内容大于形式的特点。对于中国的学者来说,大多数了解雅氏历史哲学的人,对其在该书中提出的“轴心文明”的概念都比较熟悉。换句话说,在中国的学人中,大多是通过“轴心文明”的概念而知道雅氏其人的。然而,就雅氏的历史哲学思想而言,“轴心文明”的说法固然是他的伟大发明,但他在《起源与目标》一书中所表达出来的深邃的历史哲学思想,远非“轴心文明”的概念所能概括的。因此,对于《起源与目标》一书的理解而言,我们既要抓住“轴心文明”、起源、目标三个关键词,还要理解其中所表达的有关人性、技术、自由等重要思想。
一、三个关键词:轴心文明、起源与目标
雅斯贝尔斯将人类历史分成四个时期,即史前期、古代文明的建立期、轴心期与从19世纪开始的科技时代这样四个时期。与这四个历史时期相适应,他将“世界历史”的问题也分为四个主要问题:(1)在史前迈出的哪些步子对人性的影响是决定性的?(2)从公元前5000起,最初的文明是如何产生的?(3)轴心期的基本性质什么?它是如何产生的?(4)我们如何理解科学技术的兴起?“技术时代是如何产生的?”[225]
对于上述四个问题,雅氏着重回答的是(3)和(4)两个问题,进而也是本书的重点所在与精彩之见迭出的部分。
雅氏对于“轴心期”有一个比喻性的称谓,说道:“我们可以把轴心期称作两大帝国时代之间的间歇、因自由而暂停和导致最清醒的意识的深呼吸。”[226];“轴心期”的概念是要超越基督教信仰所缔造的历史哲学,“以便引出一个为所有民族进行历史自我理解的共同框架”,这个概念的具体内容即是:“要在公元前500年左右的时期内和在公元前800年到200年的精神中,找到这个历史轴心。”[227]将这个历史轴心作为“历史的分界线”,即是“我们今天所了解的人开始出现”的分界线。这个分界线简称为“轴心期”(Axial Period)。[228]“轴心期”以前的人类文明虽然也重要,但更为重要的是奠定在“轴心期”基础之上的人类文明。雅氏说:“轴心期成了一种酵素,它将人性引进世界历史唯一的脉络中。对我们来说,轴心期成了一个尺度。在它的帮助下,我们衡量各种民族对整个人类历史的意义。”[229]这把衡量标尺可以形成三个明显的区别:一是“各轴心民族”即是“那些完成了飞跃的民族,这种飞跃是他自己过去的直接继续。对他们来说,这一次飞跃如同是第二次诞生。通过它,他们奠定了人类精神存在的基础,以及所谓的真正的人类历史。”[230]二是“无突破的各民族”,“他们尽管在时间上与突破一致,但内部却依旧不受其影响。”[231]像埃及和巴比伦文化就是如此,他们在轴心期虽然很繁荣,但“它们都缺乏那种改变人类的反思的特性;他们没有在各轴心民族的影响下经历质变;它们对其生活范围外发生的突破不再作出反应。”[232]其结果是,埃及和巴比伦的文化虽然很宏伟壮丽,但我们对他们的感觉是很疏远,不像古老的中国与印度人与现代的欧洲人更接近。雅氏由“轴心期”得出一个有关人类文明史的新观念:“中国和印度与埃及和巴比伦是并列的,并且实际上只是由于它们一直幸存至今,才使它们同埃及和巴比伦区别开来,还是印度和中国由于共同参与轴心期的创造,才迈出了使它们跨越那古代文明的一大步?”[233]而这“一大步”就是实现了“突破”。三是在“轴心期以后的各民族”被划分为两部分:“在突破世界中有其基础的民族”和“与突破保持距离的民族”,“前者是历史的民族,后者是原始的民族。”[234]在轴心期实现了“突破”的民族在精神和人性两个方面表现出了新特征:从“精神”的方面说:“在突破中成熟起来的精神一旦被思想、著作和解释传送给所有倾听和理解的人,突破的无限可能性一旦变得可以察觉,由于掌握了突破所具有的强烈和感受到了突破所表达的深度而跟在轴心期后面的所有民族,都是历史的民族。”[235]
除了上述的三个方面特征之外,雅氏还特别看重轴心期“人性”方面的变化,他认为,从“人性”的方面说:“伟大的突破就象是人性的开始,后来同它的每一次接触就象是新的开始。在它之后,只有开始展现人性的个人和民族才是在正史的进程之内。不过这种人性的发端不是藏匿的、精心谨守的秘方,而是迈入到光天化日之下。它充满了对效用的无限渴望,将自己展示给一切人,把自己暴露在任何检验与核实面前……凡是被它改造的人都苏醒过来了。”[236]
“轴心期”文明的特征可以从社会现象与精神运动两个层面来理解。从社会现象的层面来看,主要有三个特点,其一,在中国、印度、和西方三个互不知晓的地区,众多哲学流派出现了。在中国有孔子、老子、墨子、庄子、列子和诸子百家;在印度出现了《奥义书》与佛陀;从伊朗到以利亚,先知纷纷出现。而希腊贤哲如云,有荷马、哲学家巴门尼德、赫拉克利特和柏拉图,还有许多悲剧作者,以及修昔底斯和阿基米德等。其二,这些哲学流派分别展开了精神传播运动。孔子、墨子和其他哲学家,游历中原,到处赢得信众,建立了学派,希腊诡辩家和哲学家到处漫游,而佛陀则在各地云游中度过一生。“在孔子受挫于魏国和柏拉图在锡拉丘兹的失败之间,在培养未来国士的孔子学塾和服务于同一目的的柏拉图学园之间,可以找出社会学的类似现象。”[237]其三,三个地区内有大量的小国和城邦,有国家对国家,城邦对城邦的斗争。中国由于周天子软弱无力,大诸侯通过征服其他小国而扩张领土。“在希腊和近东,一些小城邦,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包括波斯所征服的城邦,都享有独立地位。在印度,有许多邦国和城市。”[238]
从精神运动的层面看,主要有四个特点,其一是反思意识的产生,“三个地区的人类全都开始意识到整体的存在、自身和自身的限度。人类体验到世界的恐怖和自身的软弱。他探询根本性的问题。面对空无,他力求解放和拯救。通过在意识上认识自己的限度,他为自己树立了最高目标。他在自我的深奥和超然存在的光辉中感受绝对。”[239]不仅如此,“这个时代产生了直至今天仍是我们思考范围的基本范畴,创立了人类仍赖以存活的世界宗教之源端。无论在何种意义上,人类都已迈出了走向普遍性的步伐。”[240]
其二,人性的全盘改变,即人性的精神化。“神话时代及其宁静和明白无误,都一去不复返。”[241]希腊、中国、印度哲学家们的重要见识并不是神话而是理性的哲学见解。“理性和理性地阐明的经验向神话发起一场斗争(理性反对神话)”,“最后发生了反对诸神不真实形象的伦理的反抗。”[242]而这一精神运动则直接产生了两种结果,一是“宗教伦理化了,神性的威严因此而增强”。二是“神话成为语言的材料,用以表达与愿意极不相同的含义:它转变为寓言。在此转变过程中,神话得到改造,并在新的深度上被理解。”[243]而旧神话则通过芸芸众生的代代相传的信仰,作为背景而被保存下来。
其三,哲学家首次出现了。“中国的隐士和云游哲人,印度的苦行者,希腊的哲学家和以色列的先知,尽管其信仰、思想内容和内在气质迥然不同,但都统统属于哲学家之列。人证明自己有能力,从精神上将自己和整个宇宙进行对比。他在自身内部发现了将他提高到自身和世界之上的本原。”[244]“人在理论思辨中把自己一直提高到上帝本身”,而被束缚与藏匿在人的躯体之内的“特殊的人性”,“渴望解放与拯救,向着理念飞升”,体验着与涅般、与道的一致性,在超越了教义与信念的不同之后,三个地区的人类表现了一个共同的精神特点,“即人能够仅仅独自一人踩出这些途径”而不断地超越自己,“他可能放弃一切尘世财物,避居荒漠、森林或山岭,作为隐士而发现孤寂的创造力,然后也可能作为智者、贤哲和先知而重新入世。在轴心期,首次出现了后来所谓的理智与个性。”[245]
其四,“人们明白自己面临灾难,并感到要以改革、教育和洞察力来进行挽救。他们制定计划,努力控制事件的进程,并第一次要恢复或创建良好的环境。”[246]“人们殚精竭虑地寻求人类能最和睦地共同生活、实行最佳统治管理的方法。改革的观念支配了实践活动。哲学家周游列国,成为智囊和导师。”[247]
就整个“轴心期”来看,这一时期的历史在人类文明史中的地位可以从四个层面来理解。其一,“在所有地方,轴心期结束了几千年古代文明,它融化、吸收或淹没了古代文明,而不论成为新文化形式载体的同是一民族或别的民族。”[248]其二,“直至今日,人类一直靠轴心期所产生、思考和创造的一切而生存。每一次新的飞跃都回顾这一时期,并被它重燃火焰……轴心期潜力的苏醒和对轴心期潜力的回忆,或曰复兴,总是提供了精神动力。对这一开端的复归是中国、印度和西方不断发生的事情。”[249]其三,“任何未同轴心期获得联系的民族仍保持‘原始’,继续过着已达几万甚至几十万年的非历史生活。生活在轴心期三个地区以外的人们,要么和这三个精神辐射中心保持隔绝,要么与其中的一个开始接触;在后一种情况下,他们被拖进历史。”[250]其四,“从三个地区相逢之际起,它们之间就可能存在一种深刻的互相理解。在初次相遇时,他们便认识到,他们关切同样的问题。尽管相隔遥远,但他们立即相互融合在一起。”[251]
“总而言之,轴心期的概念提供了借以探讨其前后全部发展的问题和标准。早先文明的轮廓渐渐消散,承载它们的民族在加入了轴心期运动时从视野中消失了。在并入自轴心期开始的历史运动之前,史前民族一直保持史前状态,要不就是灭亡。轴心期同期同化了存留的一切。从轴心期起,世界历史获得了唯一的结构和至少持续到我们时代的统一。”[252]
作为中国的读者,我们既关注雅氏“轴心轴”这个概念本身的完整意思,也关注他使用这个概念来分析中国“轴心期”文明的特征。雅氏认为,轴心期以后中国有三个特点,其一是不如西方的新开端那样惹人注目,他说:“与中国和印度相比,西方的新开端似乎惹人注目得多……金字塔、巴台农神庙、哥特式教堂——中国和印度展现不出这些在历史连续中出现的形形色色的现象。”[253]
其二是:虽然中国、印度“与欧洲的不一致不是根本性的”,但在“公元1500年,当欧洲迈出其前所未有的步伐时,中国和印度却准确地同时进入了文化衰退。”[254]
其三是:“轴心期的中国古代文明的继承人,在古老的文明中看到了他们自己的往昔。他们代代相传,连续不断;他们没有生活在新时代的感觉(除非那是一个衰微的时代);他们按照具有神话特征的理想化形态,把过去看作是一个在创造性幻想中展开的典范。”[255]
上述雅氏对于中国进入“轴心期”文明之后所表现出的特征认识,有合乎中国文化特征之处,也有一些认识上的偏颇。中国虽然没有金字塔、巴台农神庙、哥特式教堂等文明现象,但中国的古代建筑,还有长城、大运河、四大发明,以及通过科举制度选拔官员等,亦是西方所没有的。至于1500年以后,中国文明是否进入衰退期,亦可以商榷。至于他对春秋末到战国秦汉之际人们内在精神的分析,并不完全符合这一时期文化精英们的思想实际。因为在《庄子·天下》篇里,战国时代的道家感叹“道术将为天下裂”,战国后期的韩非子将他们所处的时代称之为“竞于气力”的时代,从而与“上古竞于道德”,“中古竞于智力”的时代区别开来,并明确反对儒家“师古”的历史观与政治观。但大多数思想家都认为远古的时代曾经有一个理想的“黄金时代”。因此,雅氏对“轴心期”思想家们向往远古黄金时代的说法,在原则上是正确的。
与“轴心期”这一核心概念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是“起源”与“目标”这两个概念,对此两具概念,雅氏有自己独特的规定,他认为:“起源和目标不可能获得任何令人信服的感性的真实形体,我们可用下列符号表明它们:‘人类之诞生’——起源;‘不朽的精神王国’——目标。”[256]因此,在《起源与目标》一书中,雅氏所说的“起源”与“目标”并不是一个可用来实证的概念,为人类提供一个可以通过科学实证方式检验的起源和目标,而只是一种象征,通过这一象征来揭示人类在“起源”与“目标”的两个方向都是开放的,并通过此开放性来思考人类的命运,人性的深奥性与人性的潜在可能性。正因为如此,当他说“上帝是起源与目标,是心灵的宁静。那里有安全”[257]这句话时,他所说的“上帝”不再是基督教传统中的人格神上帝,而是一种超然的存在,一种象征,它在根本上“是历史性的”。
就“起源”问题在人种学上的讨论,人类究竟是“单种起源”还是“多种系起源”,这是一个无法用科学的实证方式加以解决的问题,“因此,人类的统一起源是一个思想而不是由经验拓开的现实。”[258]对于雅氏所要讨论的人类的统一问题而言,“人类起源是单种系还是多种系并不是决定性的论据,我们在此讨论的是对人类统一性的信仰。在历史进程中,人类的统一已发展成为人类构成的组成部份;把人类与动物分隔开的鸿沟成了它的先决条件。”[259]雅氏转换了讨论的视角,将对人类起源的人种学的讨论转向对人类内部精神统一性的新起点的讨论,而他构造的“轴心期”概念就是“一个关于人类内部新起点”的讨论。他认为,“轴心期同时发端的奥秘,比起古代文明诞生的问题来,所处的水平要深刻得多。首先,其同时性更加准确;其次,它与人性的整个有意识的思想方面的精神的历史发展有关。从古代文明产生起,这三个具有独特性的地区就在基督降生前的1000年中,产生了人类精神的全部历史从此所依赖的创造成果。”[260]
就“目标”概念而言,雅氏将人类的“目标”设定为“历史的统一”,而这种历史的“统一不是事实,而是目标。”[261]其具体内涵有如下四点:
其一,目标是人类的文明和博爱。在整体上表现为人类“存在的有序化”,而这种有序化的目标就是“合法的世界秩序”,而人类的“统一通过存在的有序化给人类心灵和精神的潜力以发挥的机会。”[262]其二,目标是自由和自由的意识。“法律秩序的意志没有直接造成其目标的自由,而只是造成了政治自由,它给人类存在以可能能实现所有真正自由的机会。”[263]
其三,“目标是共同环境中的杰出人物、精神创造和文化生产,它是创造能力。”[264]其四,“目标是上帝在人类中的显现。在目标深处感知到的存在就是上帝的表现形式。”[265]
在《起源与目标》一书中,雅氏并不是要探索人类在人种学上的起源问题,而是在普遍历史观的基础上探讨人类历史统一性的起点,摆脱基督教信仰启示的先验历史观,他说:“为了使轴心期的真相真正具体化,为了把它们真正作为我们普遍历史观的基础,就要掌握超过出一切不同信仰的全人类的共有之物……在此意义上,可以说公元前800至200年间的数世纪,就是世界历史的轴心,这在经验上对所有都是很明显的。”[266]而“基督信仰启示的先验历史,则创世、堕落、诸启示阶段、预言、上帝之子的显身、拯救与末日审判所构成。”[267]而“将所有人结合在一起的不可能是启示,而必定是经验。启示是特殊历史信条采取的形式,而经验却是人人都可以理解的。”[268]“虽然轴心期局限于中国、印度、和西方,虽然这三个世界开始并没有联系,然而轴心期奠定了普遍的历史,并从精神上把所有人吸引进来。”[269]
在雅氏看来,“轴心期”文明的意义在于:“我们当今的历史意识,还有我们对自己目前状况的意识,直至我仅能暗示的结果,都是由轴心期概念所决定的,无论这一论点是被接受还是被否定。这是一个方法问题,凭此方法人类的一致性对我们变成一个具体的现实。”[270]
二、“历史的历史性”与“统一”的历史观
(一) 《起源与目标》的构思逻辑与“历史”的两个突出特征
从绝对字数的角度看,《起源与目标》一书并不能算是大部头著作,但其所涉及的思想内容却是极其复杂的。从其构思逻辑来看可以从两个层面来认识其对“历史的历史性”的分析:一是从普通人都采用的历史、现实、未来的时间序列特征来考察历史的历史性;二是从历史与自然的不同角度来规定“历史的历史性”。就第一个层面来看,他虽然采用了普通人都使用的三阶段划分历史的方法,但他对于何谓历史、何谓现实、何谓未来的具体回答,不仅与普通人的看法不同,也他之前的欧洲哲学家的看法也不一样。他所谓的历史是一个动态发展的历史,是一个朝向未来的过程,即“历史在事实上进入未来,在解释中是过去,它是各种内涵互相关联的、开放的无穷世界。总之,各种内涵关系似乎经常汇合到一个发展中的共同内涵中去。”[271]他所谓的“现实”也不只是当前的一种客观性,而一种哲学化的现实,即“现实本身也变成了历史意识的根源和目的。”[272]他所谓的“未来”,并不是某种实体化的东西,而只是“隐藏于过去和现在之中,我们能从其真实的可能性出发去理解和思考”[273]的一种“整体的历史”或曰“历史的统一”。
就第二个层面来说,他严判人类的历史与自然现象之间的不同。在他看来,“自然是纯粹的事件,它不认识自己,却首先被人认识。”因此,“自然是非历史的”。[274]而人类历史则是依赖“传统”、“精神运动”而构成的。“遗传向我们揭示自然,传统向我们揭示历史。”[275]而“使们成为人类的不是遗传,而往往是传统的内容。”[276]“历史中所有的本质,都是人们能够用来记忆,并因此而能保存为未来之因素的东西。对于人类来说,时间获得了唯一的历史性意义,而自然的存在却是同样事物的永久重复。”[277]
在雅氏看来,“历史”的结构似乎可以从两个方面去理解,一是“独一无二和不可替代的个体”构成了历史。他认为:“那种被重复的个别,那种被另一个个体取代的个体,那种相当于普遍原则的一个实例,诸如此类的东西都不是历史。要成为历史,个别必须是独特的,不可替代的,和唯一的。”[278]而这种“个体”不是“因其在时空中的位置而被称之为现实的存在”的个体,“而是被特殊的历史个性渗透、毁灭和改变的、独一无二和不可替代的个体;它不是被当作普遍的容器或普遍原则的代表的个体,而是首次使普遍原则生气勃勃的现实。它是和一切存在之起源有密切关系的自我存在,它在其意识之母体中充满信心。”[279]而这种历史的个体“只是被爱和在爱之中生长的洞察力与直觉力所披露。只有在爱之中才存在的唯一的个体逐渐向被爱所引导的求知欲无限敞开。”[280]
二是变迁。雅氏说:“举世无双的唯一性越明确,同一的重复越少,历史就越可信。一切伟大之物都是变迁中的现象。”[281]而这种变迁“是用其意义和目的记载不朽的永恒的变迁。”[282]“历史的变迁”不同于自然的重复,就在于人类“从史前获得的人性的资本”,这一“人性的资本”在生物学上不能遗传,“然而是历史本质,是可以增长或浪费的资本。它是某种真正早于一切思想的东西,它不可能被伪造成有意识地创造出来的东西。”[283]“经过在历史中发生的精神运动,这个本质首先变得成熟和清晰了。”[284]在此基础上,他又将“历史”看作是“变迁这一事实本身”,变成一个不可以作固化理解的精神对象。他说:“历史的基本特征是:历史是变迁这一事实本身。本质上持久的东西并不代表历史。一切持久的事物是历史的基础、材料和手段……在类历史迟早要终结,因为它曾经有开端。这开端既是开端,也是终结。”[285]
雅氏对人类的历史既表现出一种自豪,但也时时流露出一种忧虑,即对人类历史的不确定性,特别是人类文明随时可能面临毁灭的危险性表现出极大的担忧,进而与中国“易哲学”传统的深沉的忧患意识有着某种思想的同构性,但在具体内容上又表现出极大的差异性。
(二) “统一”的历史观
雅氏认为,人类要追求的“具有不可替代的宝贵价值”,只能属于“统一”的范围。如果“没有统一作为历史的起源、目标和依据,就没有历史。”但对于“统一”本身,我们只能假设,“永远不能真正了解这个统一。”[286]
雅氏认为,“领悟历史的统一,即从整体上思考世界历史,是寻找历史最终意义的历史认识的推动力。”[287]因此,对于历史的哲学思考就要求我们“把人类合成一体的统一”来思考。要避免将历史看作是偶然的分散、漫无目标的来来往往,以及是许多虚假途径的绝路的话,“那么,历史之统一的思想就是必然的。”[288]问题的关键是我们领悟这种“统一”的方式。雅氏从否定与肯定的两个方面对历史的“统一”做出了如下的深刻思考。从否定的角度看,他认为,对“历史统一”的理解不能从如下的思路去理解:
“人类的认识将理解不了历史的统一;我们不可以把历史的统一解释为人类生物学根源的统一;地球表面的统一和现实时间造成的共同封闭仅仅是外在的统一;我们不可能证实包罗万象的统一目标;关于世界法律秩序的思想所引向的是人类生存的基础,而不是历史内涵本身,这一思想仍有疑问;通过与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的一致性相关联并不能理解统一,因为统一只与理解发生联系;统一不是通向目标的进步和不断地走向无限的进程。”[289]
从肯定性的角度看,雅氏认为“历史统一”的观念思考问题是可能的,理由有如下五点:其一,即使在实际上我们对“历史统一的第一种解释都总是在认识上造成极其无知的感觉”,但是,作为一认识方法,“在统一的思想指导下的分类方法是可行的。”[290]其二,统一的历史观可以“得到地球的封闭性支持”,即“地球的土地和空间是一体的能控制的”,而且,“统一还得到人类统一的起源的支持。人类是同一种类,这是一个表明共同起源的生物学事实。”[291]其三,“统一的主要根据是人们在普遍都能理解的同一个精神内彼此相认这一事实。”[292]其四,“统一的思想具体出现在关于普遍可能性的意识中。”[293]其五,对于理想性的“统一”人类能力无法做详细的描述,但在“价值层、历史的起源和历史的关键阶段来理解历史”[294]的统一与整体性,还是可能的。
“从整个人类共同所有的轴心期中推出历史的统一”,[295]是雅氏对“世界历史”进行解释的一种理论尝试,并试图从此整体的角度来揭示“人类本身的历史性”,他说:“我们以整体的概念来领悟历史的统一,整体以根据经验建立的结构来表明人类本身的历史。”[296]
雅氏所讲的“历史的统一”并不以“完成人类的联合而达到顶点”,在他看来,历史始终“位于起源和目标之间,统一的思想在历史中活动着”,“更确切地说,人类的统一是历史的目的地,即获得圆满的统一将是历史的终结。在统一及统一的思想和观念指引下,历史保持运动。”[297]因此,统一的观念只是一象征,是“无比遥远的参考点”,是“融为一体的起源与目标,是超然的上帝。”[298]
如果非要将“历史的统一”作具体的理解,“统一”也只是一种“崇高的人性统一”,而这种“人性的统一”是不存在于任何现成的、僵化的制度之中的。他说:“这个崇高人性的统一不存在于知识和工具的传播中,不存在于帝国权限和征服的范围之中,不存在于那种置人于死地的禁欲主义和对近卫军进行强迫训练的极端产物之中,不存在于制度和决定的稳定与持久之中,而存在于最清晰深刻的意识和显示本质的光彩四射的瞬息时刻之中。”[299]
雅氏还提醒我们,“所有统一的事实都历史内部的简化物”,最重要的事情是领悟历史统一形式与道路的多样性,以及多样的现象在整体中发生的道理,“我们要对超过出多多样性的整体保持开放,对人类和永远是现存的人性整体保持开放。”[300]因为“这个人性包含一切。它在自身中孕育的奇迹不管有多么宏伟壮丽,永远只是其它现象中的一个现象。”[301]因此,雅氏在历史哲学的层面所说的“统一”,并非是经验意义上的人类大一统,而是一种从整体上思考人类问题的哲学方法。
三、“人性”、“自由”与人类的历史
(一) 人性与历史的内在联系
《起源与目标》一书一再给予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人性”,这是很多阅读该著作的人不太注意的一个重要内容。雅氏之所以高度关注“人性”,是因为“人性”中蕴含着我们人类所没有意识到的巨大潜能。雅氏认为,人性有两个基础,一是史前,一是历史。就“史前”而言:“人类在史前的进化,就是构成人性之基本因素的发展。”而且,“在史前逐渐形成的人性,今天仍然是真实的。”就“历史”而言:“人类的历史进化,就是精神性和技能性的遗传内容的展现。”相对于“史前”而言,“历史进化具有某种外貌,它以深刻开阔的人性为基础,采取了著作、观念、思想和精神形态等暂时形式。[302]要而言之,“史前与历史相继创造了我们人性的两个基础。史前的形成过程构成了我们生命的根基,这一形成过程是人之基本结构的成长过程。人的基本结构具有自然的冲动和自然的特性,具有我们人的构造中所有无意识部份。历史进程是人类有意识地接受过去,并在此基础上加以改建扩展的过程。它向我们显示,什么是人所能做到的,什么是我们教育、信仰、知识、能力的根源及其内容——这第二种基础就像是覆盖在火山核心上的一层薄壳,而人就是火山。解脱这层表皮是可能的,但史前时期形成的人之生命的根基却永远不可能抛弃。”[303]
“史前”与“历史”这两个人性的基础,其对于人性的作用是通过不同途径来实现的,“史前过程形成了在生物学可遗传的某种结果,它达到了经过所有历史大变动仍然保证连续的程度。”但是,“历史成果必须在意识上被传递下来,它可能会丢失。一切根植在人性领域中并突然绽开的创造之花,一切在人身上留下烙印、并因成为文化传统而改变了人类外观的东西,都如此密切地与这种传统结合在一起,以至于没有传统,历史就会完全消失,因为传统在生物学上是不能遗传的:我们会带着赤条条的原始躯体而退回去。”[304]
雅氏以一种非常思辨的、形而上学的哲学语言说道:“人完全变成人的时刻是最深奥的谜,它直至今天仍难以探究,无法理解。”[305]他还进一步说道:“什么是人?我们不能圆满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实际上不懂这个问题。这一事实,恰恰是我们人性的一个基本方面。将人如何在史前和历史中形成的问题具体化,同时也就是将人性的基本问题具体化。”[306]
雅氏认为,“人性的先决条件之一是人类的一致性,它在自然法则和人类法则的照耀下,不断被背弃,又永远重新提出它的要求。”[307]这一关于人类历史的观点,多少带有思辨哲学的循环论的色彩,而与马克思的历史唯物论与辩证法的思想是相背离的。不过,在有关人性的两个基础的问题上,雅氏高度肯定了“历史”基础之于“人之为人”的绝对重要性,表明他是一个尊重人类文明传统的哲学家,而不是一个历史虚无主义者。他说:“通过历史,人类变成了努力超越自身的存在。直到历史开始时,人类才着手完成这项高级任务。无人知道它将把人类引向何处,甚至灾难苦痛都能赋予它以猛烈之势,只是随着历史的开始,人才真正成为人。”[308]至于“历史”何以使“人真正成为人”,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1)在历史运动中,人们得到了启发、检验和提高,而且也被失落、铭记和重新浮现。但“合理化”被当作历史的起源与目标的媒介在起作用。(2)时间的短暂被意识到。在万物之中,“只有懂得自己的死亡。在对这临终情景的畏惧退缩中,人感受到时间的永恒,感受到作为一种生命现象的历史性,以及时间的流逝。人的历史意识逐渐同他对永恒的认识一致起来。”[309](3)“历史是代表杰出的个人的不断推进,各个杰出的个人号召其余的人追随他们。”但是,“历史同时依然只是事件,不断地随大流而行”,“广大民众的惊人力量及其平庸的品质,窒息了一切与他们不一致的东西。民众当中的任何东西,若未能成为他们自己的天性,未能通过这一重要意义而赢得生存的权利,未能唤取民众的信仰,那就必定灭亡。”[310]
(二)哲学意义上的“自由”与人性
雅氏认为,人类的“自我意识”在经验上必然发生的东西,“不可分解地与自由联系在一起,自由使我们所见到的图像获得了吸引力或排斥力。”[311]可见,雅氏将人的自由意志与人类在经验上的自我意识紧密地联系一起,表明他将人的“自由意志”看作是人的自我意识的一部分,是有深刻的人性基础的。换句话说,他是在深刻的人性基础上讨论人的自由意志问题的。在《起源与目标》一书中,雅氏从两个层面讨论了自由问题,一是从哲学层面,一是从政治学层面。我们在此文中仅介绍他在哲学层面对“自由”所作的阐述。
他主要从四个层面对哲学意义上的“自由”作了如下的阐述:其一,“自由是对世界的征服,并是对自我的强制。当别人对我不再是异己的,在我宁可承认自己在其余人之中,或者当外部必然性成为我自己存在的一个因素,并能这样去了解和适应它时,自由就会产生。”[312]
其二,“自由要求什么都不遗漏。一切存在之物和有意义之物都必须获得应得的利益。”[313]雅氏认为,“极端自由是自由的条件。因此自由的要旨通过两极分化和对立面的生活表现出来。”[314]“自由潜在地就是一切。它不仅准备把外部产生之物都作对立面,而且要把它合并到自己中来。”[315]
其三,自由是脆弱的。“真正的自由在于意识到自身的局限性。”[316]从主观性方面说,“哪里存在可以肯定自身,使自由变得明晰,与此同时它们也会变成明确的超然存在。”[317]从人类共体的客观性方面说,“事实是自由依赖于每个他人的自由。因此政治自由从来不可能存在于最终的和安全的永久条件中。这里自由也是在发展之中。”[318]
其四,“自由是人类的时间之路。”“人类从对自由的要求中朝创造自由而迈进。因此自由是在运动之中和辩证法之中的。”[319]
要而言之,哲学意义上的自由“不是一个物体”,因此“不能具体化为一个明确的概念”,[320]“但可以通过思考来熟悉它,可以在思想运动中达到理性的现实性”。[321]“把人们引向自由意味着引导他们互相对话”,因此“没有孤立的自由”,个人需要“牺牲其空洞的严密的自由,以利用那只与存在在一起才能赢得的自由。”实际上,“与真理对抗的因而也是与自由对抗的”,[322]因此,为自由而斗争也就是为真理而斗争,而“自由地为真理而斗争是一场爱的斗争”。[323]
四、“世界历史”观念与非欧洲中心主义的思想
雅氏对欧洲中心主义的观点有一个反省,他说:“直到19世纪末,对我们来说历史基本上是仍是欧洲史。对于那时的欧洲意识来说,世界其余地方都是殖民领土,只具有次要意义,注定是欧洲掳掠的来源。列强一直在寻求为自己赢得广大的领土,现在展开的世界历史的基础,是那时列强无意奠定的。”[324]他又说:“人类整体和一切旧文化已被拖进共同的破坏或复兴之川,这一事实的重要性只是近10年来才被意识到。我们中的长者与儿童一样,仍完全生活在欧洲意识中。”[325]因此,他要超越西方学者自18世纪末以降形成的欧洲中心主义思想框架,努力从人类的整体性与未来世界的一体化的新角度,来思考整个人类的历史命运问题。
当然,雅氏所处的时代与其前贤也不一样,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人类的整体性已经在各方面都展现出了一些端倪,正如雅氏自己的断言:“整个世界已成为问题和任务”,“历史已发生了总体的质变”,“基本的事实是,再也没有任何东西可置身事外。世界是封闭的。地球的统一性已经达到。新的危险和新的机会暴露了。一切重大问题都成为世界的问题,目前状况已成为人类的状况。”[326]因此,作为时代的精神先驱,雅氏已经真切地看到了“人类的真实统一”的征兆,他说:“今天,第一次有了人类的真实统一,它表现于这一事实,没有一处发生的大事不会引起全体的关切。在此情况下,欧洲人通过科学和发现造成的技术革命,仅仅是精神灾难的物质基础和加速原因。”[327]雅氏的这一说法,在我们今天的世界显得格外亲切、真实。
对于“人类真实统一”之后的结局,也即是“世界历史”的真实达成后的人类面貌,雅氏有这样的一种预言:“一旦这一过程完成,中国将不再是中国,中国人将不再是中国人,可能也适用于全人类。在这意义上,欧洲人感到他们处于德·格鲁的时代,欧洲也将不再是欧洲,欧洲人不再是欧洲人。然而,那将是我们无法预见其形象的新中国人和新欧洲人。”[328]这即是说,在真实的“世界历史”之中,人的形象将超越以往在国别史时代深深打上地域与民族文化烙印的形象,而以一种融合后的新面貌出现。这一说法与康德所设想的“世界公民”概念有某种相似之处。
结语
以上四点,是我对《起源与目标》一书的基本内容及其核心思想的个人化的解读。说实在的,该书在很多方面都是很难理解的,并且有很多抽象的玄思,也不乏晦涩之处。有些地方的叙述与思考还带有文学的浪漫,如他对人性的飞跃与人类的结局的思考与描写,就体现了哲学的玄思与文学的浪漫:“我们可以把导致历史的人性所造成的飞跃,想象成人类遭遇的灾难。人的堕落和外来力量的入侵那种不可理解的事情发生了。历史可以是一场壮观而短暂的烟火轮的熄灭过程。在初始发生的,还会颠倒过来再发生。人类最终回复其史前存在的极乐状态。”[329]类似的这样表述,在全书中还有很多处,无需更多的引证。
《起源与目标》一书表面上是以“历史哲学”的面貌出现的,但在其中讨论的许多问题远非狭义历史哲学所能涵盖,其中对“技术”的哲学思考,对信仰的哲学阐述,对自由的真正意蕴与自由在经验生活的多重表现的思考,都让该书超越了一般的历史哲学的内容。我们不妨说,雅氏是在极其宏阔、开放的人类历史视野里,以哲学的“起源”与“目标”的观念来思考人类的命运问题。他紧紧抓住现代文明所发展的“自由”精神与现代科学文明发展出的“技术文明”两个最为重要的现象,要求人类在面对未来的危险与不确定性的难题的时候,通过回顾“轴心期”文明的精神遗产,为未来提供某种方向性的指引;而对从人类文明基础之上发育出来的“技术”现象,强调要用思想或精神的指导,以使它造福于人类而不把人类引向万劫不复的深渊。
最后,我希望有人能直接从德文重新译出《起源与目标》一书,以便广大的中国读者能更为准确的理解该书的思想。在世界历史的新阶段,中国的学人与政治家要有深广的世界眼光与人类眼光,建议认真研读雅氏的这本著作,并通过此本著作回溯西方学术界如何从“欧洲中心论”跳出来的思想历程。而“比较哲学”的思想起点亦当从雅斯贝尔提出的“世界历史”开始。
佛耶比较与对话:个案研究
晚明天(主教)佛对话文存——《辨学遗牍》
麻天祥 李彤 韩燕丽[330]
内容提要:本文对《辨学遗牍》一书的成书过程、版本及思想背景进行了全面、详尽的考证总结。在此基础上,着重以这一文献为中心和样本,揭示出晚明时期天主教与佛教碰撞、对话和融通的轨迹与特征,对其中所蕴涵的理论教训和启示进行了总结评析。
关键词:《辨学遗牍》利玛窦 天主教 佛教
一、题解
四库总目提要(子部杂家类存目)载:
《辩学遗牍》一卷,明利玛窦撰。利玛窦有《乾坤体义》已著录是编,乃其与虞淳熙论释氏书,及辩莲池和尚《竹窗三笔》,攻击天主之说也。利玛窦力排释氏,故学佛者起而相争,利玛窦又反唇相诘,各持一悠谬荒唐之说,以较胜负于不可究诘之地。不知佛教可辟,非天主教所可辟;天主教可辟,又非佛教所可辟,均所谓同浴而讥裸裎耳。
应当说,这是天主教传入中国后,天主教与佛教对话的最早的原始资料。署名利玛窦撰,实为利玛窦与虞淳熙居士和莲池袾宏辩驳天佛观念的往来书信,及其后托名之作。纪晓岚在四库总目提要中以“同浴而讥裸裎”批评二者各执偏见,“以较胜负于不可究诘之地”,认为佛教可辟,但非天主教所可辟;天主教可辟,亦非佛教所可辟,显然站在第三者,或许是严守儒家的立场而作壁上观的。
《辩学遗牍》明天学初函本,国家图书馆善本部藏。《辩学遗牍》(以下称《遗牍》)由两部分组成,包括四篇文章。前编是利玛窦与虞淳熙往还书信,即《虞德园铨部与利西泰先生书》(以下称《虞书》)及《利先生复虞铨部书》(以下称《利书》),二氏辩论天佛二教事;后编旧题《利先生复莲池大和尚竹窗天说四端》(以下称《复》)。此《复》录一端《天说》,并有辩驳,凡四节。文末附凉庵居士李之藻和弥格子杨廷筠所撰跋二则。
现存《辨学遗牍》主要有三种:一是由北京大学宗教研究所主编,2003年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郑安德等标点的《明末清初耶稣会思想文献汇编》(五卷本)(以下简称《汇编》),《辨学遗牍》收录在第一卷第四册,依据1919年《重刻本辨学遗牍》编辑整理而来;二是由台湾学生书局在1965年影印金陵大学藏万历天启闲刊本出版的六册本《天学初函》,其中《辨学遗牍》收录在第二册(以下简称六册本);三是由明李之藻编,黄曙辉点校,由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出版,2013年的《天学初函》四册本(以下简称四册本),其中《辨学遗牍》收录在第一册,这也是目前最新版本。《天学初函》,明李之藻主编,分理、器二编,书十九种,保存了明清以降中西文化交流过程最初的一批文献。初刻于1628年,被称为“中国天主教第一部丛书”。据《天学初函》记载,《辨学遗牍》1609年首刻于北京,燕贻堂续梓版。
上述书信作者简介如下:
利先生,即明末来华的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字西泰,原名Matteo Ricci,生于1552年,1582年抵澳门。初在广东肇庆,随后北上韶州、南京、南昌、北京等地传教,1610年卒于北京,终年五十九岁。
虞淳熙,字长孺,号德园居士,钱塘人。1583年中进士,官吏部稽勋司郎中,故人称虞铨部。晚年归隐,1621年卒。有《德园集》六十卷。
莲池,字佛慧,俗姓沈,浙江仁和人,1535年生,1615年卒。四十余岁出家,入古杭云栖寺后,亦称云栖大师,勤于念佛三昧,倡禅教净合一,诸宗融合的新佛教,被誉为“法门之周孔”。与憨山、紫柏、藕益齐名,并称为明末佛教四大师。
据陈垣先生考证,第四篇《复》书显然系托名之作。其重刊序曰:
一、 《辩学遗牍》考证1、《利复虞淳熙书》为利氏所作《辩学遗牍》一卷,旧本题利玛窦撰。前编为《利复虞淳熙书》,此书为祩宏和尚所已见,云栖遗稿《答虞淳熙书》曾提及之。2、《辩竹窗三笔天说》非利氏所作,后编为《辩竹窗三笔天说》,殆非利撰。据祩宏自叙,《竹窗三笔》刊于万历四十三年乙卯,而利己于三十八年庚戌物故,岂其书未刻,其说先出,故利 得而辩之然?《天说四篇》皆《三笔》编末之文,庚戌与乙卯相距五年,利未必得见。且细考原辩语意,明在《三笔》刊行以后,而其中并无一语可确指为利作之据。如《复淳熙书》之屡自称窦云云者,则又显非志在托名利作,以动人观听者也。当时天教人材辈出,西士、中士中能为此等文者不少。此必教中一名士所作,而逸其名。时人辗转传钞,因首篇系利复虞书,遂并此篇亦题为利著。李之藻付梓时,偶未及考,故未订正耳。之藻跋谓,此系得自友人一钞本,则其文为之藻本来所未见可知也。
二、本书的由来说明1、再版订正万松野人主天津《大公报》时,曾以此卷刊入报中,今欲再版,属余订正。2、补刊杨序,余以旧题由来已久,姑仍其旧而揭之如此,并补刊弥格子跋一篇。弥格子者,杨廷筠也。此跋崇祯间闽刻本有之,《天学初函》本无有。3、祩宏的写作动机,又《袾宏和尚答虞淳熙》一书亦附录之,足见袾宏始轻慢而后戒严,实因利说日炽以至所谓名公皆为所惑,乃有四《天说》之作也。不然既以利说为渔牧蚊蛙不足辩矣,又胡为至再至三而辩之?然自吾人观之,辩学固美事也。
为了证实《辨学遗牍》后编是托名利玛窦之伪作,云栖株宏的弟子张广湉尝从三方面予以辩驳:一、《辨学遗牍》乃辩云栖《天说》四则而作,然《竹窗三笔》出时,利玛窦已亡故,此其脱空之谎一也。二、闽中所刻《遗牍》附有弥格子跋,谓云栖临终自悔错路误人,此又一谎言也。三、傅泛际自许立论相答,后又称不欲笔战,自语相违,此又脱空之谎也。而且,《利复莲池和尚书》的论证也是针锋相对、逐条批驳、胜气相加,与利氏在《利复虞书》中提倡的“和言增辩力”和“若得抠趋函又,各挈纲领,质疑送难,假之岁月,以求统一,则事逸功倍,更惬鄙心矣”的精神相左。至于《辩学遗牍》中《利书》更强调,辩论当以理为主,不当以信徒为据,也不当以势力人情为虑,“其辩之明,亦惟恐众生堕此危池耳。”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
一、《辨学遗牍》是晚明天佛对话的原始资料,涉事人有利玛窦、虞淳熙和云栖祩宏,以及其后托名利玛窦的天主教传教士,还有纪晓岚诸名士。尝收入《四库全书》、《天学初函》等。
二、复莲池书系利玛窦以后的传教士托名之作,言语之间,“胜气相加”,与利氏“以求统一”的宗旨相左。
三、利玛窦虽然以合儒辟佛为策略,对佛教多加指责,但强调以理为主,不以信徒为据,不以势力人情为虑,以求统一,可以说是宗教对话的基础,也是明末天主教在中国传播的敲门砖。
四、儒家虽作壁上观,但其言佛教可辟,非天主教所可辟;天主教可辟,非佛教所可辟,提示宗教对话确实需要有知己知彼的深层次的理解,即同情的理解。
五、对话虽强调以理为主,但对义理深入不足,大多徜徉在信仰层面。这也是早期文化接触的特征。尽管如此,对话仍然是必要的,所谓“辩学固美事也”。
二、背景
基督教在中国传播有四个阶段:唐朝的景教、元朝的也里可温教、明末清初的天主教、清末的天主教和东正教。在前两次传播中,基督教对中国社会影响甚微,第三次传播,在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的努力下,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
1579年,传教士罗明坚从印度来到澳门,1583年,至两广总督驻地,并获得两广总督陈文峰好感。但是,与官府的态度截然相反,当地百姓对罗氏及其传教士极为反感。为了避免与当地民众冲突,罗明坚贯彻了范礼安的指示[331],入乡随俗,改穿僧服,“同化为中国僧侣(或称和尚)”[332],从而启动了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播。
之后,应罗明坚要求,耶稣会派遣利玛窦为其助手。“利玛窦初至广,下舶,髡首袒肩,人以为西僧,引至佛寺。”[333]利玛窦到达肇庆,易服之外,并学习汉语,了解中国风俗文化,以与民众和士大夫交好。于其时,利玛窦闭口不谈传教事务,在翻译天主教有关典籍时,更是汲取佛教教义,融会贯通,因而取得了一定的成效——“读书之人接到《祖传天主十戒》,大致一目了然,知与佛教的五戒八戒相仿……”[334]为天主教在内地的传播开启筦钥。
1589年,利玛窦和传教士麦安东离开肇庆到达韶州,继续着僧袍,广交游,藉此推动天主教的本土化。但是,令利玛窦始料不及的是,当地僧人在中国社会的地位不高,民众多视之为另类;利玛窦以“寺”命名的教堂也成了民众轻薄侮谩之所。经观察,利玛窦发现,僧团内部鱼龙混杂,僧人行为放荡不捡,“或为打劫事露而为僧者;或为牢狱逃脱而为僧者;或悖逆父母而为僧者;或妻子斗气而为僧者……以至奸盗诈伪,技艺百工,皆有僧在焉。”[335]“和尚们都是,或大家认为的是全中国最低级和最没有教养的人。一是由于他们的家世;一是由于他们无知和缺乏教育……他们虽然没有妻室,但并不谨守清规。不过他们与女人有染时,尽量在暗中进行,以免受到官方的制裁。他们犯了罪,若有真凭实据,官方会罚他们坐监,加以殴打,甚至杀死,对他们没有一点敬意……在这个时代,佛教又相当兴盛,建了许多新庙,旧庙重加整修。但是信佛的大部分是妇女、太监,无知的老百姓。”[336]于是,利玛窦对身着僧服以利传教的思想有所的怀疑。同时,在利玛窦看来,佛教与中国的权利阶层相分离,中国的文人学士大多恪守儒家原则,真正位于统治地位的是儒家思想和恪守儒家思想的儒士而非佛教;充分认识到,要使得天主教在中国迅速传播,首先要跻身儒林,进入中国上层社会。1594年,利玛窦接受瞿太素等人的建议,决定易僧服为儒袍,取消传教士的僧名和以“寺”命名的教堂,改称“西儒”。
利玛窦的易服行为不仅表现出向儒家的靠拢,而且标志着和佛教的公开决裂。应当说明,利玛窦对佛教的看法不尽全面,明代佛教在中国社会还是有其深刻和广泛影响的。但是利玛窦执着于对佛教的偏见,转而将佛教视为天主教东传的一大障碍,由是高扬“合儒辟佛”的策略。但是利玛窦在批判佛教的同时,还是希望在教理上与佛教“以求统一”,目的虽然是为了推动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播,主观上同样表现了文化融合的责任,客观上也起到了文化会通的效果。然而,继其后来华的传教士违背了利玛窦“以求统一”的原则,托名利玛窦,不仅给予佛教激烈的评判,而且对儒家礼仪也排斥一切妥协[337]。佛教徒因此据理力争,从最初的轻慢、调和,终至“辩至再三”。
三、辩学
1607年底,虞淳熙应杭州知府周野之请,为利玛窦新作《畸人十篇》撰写序文。阅其书,书中间有不尽如虞氏意者,于是致书利玛窦,以与之辩析学问,此信题为《虞德园铨部与利西泰先生书》。书信开篇,虞淳熙友好地表达了对利玛窦带来的算数天文等知识和技术的肯定与向往,毫不吝啬地赞誉了利玛窦贡献,称其为“贤者”。接着,虞淳熙说明明末儒释道三教合一的文化格局。他说:“不佞生三岁许时,便知有三圣人之教,声和影随,至今坐鼎足上不得下。”[338]至于佛教,经印度传至中国,历经千余年,适时地汲取、借鉴了儒道思想,并在中国这片土地上植根生长,三圣之教,“声合影随”。在此,虞淳熙委婉表示,既然佛教同样作为外来宗教可以在中国长足发展,那么基督教也可效仿佛教,在中国落地生根。然而,虞淳熙又指出:“侧闻先生降神西域,渺小释迦,将无类我鲁人诋仲尼东家丘,忽于近耶?”借孔子西邻不识孔丘学问的典故,批评利玛窦“渺小释迦”,漠视西来佛教是“相近相轻”,说明文化隔膜的地缘因素[339]。从根本上看,虞氏认为,利氏“渺小释迦”的真正原因显然是未能遍阅佛教经典,对佛教精神和价值取向缺乏了解。以此一知半解的知识对佛教妄施批评,也就难免言不及“义”,而失之千里,即所谓“不全窥其秘,而辄施攻具,舍卫之坚,宁遽能破?”自然也就是言者谆谆,听者藐藐了。基于此,虞淳熙对症下药,为利玛窦推荐《宗镜录》、《戒发隐》、《西域记》、《高僧传》等一系列佛教文献,希望利玛窦认识佛教,理解佛教,在文化接触的过程中,促进与天主教的相互资益,共同发展。同时,虞淳熙还列举陆象山、王阳明等人对佛教的认识、汲纳,说明佛教与儒家思想的融会贯通,指出天主教在中国本土化发展的必由之路,也就是文化趋同之路,与利玛窦“以求统一”的思想不谋而合。
可以看出,虞淳熙并没有将天主教放在佛教的对立面,而是引导利玛窦对佛教深入了解,使其认识到攻讦佛教之难,倡导天佛相容,明显地表现出调和天佛、文化趋同的理念。
利玛窦积极回应了虞淳熙的来信。《利书》曰:
其以技巧见奖借者,果非知窦之深者也。若止尔尔,则此等事,于敝国庠序中,见为微末。器物复是诸工人所造,八万里外,安知上国之无此?何用泛海三年,出万死而致之阙下哉?所以然者,为奉天主至道,欲相阐明,使人人为肖子,即于大父母得効涓埃之报,故弃家忘身不惜也。
显而易见,利玛窦并不在意虞淳熙对其“精天文方技、握算之术”的赞誉。他强调,以“微末”之“技巧”见奖者,实在是对自己的误解。他说:我之所以“弃家忘身”,“泛海三年,出万死而致之阙下”,就是要阐明“奉天主至道”,而“使人人为肖子”,即天主的忠实信徒,和盘托出其来华传教的使命。
既然奉天主教为至道,其他思想学说自然也就是旁道、外道,或者小道。所以利玛窦特别强调:“独以大道商榷”,表现了他的卫道精神。
利氏首先肯定虞氏“亹亹[340]千言,诲督甚勤,而无胜气。欲窦据理立论,以阐至道。敝乡谚云:和言增辩力。”短短数语,足见利氏文化对话的诚挚态度。利氏还表明,平生奉戒,坚于金石,决不敢犯诽谤之戒,对佛教的非议只不过是就事论事,据理立论。诚所谓,“佛教果是,果未尝实见其非,辄遂非之,不诽谤耶?”至于非佛是儒,更非佞谄儒学和士大夫,实在是“直心一意,所是所非,皆取凭于离合。”利氏进一步解释说:“窦自入中国以来,略识文字,则是尧舜周孔而非佛,执心不易,以至于今。区区远人,何德于孔,何仇于佛哉?”,甚至强调,“中夏人士,信佛过于信孔者甚多,何不并佞佛,以尽谄士大夫,而徐伸其说也。”以此表明其是儒非佛的价值取向,只是遵循义理的离合,是自己一心侍奉上帝的选择。他说:“尧舜周孔,皆以修身事上帝为教,则是之。佛氏抗诬上帝,而欲加诸其上,则非之。”如是而已。至于虞淳熙建议利玛窦遍阅佛教经典再行辩论,利玛窦毫直截了当地说:“夫上帝一而已,谓有诸天主不诬乎?渺小人群,欲加天主之上,不抗乎?其为瑕衅,孰大于是?亦何必遍翻五千余卷而后知也?”上帝是唯一的,至高无上的,是生成一切而不被生成的绝对,如此简单的道理,又何必遍读佛经而后知。在这里,利氏不仅坚持了卫道上帝的信仰,也表现出在辩论过程中,徐伸其说,据事言理,据理立论,而无胜气的文化对话的立场。
《利书》同样表示,愿意接受虞氏的建议,阅读佛教经典。但是,他还是指出:佛经中“捕风捉月者实多”,“窦辈所与佛异者,彼以虚,我以实;彼以私,我以公;彼以多歧,我以一本;此其小者。彼以抗诬,我以奉事,乃其大者。”不仅以虚实、私公、多一区别佛教与天主教,凸显天主教之优胜,而且在最后,尤以“抗诬”或“奉事”上帝为准绳,比较二者优劣,显然是从信仰上立论的。但是,利玛窦毕竟还是希望以理服人,希望“质疑送难”,在“以理为主,不以信徒为据,不以势力人情为虑”的基础上平等对话,“以求统一”。
收到利玛窦的回信后,虞淳熙转呈云栖大师。云栖大师回复见《云栖遗稿答虞德园铨部》,内容简明扼要,文曰:
利玛窦回柬,灼然是京城一士夫代作。向《实义》《畸人》二书,其语雷堆艰涩,今柬条达明利,推敲藻绘,与前不类。知邪说入人,有深信而力为之羽翼者。然格之以理,实浅陋可笑,而文亦太长可厌。盖信从此魔者,必非智人也。且韩欧之辩才,程朱之道学,无能摧佛,而况蠢尔么魔乎。此么魔不足辩,独甘心羽翼之者可叹也。倘其说日炽,以至名公皆为所惑,废朽当不惜病躯,不避口业,起而救之。今姑等之渔歌牧唱、蚊喧蛙叫而已。
遗稿指出,但从文字上看,《利书》非利氏口吻,实为其羽翼者捉笔,既谓之“邪说”,亦有为之开脱之意。不过还是指出,其内容“格之以理,实浅陋可笑。”况且中国佛教历经千年,以韩愈、欧阳修之辨材,程氏、朱熹之道学,皆无能损毁佛教,区区“蚊喧蛙叫”,更不值一论。不过,“倘其说日炽,以至名公皆为所惑”,自然义不容辞,将“不惜病躯,不避口业,起而救之。”至1516年,莲池大师面对天主教“欲以此移风易俗,而兼之毁佛谤法,贤士良友多信奉者”的状况,决定“略辩其一二”,遂作《天说》四端,即《天说》三篇,及《天说余》一则。《复》书是后世托利玛窦之名对莲池大师所作《天说》四端的辩驳。
莲池株宏在《天说一》中指出:
彼虽崇事天主,而天之说实所未谙。按经以证,彼所称天主者,忉利天王也。一四天下,三十三天之主也。此一四天下,从一数之,而至于千,名小千世界,则有千天主矣。又从一小千数之,而复至于千,名中千世界,则有百万天主矣。又从一中千数之,而复至于千,名大千世界,则有万亿天主矣。统此三千大千世界者,大梵天王是也。彼所称最尊无上之天主,梵天视之,略似周天子视千八百诸侯也。彼所知者,万亿天主中之一耳,余欲界诸天,皆所未知也。又上而色界诸天,又上而无色界诸天,皆所未知也。
株宏此说,完全以佛教的信仰,诠释天主。以此而论,在三千大千世界中,实有万亿天主。天主教的天主,仅仅是佛教中的忉利天王,是诸天王中之一,更毋庸说欲界诸天、色界诸天和无色界诸天了。可以看出,株宏试图将天主教纳入佛教的宇宙框架之中,用佛法诠释天主。另一方面,株宏又以“理”解读天主,明确指出:“天主者,无形无色无声。则所谓天主者,理而已矣。”如此,以诸多否定唯一,以普遍涵盖独特,天主的创生一切而不被创生的地位也就荡然无存了。
三千大千世界,万亿天主之说,是佛教构建的宇宙框架,同天主教上帝创世的万物生成论,显然是分河饮水,各持一说。《复》书强调:天主是独一无二的至上存在,故只可侍奉一主,“二之,是悖主也,安得云敬天善事耶?”株宏视天主为忉利天王,自然也就不是唯一和至上,信仰上的冲突也就在所难免了。所以,《复》书以救世的口吻说:“以佛为主┄┄必受甚深地狱之苦”,“西士数万里东来,正为大邦人士认佛为主,足可叹悯故也。”同时,又以现代地理、天文学知识,批评佛教的时空观念。
《复》曰:《天说》中,三十三天、四天下之说,实为“讹传谬说者”。首先,“西国地理家,分大地为五大洲。其一洲,近弘治年间始得之,以前不识,止于四洲。”“此四天下之说所自来也。”其次,“西国历法家,量度天行度数,分七政为七重”,“七政之中……少者三重,多者五重,总而计之,约三十余重。此皆以玑衡推念得之,非望空白撰之说也。此三十三天之所自始也。此二端者,自有本末。”也就是说,无论四天下,还是三十三天,都是佛教袭取西方地理、历法家的成果,而又有所改窜,“窜入谬悠无当之语耳。”而且,“印度佛经中无有”,“独中国佛藏中有之,不知所本。”并推测,此皆“祖邹衍之说”。“不然,何彼湮灭之尽,此相肖之甚也。”
平实而论,上述批评言之有据,而且对中国文化有相当深入地了解。只不过分歧不在知识,而在信仰。
就株宏天主即“理”之说,《复》驳之曰:“天主是神”,“谓天主无形无色无声者,神也。神无所待而有,而万物皆待之而有,故虽无形色声,能为形色声,又能为万形、万色、万声之主。”故“天主非理”。并以佛、菩萨“多有神通灵应”为例,说明佛教也是有形有色的,以此指责株宏自相矛盾之处。事实上,《圣经》中也说:I am truth, I am life, I am way。应当说,“理”,恰恰是天主教同佛教,以及其他中国宗教对话的基础,《复》书以“天主非理”,批驳株宏之说,未免有点胶柱鼓瑟了。
《复》书继以“佛经[341]系会合之作”,是“杂取所闻于他教者”,以此从根本上否定佛教。《复》指出:佛教天堂地狱之说,取诸天主教;“轮回转生,则闭他卧刺白[342]撰之论”;“迨后流入中华,一时士大夫,醉心其说。翻译僧儒,又共取中国之议论文字”,“若其间钩深索隐”,“最上一乘者,综其微旨,不出于中国之老易。”如此回应佛教的批评,显然多了一些“胜气”,缺少了些商榷的态度,而且也不尽正确,但是也不无道理;特别是“杂取中国的议论文字”、“尽取老易玄言”,既符合中国佛教之特色,事实上也揭示了文化融合,或者说文化趋同(Cultural convergence)的历史真实。
其余,《复》书还在轮回、事天、戒杀三个方面驳斥《天说》,内容多涉及信仰层面:佛家认为轮回必有,“一切有生,皆宿生父母”,杀生即杀父母,婚娶即妻妾父母,故戒杀生、戒婚娶;天主教说明,轮回必无,“故禽兽可得而杀与用,人可得而嫁娶”,无非是各执一词,莫衷一是,逻辑上也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比如,既讲灵魂不灭,又说轮回不可证实;既说佛教主张灵魂常在,又批评六道轮回“自背其说”。所有这些,皆不可说之说。二者无所谓优劣,诚所谓“同浴而讥裸裎耳”。
四、启示
上个世纪末,美国著名学者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提出了他的“文明冲突论”,认为冷战后的世界格局,取决于七大或八大文明[343],文明的冲突,不再是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而是文化的差异,主宰世界潮流的将是文化的冲突。这一文化冲突论在思想学术界影响甚广。事实上,不同文化由于封闭的地理格局不断地开放,相互接触的同时,既有冲突,也有互相吸收与融合,呈现了趋同的态势[344]。《辨学遗牍》反映的正是晚明时期天主教东传华夏,与佛教发生的冲突,以及在冲突中的对话。
应当承认,在这场辩论中,虽然各持己见,坚守各自的信仰,但始终保持平等对话的态度,无胜气而求统一,“往复不置又似极相爱慕,不靳以其所学深相订正者”。虽然,“终于未能归一”[345],但还是可以看出,佛教与天主教并非形同水火,势不两立。遗憾的是,《复》书易人,托名利玛窦,胜气相加,与佛教针锋相对,偏离了“和言增辩力”,不当以信徒为据,也不当以势力人情为虑,“假之岁月,以求统一”的思想轨迹,乃至以后,继利玛窦来华传教者,全面否定主张与中国传统文化积极对话的“利玛窦规矩”,排斥一切妥协,尤其是“敬孔祭祖”,挑起了“礼仪之争”,最终导致雍正即位后,长达百年的教禁,从反面印证了文化对话的必要性。
另外,依现在的学术水平,《辨学遗牍》讨论的问题既有普遍性,如天主的性质;更多的则是粗浅而不足论者。其言虽简而意不赅,说理不详,缺乏系统的逻辑性。现在,我们对这一文献的重新审视,关注的不是他们说了些什么,而是他们“往复不置又似极相爱慕”,并以“其所学深相订正者”,也就是对话的本身——不仅再现了文化接触中平等对话的历史,也昭示着文化融合与趋同的现在与将来。
鸠摩罗什与利玛窦的本土化传教策略比较
黄超[346]
内容提要:在比较鸠摩罗什与利玛窦的传教策略时,中国学者倾向于认为,鸠摩罗什的“改梵为秦”为一种重在思想交融的“内在本土化”策略,而利玛窦的“易佛补儒”是一种重在宗教传播的“外在本土化”策略。本文将依据宗教信仰的层次性理论,联系具体的历史背景,尝试说明,鸠摩罗什的本土化策略是一种“非主体性”的宗教“融入模式”,具有古代东方宗教传播的“弥散性”特征;利玛窦的本土化策略则是一种“主体性”的 “嵌入模式”,具有现代社会学意义上的“主体间性”特征。
关键词:融入 嵌入 鸠摩罗什 利玛窦 本土化
人类社会进入二十一世纪,宗教对话与文化交融的迫切性日益凸显,鸠摩罗什与利玛窦的本土化传教策略不约而同地受到东西方学术界、宗教界的广泛关注和讨论,此一现象的出现绝非偶然。在比较二者传教策略时,中国学者倾向于认为,鸠摩罗什的“改梵为秦”为一种重在思想交融的“内在本土化”策略,而利玛窦的“易佛补儒”是一种重在宗教传播的“外在本土化”策略。本文将依据宗教信仰的层次性理论,联系具体的历史背景,尝试说明,鸠摩罗什的本土化策略是一种“非主体性”的宗教“融入模式”,具有古代东方宗教传播的“弥散性”特征;利玛窦的本土化策略则是一种“主体性”的 “嵌入模式”,具有现代社会学意义上的“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ity)特征。我们不必将“融入模式”和“嵌入模式”平面化地理解为一种排斥性的非此即彼的关系,相反,本文认为,宗教信仰的层次性[347]决定了信仰层面的“嵌入”和文化层面的“融入”是宗教本土化过程中内在具有的张力,直面这一张力也是诸宗教之间展开“主体间性”对话的基本前提。
一、“佛是戎神”与“磐石开裂”
无论是两汉之际的佛教传入中国,还是晚明时期的基督宗教再次入华,其本土化的传教策略都是围绕儒家这一中轴展开。儒家的文化性和“宗教性”[348]构成了佛教和基督宗教在中国本土化的现实处境。
佛教于两汉之际(或东汉初年)传入中国,经东汉两百余年的发展,至东汉末年已初具规模,当时的佛经翻译以西域僧人为主,翻译内容具有随意性,僧人带来什么就翻译什么,大、小乘经典混杂,形成南北佛教差异,与此同时,早期佛经翻译在语言上依赖黄老之学,不仅导致两晋“六家七宗”的歧义,而且使儒家士人往往把佛陀信仰看作道教的神仙方术,因此,梳理、辨析佛教经典的内在差异与发展理路,摆脱黄老而自立,进而与儒、道平等对话成为佛教进一步发展的迫切需要。魏晋南北朝时期,政变不断,战争频仍,中央集权削弱,儒学独尊地位被打破,佛教传播获得了有利的思想和社会空间,儒释道的冲突与融合成为中华文明的历史趋向。鸠摩罗什在这一特定的时代背景下登上历史舞台。
不容忽视的是,东晋十六国时期的北方少数民族统治者对佛教的倚重是佛教迅速发展的直接助力,同时也制约着佛教的外在形态。一方面,他们视佛教的神异功能乃国之“祥瑞”,可为王者护国绥众,不可或缺;另一方面,他们为获得与汉民族在文化上的平等地位,刻意强调本民族“生自边壤”,“君临诸夏”,“佛是戎神,正所应奉”。但是,鸠摩罗什的卓越之处在于,他并不满足于后秦国师的“尊荣”,以及“闲阴阳”、“测吉凶”的神通展示,他真正的事业核心在于奉行和弘扬龙树、提婆的中观思想,他的思想伙伴和对手,除了以庐山慧远为代表的大乘涅槃学派,就是通晓般若、轻贱礼法、清谈玄理的魏晋名士。鸠摩罗什正是在魏晋玄学家那里找到了可以在中国哲学与佛教义理 之间相互转译、共同理解的典雅语言。
与魏晋时期的思想激荡类似,晚明虽然在政治上高度中央集权,但是社会思想上却相对活跃。[349]程朱理学虽被奉为正统,但是,遭到李贽等思想家最激烈抨击。儒释道“三教归一”成为普遍性的思想诉求。在利玛窦之前,基督宗教传入中国已经经历两次高峰。唐朝景教模仿佛教而兴盛一时,后因武宗会昌灭佛而殃及池鱼,一蹶不振。元朝也里可温教依附于政权进入中原,结果因元朝覆灭而在中原销声匿迹。明朝中叶以后,基督宗教第三次叩门中国。此时,欧洲经历了文艺复兴,耶稣会士为重振天主教影响而源源不断地踏上了东方传教之旅。耶稣会教育与传教结合,他们创办大学,活跃于政界、学界,传教士要求既接受严格的神学教育,又接受正规的大学教育。1551年,耶稣会创始人之一、西班牙人方济各·沙勿略到达中国广东上川岛,但是因为明朝严厉的海禁而无法进入内地传教,不久即病死于岛上,临终前发出“磐石何时开裂”的叹息。
富有戏剧性的是,身为耶稣会士的利玛窦乃是以“西僧”的身份叩开中国的大门[350]。1582年,利玛窦陪同罗明坚抵达肇庆,获肇庆总督赐与房屋,条件为“换上中国衣服,变成中国皇帝的子民。”在自我身份定位问题上,他们觉得基督宗教与佛教有某些相似,更为重要的是,明朝禁海令异常严厉,外国人不得进入内地,但是,自汉唐以来,外来僧人出入中国频繁,不会引人注目。于是,利玛窦改用中国姓名,削发剃须,身着僧衣,自称:“弃俗事天的僧人,来自天竺国,向慕中国政治昌明,愿得一块干净土,建屋造堂,终身事奉天帝。”1585年,利玛窦于肇庆城东建立第一所教堂。当地知府题赠匾额“仙花寺”、“西来净土”,前者悬于门首,后者挂于中堂。唐朝贞观年间的叙利亚传教士阿罗本融通佛教,受到唐代数位皇帝礼遇。但是,时移境易,利玛窦在经历了一连串的挫折后发现,如果仅以“西僧”的身份出现于晚明中国,是很难有所作为的,想见到中国皇帝难于登天,即使进入北京也几无可能。1594年,利玛窦接受瞿太素的建议并报请耶稣会总会长许可,取消“僧”名“寺”名,脱掉僧服,改着儒装,头戴方巾,自称“西儒”和“道人”,见客时以秀才礼应对。不仅如此,利玛窦“僦馆延师读儒书”,“居恒手不释卷,经目能逆顺诵”,[351]为走上合儒的传教路线奠定了坚实基础。
二、“改梵为秦”与文化“融入”
方立天先生指出,鸠摩罗什对中国佛学与中国思想界的影响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第一,推动中国佛教思想的发展进入一个新的阶段。第二,促进南朝学派和隋唐学派的形成。上述两个方面的影响都离不开鸠摩罗什的佛经翻译和对大乘空宗思想的弘扬,鸠摩罗什的佛教中国化或本土化策略亦主要通过这两项活动体现出来。
关于鸠摩罗什佛经翻译的创新和成就已经有了诸多的研究成果,本文主要从比较宗教学的视角探讨其译经工作在佛教本土化方面的重要影响。汉初以来,佛经翻译的质量问题受到多方面条件的制约,首当其冲的是佛经的来源及其可靠性问题。季羡林先生指出:“最初译为汉文的一些佛教术语,是通过吐火罗文的媒介,这个事实虽然是铁证如山,可是时间和过程,至今仍然是隐而不彰。我们只能推测,在佛教传入中国的初期,龟兹和焉耆曾起过中介作用(另外还有一条由大夏、大月支直达中国的道路) ,吐火罗文曾被使用来翻译佛经,否则就无法解释那些汉文初期佛教术语是怎样产生出来的。”[352]由此可见,早期佛经翻译所依据的原典多是吐火罗文“二手”版本,而当时的翻译方法又“多滞文格义”,逐字直译,导致汉译佛经与梵文佛经无论在义理还是辞章方面都相差甚远。鸠摩罗什译经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正本清源。403年,在长安逍遥园里,鸠摩罗什手持《大品般若经》梵文原本,姚兴手持前人所译汉文译本,八百僧人参与切磋,逐字逐句推敲对照,一时盛况空前。但是,回到梵文经典并不能解决翻译中所遇到的所有问题,相反,梵文佛经中所融合的印度文化特色与中印文化差异却因此凸显出来。鸠摩罗什真切描绘了这种差异,“天竺国俗,甚重文制,其宫商体韵,以入弦为善。凡觐国王,必有赞德见佛之仪,以歌叹为尊。经中偈颂,皆其式也。但改梵为秦,失其藻蔚,虽得大意,殊隔文体,有似嚼饭与人,非徒失味,乃令呕哕也”[353]。
这种文化差异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文字音节。南朝梁慧皎对此有精当的评点:“自大教东流,乃译文者众,而传声者寡。良由梵音重复,汉语单奇。若用梵音以咏汉语,则声繁而偈迫;若用汉曲以咏梵文,则韵短而辞长。是故金言有译,梵响无授”[354]。其二为宫商体韵。印度风俗以“歌叹为尊”,“然天竺方俗,凡是歌咏法言,皆称为呗”,佛教经典与古印度音乐融为一体,因入弦而繁复,动辄万言。鸠摩罗什之前的译经家对此有深切体认并作出了相应的努力。慧皎指出:“然夷夏不同,音韵殊隔,自非精括诂训,领会良难。属有支谦、聂承远、竺佛念、释宝云、竺叔兰、无罗叉等。并妙善梵汉之音,故能尽翻译之致。一言三复,词旨分明,然后更用此土宫商,饰以成制”[355]。此外,以曹植为代表的士人亦“深爱声律,属意经音。既通般遮之瑞响,又感鱼山之神制。于是删治《瑞应》《本起》,以为学者之宗”[356]。但是,充分尊重佛经原典的体例与音律的字面直译虽然尽可能多地保留了梵文佛经的外在特征,但是,这样的汉译经典却并不一定适合在中国的传播与流行。鸠摩罗什独辟蹊径,放弃直译,采取了更为本土化的意译。“曲从方言,而趣不乖本”[357],“文虽左右,而旨不离中”[358]。陈寅恪认为鸠摩罗什的意译“较诸家雅洁”,其特色有三:或删去原文繁重,或不拘原文体制,或变易原文。[359]鸠摩罗什所译《大智度论》,“三分除二”,仅得一百卷。在其全部翻译经论三百余卷中,“唯《十诵》一部未及删繁”。鸠摩罗什对于自己采取的删繁就简意译策略十分自信,他在给弟子的遗言中宣称:“愿凡所宣译,传流后世,咸共弘通。今后众前发诚实誓,若所传无谬者,当使焚身之后舌不燋烂。”
从比较宗教学角度来看,梵文佛经的歌咏与繁复特质源于印度佛教的宗教礼仪实践,是印度佛教的基本构成要素。因此,我们可以说鸠摩罗什的简洁译法削减了印度佛教的宗教性。在这一点上,玄奘与鸠摩罗什形成鲜明对照。玄奘“将顺众意,如罗什所翻,除繁去重”,但是,“作此念已,於夜梦中即有极怖畏事以相警诫”,转而“不敢更删,一如梵本”[360]。但是,事实却证明,玄奘译经数量多,鸠摩罗什译经流传广。
鸠摩罗什打破梵文佛经体制的制约后,在译经语言上自觉靠近魏晋士人的行文简约、风雅唯美特点,注重汉语自身的音律特质,并最终形成了一种中国化的佛经歌咏文体,以中国化的审美形式重新赋予汉译佛经以礼仪实践性。胡适称其“造成一种文学新体”,这种评价只是指出了鸠摩罗什译经的文学性一面,对其宗教性的创新并没有揭示出来。笔者认为,鸠摩罗什的译经策略体现了创造性融入的本土化策略,其译本经历了涅磐重生,获得了新的生命。据此而论,梁启超誉其为“译界第一流宗匠也”,鸠摩罗什是受之无愧的。
在宗教观念上,青年时期的鸠摩罗什由小乘改学大乘,精于龙树、提婆的空宗之学。大致来看,佛教的创立及其发展经历了一种“去神话化”和“思辨化”的过程,无论佛教相对于婆罗门教,还是大乘佛教相对于小乘佛教,其神话色彩越来越淡漠,而思辨性却逐步增强,以至于后来的学人甚至称佛教为无神的宗教。鸠摩罗什弘扬大乘,破斥小乘;宣扬无我义,破除“神我”论,与注重有无本末之辩的魏晋玄学形成思想上的契合。但是,这也导致了作为思想的佛学与作为宗教实体的佛教在某种程度的分离,以鸠摩罗什为代表的般若性空思想以佛学形态为社会上层的士大夫所青睐,而以庐山慧远为代表的涅磐妙有思想则主要以佛教形态流行于普通民众之间。
鸠摩罗什的“改梵为秦”是一种思想性的文化“融入”策略,其核心不在于一种宗教的对外传播,而在于不同文化之间的思想对话与交融。正因为如此,佛教作为一种宗教形态在印度逐渐衰落,但是,作为一种文化形态却因传入东土而发扬光大,并通过与中国文化结合而重新获得本土化的宗教形态。
三、“补儒易佛”与信仰“嵌入”
2001年10月,罗马教宗若望·保禄二世在《利玛窦到北京四百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致词》中给予利玛窦高度的评价:“利玛窦神父最大的贡献是在‘文化交融’的领域上。他以中文精编了一套天主教神学和礼仪术语,使中国人得以认识耶稣基督,让福音喜讯与教会能在中国文化里降生。由于利玛窦神父如此道地的‘做中国人中间的中国人’,使他成为大‘汉学家’,这是以文化和精神上最深邃的意义来说的,因为他在自己身上把司铎与学者,天主教徒与东方学家,意大利人和中国人的身份,令人惊叹地融合在一起。”
利玛窦开创的“文化交融”事业的核心在于儒学与基督教结合,他认为基督教在华的命运取决于“中国人是否能接受儒学与基督教结合模式”这样一个复杂的问题。[361]与利玛窦的一些后继者或批评者的理解不同,利玛窦的适应方法体现了一种精致的策略性,既具有对基督宗教信仰核心的固守,又包含了对儒家传统本质的理解。其结合模式是通过对中国古代经书的重新阐释,在儒学中吸取社会和道德成分,而基督教则贡献其宗教成分。若望·保禄二世认为,利玛窦的洞识基于早期教父们“在基督福音与希腊罗马文化相遇时的所作所为”。
利玛窦的“补儒”策略是与儒学保持了明晰的距离感和冷静的批判意识的思想对话。利玛窦认为,作为晚明正统的新儒学已经背离了儒学最初的内容,从原来的有神论走向了泛神论和无神论。基于基督宗教信仰的审视使利玛窦得出否定性结论:新儒学与基督教之间矛盾巨大,它们之间不允许有思想上的调和。因此,“补儒”必须另辟蹊径,《天主实义》中,利玛窦创造性地运用儒学的释经传统,将古代经书上的学说与新儒学的重新阐释区分开来。“余虽末年入中华,然窃视古经书不怠,但闻古先君子敬恭于天地之上帝,未闻有尊奉太极者。如太极为上帝—万物之祖,古圣何隐其说乎?”(《天主实义》上卷第14 b页。)具体来看,第一、利玛窦将“陡斯”与先秦典籍中的“上帝”等同起来,赋予“祀天”、“事天”、“昭事上帝”以基督信仰层面的宗教含义,并视之为先秦儒学的精髓和根本。第二,将宋儒确立的太极、理、气等本原、本体概念纳入“依赖者”范围。认为导致宋儒“错认天主”的原因有二:一是秦火之后,先秦典籍之真义不传;二是佛教东传的影响。第三,区分先儒与后儒,先秦典籍与后儒著作,先秦诠释与后儒诠释。主张“回到儒家先圣”以获得儒学道统意义上的“合理性”。
利玛窦的适应策略还体现在政治层面,他强调谨慎行事,主张“宁可少要几名好的基督徒,也不要一大批滥竽充数的人。”其后继者金尼阁指出:“这里的关键问题是,中国人承认我们完全不会策划革命事件,我们也不追求任何物质利益,而是前来传播独一无二的教法,这种教法与帝国的利益在任何方面都不会对立。”[362]为论证基督宗教能够在中国“补益王化”,耶稣会传教士们具有某种把欧洲描绘成田园诗般的形象的倾向,这种倾向影响和吸引了儒家士大夫,作为利玛窦的弟子,徐光启这样写道:“佛教东来千八百年,世道人心未能改易……必欲使人尽为善,则(西洋)诸陪臣所传事天之学,非可以补益王化,左右儒术,救正佛法者也。盖彼西洋邻近三十余国,奉行此教千数百年,以至于今,大小相恤,上下相安,路不拾遗,夜不闭关,其长安久治如此。”[363]
与“补儒”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易佛”。利玛窦一方面借用儒家反佛教的典型观点,宣称“没有什么比儒家给予佛教的恶名更具破坏性的了”;另一方面,针对佛教传入中国的传说,利玛窦争辩道,明帝梦佛传说其实是关于基督教的,明帝派遣的使团没有找到正在印度传教的使徒圣多默,误将佛教当成基督教带了回来。利玛窦虽然认为佛教不仅借用了希腊哲学家德谟克利特的世界多重性观点,毕达哥拉斯的灵魂轮回说,而且还似乎修改了基督教的三位一体说、天堂地狱观念,但是,他强调,任何本可以在佛教教义中找到的真理之光,都被彻底地混淆,并被荒谬掩盖了。[364]佛教寺庙成了“嘈杂的大旅店。”
利玛窦的“补儒易佛”策略具有丰富的层次性,具体表现为信仰层面的独立、排它;文化层面的融合包容、政治层面的主动适应等等。正如卡尔·巴特所说:“对福音最大的危险,不是它被拒绝,而是它被平和地接受,成为另一种不会伤人的属人的理性与文化。”[365]毫无疑问,传播基督宗教是利玛窦坚持的根本使命,从以上分析来看,信仰的外在“嵌入”正是利玛窦本土化策略的本质特征。其身后的中国礼仪之争主要责任似乎不在利玛窦本人,而在于利玛窦的后继者和批评者对其适应策略的平面化理解。[366]
四、“弥散性”与“主体间性”
鸠摩罗什之所以可以采取“改梵为秦”的宗教“融入”策略,不仅与佛教自身的宗教理论和组织形态密切相关,而且与中国传统宗教的“弥散性”特性内在契合。麦克斯·缪勒通过考察印度《吠陀》文献,将“否定原则”宣布为“一切宗教的根本原则”[367],作为印度宗教的“否定性”发展的佛教,不仅在思想层面具有鲜明的“自否定”特征,而且在组织层面表现出内在的“自我解构”特性,这就决定了佛教在传播过程中并不执着于对自身作为一个宗教实体的“主体意识”的坚持。与佛教作为宗教实体具有的“非主体性”特征相对应,“在历史的绝大多数时期里,在中国社会制度框架体系下缺乏一个结构显著的、正式的、组织化的宗教”[368]杨庆堃颇具创意地区分了“制度性宗教”和“弥散性宗教”,他认为中国传统的宗教信仰和实践弥漫在多种世俗制度当中,并且已经成为世俗制度的组成部分。“所谓弥漫性宗教,即拥有神学理论、崇拜对象及信仰者,于是能十分紧密地渗透进一种或多种的世俗制度中,从而成为世俗制度的观念、仪式和结构的一部分,失去了显著的独立性。”“正是这种弥漫的形式,使人们能够最大限度地接触到宗教。”[369]而作为弥漫性宗教的核心内容的祖先崇拜、作为道德意义超越之源的天、气、阴阳五行等观念又被吸收进儒家传统,发展成为儒家“宗教性”的组成部分。因此,具有“非主体性”特征的佛教与具有“弥散性”宗教特征的儒家实现某种实体意义上的“融合”,至少在逻辑上成为可能。当然,历史地看,佛教同时具备制度性宗教的一般特征,其“非主体性”从某种意义上恰好是其“主体性”的体现,佛教与儒家的“融合”并没有消解两者之间的内在张力。特别是晚明以来,伴随着与耶稣会“补儒易佛”的辩难,佛教作为宗教实体的“主体性”被“激活”和加强。
“补儒易佛”是一种“主体性”的宗教传播策略,利玛窦努力在信仰的“嵌入”与文化的“融入”之间保持平衡,但是在信仰与文化之间划出清晰的界限并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当文化“融入”的限度渗透到信仰领域时,“中国礼仪之争”首先在西方宗教、文化的核心处凸显出来。利玛窦只承认中国人是品德高尚的异教徒,但是,其索隐主义追随者却推出了更激进的文化适应观念:中国人和欧洲人在血统上和信仰上拥有共同的祖先[370]。礼仪之争中耶稣会代言人李明和郭弼恩分别在《中国现势新志》、《中国皇帝容圣教圣旨的历史》中表达了更系统、更明确的观念,其中对西方宗教、社会观念最具冲击性的论点包括:一、中国人近两千年来(即公元前2000年左右——公元1年)都保留着对真正的神的认识,并且他们敬奉神的方式就是对基督徒来说都是一种榜样和教导。二、犹大地的人献给上帝的神殿更富丽堂皇,甚至耶稣都到场并祈祷,来把它献给上帝,如果说犹大地的人在这方面更胜一筹,那中国人在世界上最古老的神殿中向造物主献祭,这对中国来说难道不是一种无上的虔诚吗?三、不管神圣的上帝是怎样明智地在世上各国间分配他的恩宠,中国都没有什么可以抱怨的,因为没有哪个国家比它得到了上帝更多的一贯的偏爱[371]。这些论点将东方异教徒视为西方精神领域的榜样,从而引发了有关异教徒与基督教救赎两者之间关系的激烈讨论,不仅如此,这些争论还关涉到在世界史范围内的人们对神的认识的演变和发展、在地理范围上对上帝恩宠的理解。1700年7月,索邦神学院对这些表述进行审查,并将这些观点鉴定为“虚假和轻率的”。我们并不完全赞同汉学家谢和耐将礼仪之争主要归结为“这是非常武断地把一个属于非常广泛范围的问题局限在一个仅仅于西方伦理范畴中才有意义的细节问题上。”[372]因为,在东方世界,在中国的士大夫、佛教徒中间,类似的争论以同样激烈的方式在持续进行。儒家所能够接受的“补儒”更多局限于对自身义理的外在确证和明晰化,康熙年间的《天儒同异考》乃中国天主教徒所著,该书分疏合儒、补儒、超儒,明确指出:“天壤间是有真理,儒教已备,而犹有未尽晰者,非待天主教以益之不可。”[373]中国礼仪之争已经关涉到“主体性”的宗教传播在信仰与文化之间的层次性问题以及各层次之间的差异与同一性问题。中国礼仪之争所采用的“主体性”思维模式一方面没有超越自我中心,另一方面又将信仰和文化平面化,其逻辑结论必然导致诸宗教、文明之间的关系只能是文明冲突论的暴力模式、商业竞争的资源攫取和占有模式、体育竞争式的强弱模式。令人遗憾的是,“在当前有关宗教对话的讨论中有一种忽视宗教对话的层次性从而把宗教对话平面化的倾向,如果任其发展下去,不仅有可能使我们或者墜入盲目的乐观气氛中,或者墜入消极的悲观气氛之中,而且还可能使我们的讨论误入华而不实的歧途”[374]。
在反思传统“主体性”思维局限性的基础上,当代学者提出“主体间性”概念,这种主体间性不仅适应于人类个体之间,也可以类比地运用于宗教、文明之间。哈贝马斯在“交往行为理论”中提出“互主体性”和“交往”问题,强调“不可替代的个人的自主性和所有人都植根于一种主体间共有的生活形式的事实”,[375]提倡一种以语言为媒介的“商谈伦理学”。我们比较鸠摩罗什与利玛窦的本土化传教策略,无非是想说明,不管是信仰层面还是文化层面,对“他者”的尊重、平等对待和包容是任何有意义的宗教对话得以正常进行的基本前提。从这个意义上说,无论是鸠摩罗什的“非主体性”的文化“融入”模式,还是利玛窦努力在信仰“嵌入”与文化“融入”之间保持平衡,身体力行儒学与基督宗教的结合模式,都体现出一种现代意义上的“主体间性”特征,因此,我们似乎可以说鸠摩罗什和利玛窦是哈贝马斯“商谈伦理学”的最初探索者和实践者。
学术新人
涩泽荣一的《论语》观研究
宗辰欣[376]
内容提要:涩泽荣一本着“实学主义”的原则汲取《论语》之精粹,经由对《论语》义利观的创造性诠释建构起“《论语》与算盘”结合的儒家经济伦理,用以指导实业,并以《论语》的天命观和“穴居主义”、“知行合一”的修身观来安身立命。其经济伦理不仅贬抑了贱商思想,使得日本工商业大兴;且对工商业者的道德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他以“士魂”辅助“商才”,“义利合一”成为工商业活动的原则,促进了日本经济的良性发展。本文通过对涩泽荣一的“实学主义”思想、经济伦理思想、天命观和修身观的探讨,力图呈现其对《论语》继承和改造后的思想体系,希冀能对中国的经济发展有所启发。
关键词:涩泽荣一 《论语》 经济伦理 义利 实学
《论语》采撷了孔子生平的言传身教,以修身、治国之道授人,流传至今日已两千多年,其精粹深深嵌入了中国人的骨髓,甚至影响了包括日本、朝鲜等在内的东亚文化圈。
涩泽荣一关于《论语》的思想孕育于江户时代,成熟于明治时代。他少年时期习《论语》的经历及江户时代混乱的工商业状况皆是其思想生发的引子。而其思想形成的契机则是明治六年的弃官从商,他开始以《论语》的教诲作为其从商所秉持的信条。涩泽荣一的一生,所参与的经营事业近六百件,几乎是日本社会各方面的创立者和指导者,为日本的现代化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被称为“日本企业之父”、“日本资本主义之父”、“儒家资本主义的代表”等。
涩泽荣一深受儒家义理的熏陶,幼时即学习儒家经典,《论语》对其影响尤为深远。“我生平尊奉孔子之教,同时以《论语》为处事的金科玉律,经常铭之座右而不离。”[377]他勤读论语乃至于韦编三绝,并组织《论语》学习会,在企业里也经常以《论语》教育员工,资助《论语》研究活动,收集各种《论语》注本,现存于东京都立图书馆“青渊《论语》文库”就有243种,可见其信奉《论语》之心甚笃。
涩泽荣一撰写了数本著作以阐述其思想。成形于1909年的《论语与算盘》是其集大成之作,奠定了“义利合一”经济伦理的基础。他将《论语》作为第一经营哲学,与“算盘”相结合,既讲精打细算赚钱之术,也讲儒家的忠恕之道。“论语与算盘”的经营模式为各企业所借鉴,成为了日本近代化过程中的推动力。为了普及《论语》,1925年他撰写的《论语讲义》结集出版,他在阐释过程中着眼于经济,强调道德存在于实际行动中,主要针对经营者来谈作为道德核心的“信”。他的经济道德理论使得工商业者开始注重诚信,促进了日本的工商业快速发展及经济环境的有序化。
一、 实学主义
涩泽荣一否定后世儒者解读《论语》时空言心性天理使得《论语》艰深化的解读,而将《论语》视为“一种普泛的实用教诲”, 是“一言一句悉能立用于日常处世实际的教,说的都是朝闻之、夕可行之的道”[378],浅近易解,可应用于士农工商各阶层之人。他强调其日常实用性,认为“修养不是理论”,而是需要亲身践行的,不能像后儒 “只研究章句之末而远离实行”。这种对于学问实用性的推崇正契合当时日本各领域亟需振兴的境况。
涩泽荣一承袭批朱派的观点,认为朱子的“学问与实际完全隔绝,经学到了宋代尽管有了很大的振兴,但并没有把它运用到实际中”[379],其将富贵货殖视为不义的观点是与现实脱节的。而《论语》则蕴含了货殖之道,更具有普适性。但他也客观地指出,“《论语》的章节中,因时代的关系,也有于今日之世不能原封不动加以应用的内容”,故他顺应时代发展的要求,在总结其企业管理经验的基础上,以西方观念如重商思想、重利思想对《论语》加以积极改造和创造性的转换。他发掘出《论语》中可用于指导实业和塑造人格的道理,将《论语》与算盘相结合,创立了义利合一的经济伦理思想,并运用其理论创立了多家企业。他亦强调“知行合一”的修养论,他以《论语》修身,还以《论语》教育员工,为其撰书诠释以教化百姓。《论语》不再仅仅停留在理论层面上,而对社会生活和个人修养皆有裨益,实现了实学主义经世致用之目的。
二、经济伦理思想
《论语》与算盘,看似毫不相关甚至是以传统儒家伦理看来是背道而驰的两样事物,在涩泽荣一的眼中是紧密相连的,“《论语》与算盘的关系是远在天边,近在咫尺”,甚至是相辅相成的,“算盘要靠《论语》来拨动;同时《论语》也要靠算盘才能从事真正的致富活动。”《论语》被用来指导商业活动,“我觉得,遵循《论语》的箴言进行商业活动,能够生财致富。”对这一做法,他解释道:“我之所以爱读《论语》,是因为本来商人是争铢锱之利的,贤者如有一步失误的话,是为利而失道的,更何况商人生活在世俗社会之中,如无防止失误的规矩准绳,那么是很危险的。”[380]
德川时期的商人奉持现金主义,轻信义、重金钱,认为只要能赚钱,便可以抛弃道德规范的约束。明治前期,特权商人和城市农村中小商人贫富差距极大,商业思想禁锢,商人趋利而失德,涩泽荣一不禁为此现状担忧:“我们日本的工商业者却还不能完全摆脱旧有的习惯,往往存在着无视道德观念、图暂时的利益的倾向,真令人感到不安。”[381]针对此现象,他提倡以《论语》之教来修身,提高商人的道德水平,使得经济与道德可以共同发展。
1、工商兴邦
封建时期,日本以农业经济为根基,亦受中国文化影响,认为商业会动摇封建制度,对外采取了“锁国政策”,限制对外贸易,使得商业发展滞缓;对内则一直实行严格的士农工商身份制度和重农抑商政策。根深蒂固的贱商思想使得商人社会地位低下,处处受到歧视和限制。维新以后,对外贸易增长,政府以“殖产兴业”为方针,政府和商人的关系也愈加密切。尽管商人阶级勃兴,但贱商思想仍旧存在,商人亦鹜求利益而不顾道德,政府愈加打压商人阶级,经济发展迟缓。
涩泽荣一十分肯定商业的重要性,力图提升商人地位。在考察西方各国工业文明时,他对于西方的重商主义感到惊讶不已,他发现西方并没有“官尊民卑”的思想,商人地位与官员平等,甚至是欧洲君主都十分关心国家的工商业发展。西方的商业经营理念、商业行为准则和商业价值评判都让他受益匪浅。他认为一个国家的富强,是建立在工商的兴盛之上的,“欧美各国之所以能获得那样的繁荣,完全是由于工商业的高度发展”[382],而“日本,商业最为不振,商业不振就不能增进国富”[383],故他摒弃了日本传统的贱商思想,“产生了谋求工商业发展的想法,从此开始定下成为实业界人物的决心”,[384]大力提倡振兴工商实业,并怀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身先士卒地投入商业。
涩泽荣一在面对资本主义的思想和日本的经济现状时,试图在《论语》之中找寻到兴工商的理论依据,他以西方的重商观念为出发点来重新诠释《论语》,一反陈见,摆脱后儒对孔子义利思想的阐释,认为孔子并不反对富贵,只是反对不仁不义之富贵。他说:“自古以来,信奉儒家的学者对孔子的学说一直存在误解,这当中对孔子的富贵观念和货殖思想的误解是最为严重的。按照他们对论语的解释,仁义王道与货殖富贵两者犹如水火互不相容,可实际上翻遍论语二十篇,根本找不到诸如富贵者无仁义王道之心,而要做一个仁义的人,就必须抛弃富贵观念之类含义的话。事实上与人们的误解相反,孔子恰恰是主张人们走殖货之路的。”[385]如《论语·里仁》篇云:“富与贵,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说明富贵是人人皆渴求的,当然也包括孔子,但需要以正道得之。《论语·述而》篇云:“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意即经由正道得来的财富,便可以去追求,即使地位低微也不排斥。《论语·泰伯》篇云:“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国家运行有序时仍贫贱多数是因为懒惰,而国家大乱时富贵则多因无德。可见孔子并不鼓励贫穷、鄙视富贵。《论语·子路》篇云:“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 教之。’”意即孔子主张在人口众多的基础上使人民富裕起来,再施行教化。孔子对于富贵的认可态度促进了人们在满足其物质需求上追求更高的精神需求,行事以义为先。孔子提出其理论是希望能得到人们广泛的践行,若脱离实际,一味“存天理灭人欲”,则难以被普通百姓所接受。涩泽荣一以孔子的货殖理论批判鄙视富贵和贱商思想,而以工商为富民兴邦之本,并依据儒家道德伦理建立起一套规矩以指导工商业者的行为,使得商业活动能得以有序地开展,正契合了《论语》庶、富、教的思想。
涩泽对于孔子义利观的新诠释是应时代要求而生的,是为了使当时的人们不耻于从商、国家不抑制商业发展,从而促进国家经济的发展。他对于《论语》中“重义轻利”的取向也并未多言及,可见其理论是出于实用性需求而对孔子思想进行的改造。
2、 士魂商才
涩泽荣一将“士魂商才”作为日本工商业者的理想人格,“士魂商才的真正意义,就是要具有卓立人世间所必备的武士精神,但仅有武士精神而无商才的话,在经济上又会招来灭亡之运,故有士魂尚须有商才。”[386]商才为士魂提供物质基础,而士魂为商才提供可持续发展的动力和精神上的升华。涩泽荣一将士魂和商才对举,即是将士与商放在了平等的位置,提升了商人地位。“古来日本人尊武士认为做政府官吏为无上光荣,做商人为耻辱,此乃本末倒置。”[387]
涩泽荣一以武士道为商人提供内在的精神力量,“武士道的真髓是正义、廉直、侠义、礼让、敢作敢为等美德,故一言以蔽之,称为武士道。”[388]
武士道亦承袭神道教教义,以忠君爱国为行为准则。日本的武士最早出现在大化革新后不久,应贵族藤原氏、平氏、源氏家族保护领地和壮大势力的需求而产生,战国时代形成为特权阶层,是社会组织的中坚。武士及其家庭皆附庸于主家,绝对忠诚主家,并通过等级制度层层隶属的关系,全国的武士都要效忠于天皇。武士的理想生活是“血和泪”的生活模式,“血是对家主的牺牲,泪是对百姓的怜爱”。[389]“轻生死”、“重然诺”、“当意气”是武士独有的特性。武士道的基础就是封建制度下面的食禄报恩主义。儒学传入之后,日本人便在汲取了儒家思想的基础上阐述武士道。如山鹿素行称武士道为“道的自觉”,强调武士道以忠孝为本,制定出一系列礼法来规范武士的行为。新渡户稻造认为:“儒家孔子的教导是武士道最为丰富的渊源。他的政治伦理,主张平静、宽厚、处世智慧,非常适用于构成统治阶级的武士。”[390]但武士修习儒家学说只是为了获得智慧,武士道的本质仍是“和魂”。至明治时期,又融入欧洲思想,成为维新时期中的政治道德的基础。武士道亦逐渐成为一种民族精神,推动着日本前进。武士道的演变过程可概括为“由制度论的武士道,一进而为道德论的武士道,再进而为信仰论的武士道。”[391]武士道深深锲刻于日本人的灵魂之中,其影响潜移默化,并未随着社会变革而消亡,而是以纵式社会结构中的“亲子关系”和以“情”为主调的企业伦理这一新形式保留于日本当今社会。
武士道融入工商业可以说是涩泽荣一的“士魂商才”说的成就。日本封建时代的商人多是市侩、势利、人格卑陋者,因为“商人在社会阶级上既然处于被治的阶级,住的地方又和治者阶级接近,所营的生业又要依赖治者阶级,只在一种极鄙陋暧昧的空气里面,作世袭的守财奴,性格上自然发生出很龌龊的鄙卑习惯来。人格上毫无地位的商人,当然不会有高尚的德性,因为高尚的德性,不但不能够帮助他的生活,反而可以妨害他的生活。”[392]商人的大量财富没有太多途径能向产业资本转化,便向农民放高利贷,而后获得无钱偿付的农民的土地,使得大量农民失去土地沦为佃农。商人积蓄了钱财后便用以寻欢作乐,生活奢侈无度。武士对于商人是十分鄙夷的,将商人的习性称为“町人根性”。“日本封建时代所谓‘町人根性’,一方面是阴柔,而一方面是残酷,以政治上的弱者而争生活上的优胜,当然会产生这样的性格。”[393]涩泽荣一不满于这种“町人根性”,提出不能背离道德而存在的“商才”概念:“所谓商才,原应以道德为本,舍道德之无德、欺瞒 、诈骗、浮华、轻佻之商才,实为卖弄小聪明、小把戏者,根本算不得真正的商才”。[394]他以武士道来改造町人根性,他认为,“为人处世时,应该以武士精神为本”[395],“日本人必须以充满大和魂的武士道来立身,不论是商业,还是工业,如果以此心作为精神,在工业上也能争勇于世界之林。”[396]他指出,武士道即实业道,“今直移武士道为实业道可也。”[397]
明治初年,废藩置县后,武士的世袭财产、职务特权、知识特权都被取消。武士道中蕴含的鄙弃金钱、忠义诚实、不谄媚逢迎等道德品质使得武士难以与狡诈的商人竞争,武士境地愈加悲惨。涩泽荣一便指出,作为“充满大和魂的武士道的根基是《论语》,但后儒片面地解释了它,向社会传播了错误的观念”,[398]这使得国人以富贵、功名为恶,导致了道德高尚、以身报国的武士们贫困潦倒。他认为士魂还需要辅助以商才,来保障其物质条件,免遭食不果腹之厄运。
涩泽荣一提倡以《论语》来塑造士魂商才,士魂和商才两方面都需要经由对《论语》的学习,“只有《论语》才是培养士魂的根基”,“商才也要通过《论语》来充分培养”。
3、义利合一
义,宜也,指事物或现象的最适宜的状态。这是西周至春秋时普遍的定义。它是动态的行为原则,而不是僵化的道德教条。在孔子思想中有所引申,也指与“他人”相对的“自我”而言,以其为构成理想人格的道德禀赋。利,利益也。追溯中国古代的哲学思想,“义利之辨”一直贯穿其中。
早期儒家经典中多呈现 “义利合一”的思想。《周易》中,“利”作为乾卦的四德之一,“乾,元、亨、利、贞”。利者,利物也。天有善、美、利物、贞正之四德,可见利地位之高。《象传》:“利者,义之合也。”和,相应也。有义而后有利。还说:“利物足以和义。”利物即利人,利人完全合于义。《国语·周语下》也说:“言义必及利。”《大学》中,则讲“以义为利”的思想,“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强调以仁义治国,就必然会有合理的“利”,体现了“义以生利”的思想。“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财,有财此有用。德者本也,财者末也。”即是德能生财。“仁者以财发身,不仁者以身发财”又强调了有仁德之人只是以财为手段,而对自身和社会发展孜孜以求,保全了生命、人格、尊严。
孔子提倡“见利不亏其义”(《礼记·儒行》),将其视为君子应有的一种品格:“君子义以为上”(《论语·卫灵公》),“君子有九思: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疑思问,忿思难,见得思义。”(《论语·季氏》)他将君子与小人对比,通过小人行事不思虑后果、只贪图眼前的小惠而突出君子以义为先的品质:“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君子怀刑,小人怀惠。”(《论语·里仁》)对于君子和小人,“义”都是行事时不可或缺的基本原则:“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小人有勇而无义为盗。”(《论语·阳货》)孔子虽然主要强调要“以义为上”,但并未完全否定利,而是“见利思义”,“义然后取”(《论语·宪问》)。
细析儒家的义利观,主要有三种取向:1、义务论:董仲舒、朱熹等将利视为对义的阻碍,否定利的价值;2、目的论:南宋功利派、清儒颜元等以利解义,先义后利,义成为手段,利成为目的;3、公私论:孟子、程颐等以公利为义,以私利为利,“义利之辨”最后归结到社会与个人的对立,应以公利为先。
对于儒家“义利”观的演变,涩泽荣一认为:“孟子也主张谋利与仁义道德相结合,只是后来的学者将两者越拉越远,反说有仁义而远富贵,有富贵则远仁义。”[399]朱子学派对于孔孟学说的误读使得孔孟学说不切实际、虚无缥缈,“造成从事于利用厚生的实业家之精神几以利己主义为本”[400],仁义道德不为工商业者所重,而成为圣人一般的理想化人格才具有的特质,愈加远离百姓而难以实行,则社会贫富差距加大,民风逐渐沦入卑鄙无耻之境。为了除宋儒义利学说之弊,他指出道德和财富应相结合,“抛弃利益的道德,不是真正的道德;而完全的财富、正当的殖利必须伴随道德”[401],谋利的同时必须重视仁义,“真正的谋利当以仁义道德作为基础,否则绝不可能传之久远。”[402]“谋利和重视仁义道德只有并行不悖,才能使国家健全发展,个人也才能各行其所,发财致富。”他将此信念总结为“义利合一”:“极力采取依靠仁义道德来推进生产,务必确立义利合一的信念”。
涩泽荣一将“义利合一”原则运用到工商业之中,倡导基于仁义来谋求利益:“所谓实业,无疑以谋求利殖为本旨。若商工业无增殖之效,商工业即无存在的意义。……但所谓图利,如果全为一己之利,根本不顾他人,那又不然了。……真正的利益,若不基于仁义道德,则决不可永续”。[403]仁义道德与工商业的可持续发展相连接,“至如工商实业,亦当以仁为大本。仁为大本,则工业无粗制滥造,商业无骗瞒诈术,商工道德自然提高。”[404]提高商工道德则必然会获得消费者的信任和口碑,则扩大了市场,盈利必将更多;若反其道而行之,为了一时之利而抛弃道德,则产品的粗劣和销售中的欺骗必将被揭发而使得信用破产,生意难以维持。可见“义利合一”是工商业者在从事实业过程中必须贯穿始终的原则。
3、 公利与私利
儒家在“公利与私利”问题上一向偏重“公利”,强调国家人民利益至上。《论语·雍也》篇云:“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可见孔子认为“私利”是经由追求“公利”而实现的。程颐将义利问题转化为公私问题,以“理”为公,“利”为私:“理者天下之至公,利者众人所同欲。苟公其心,不失其正理,则与众同利;无侵于人,人亦欲同之。若切于好利,蔽于自私,求自益以损于人,则人亦与之力争,故莫肯益之,而有击夺之者矣。”“私”逐渐被视为“奸邪”,而受到排斥。
而在日本,并没有将“私”置于道德层面上而否定“私”。“私”作为独立于“公”的领域,限于狭小的单一家庭。在“私”的领域,有世袭和职业专门意识的继承。在朝廷、国家的“公”的领域,日本并没有似中国一样在 “公”的概念上派生出的平均分配含义。沟口雄三认为,“在日本‘公’的领域经常是优先于‘私’的领域,这是在明治时代建立在封建上下关系概念上的一种集团式的资本主义。”[405]
涩泽荣一将公私理论由政治领域延伸到经济领域,他认为“作为工商业者必须时刻牢记一件事情,那就是所说的公益和私利之分”[406]。公益与私利并不是水火不容的关系,而是共生的,涩泽荣一阐述道:“通过各自经营而获得的私利与公益没有什么不同。 ……也就是说通过从事某项事业而得到的私人利益也有益于公家,而从事可以给公家带来利益的事情对私人也是有益的,也能造福于子孙。这样看来,原来把私利和公益对立起来是错误的”[407],以追求公益为目的的行动必会促进私利的获得,“谋求社会利益、使国家富强,终究会给个人带来利益”[408]。
涩泽荣一认为人各有其分,“大约人活在此社会上,必有其应尽的义务。即各人应其分,就职务,由近及远,先行于乡党邻里,及一郡一县,再及于国家社会。”[409]他在强调社会义务和分工的绝对必要性基础上讨论“公”的意义,即道德的必要性,“吾人共存此世上,谁也不能一个人活下去,应该相依相助。道德的必要性即由此产生。”“本来营商业肯定是为了自己而从事的一种行当,但若认为商业这职分只是为了自己,那就大错特错了。照理说,一方生产商品,一方消费商品。立于其间,全其互通有无职分,便是商业的目标。而此行为,应当互相依靠帮助。不管你多么想一个人独力去做,那是谁都办不到的。”[410]人是社会动物,离开社会难以生存,故人行事不能只考虑自己的利益,而需要顾及社会利益,行使社会义务,对社会负责,正如涩泽所说,“作为国民不知有君国,生为人不知有社会,便不会有真正的基于人生意义的行动。而忘了国家,忘了社会,其做人不就与禽兽相去不远了吗?”[411]
涩泽荣一以国家利益为唯一的公益,“任何事业,如果不是在国家观念下策划,便没有作为事业的价值,也就不容许存在。”即使企业肯定会有利于一个整体,一方民众,但是如果它不是有利于国家,就是一种私益,没有存在的价值。故他提倡人们在谋利时因先考虑是否有利于国家,追求“诚意而得之利”:“超越私利私欲观念,出于为国家社会尽利益就是国家和社会的利益,而为了国家和社会的利益从事工商活动就是他所提倡之诚意而得之利”[412]。“至于致富的手段则首以公益为宗旨,绝不做出凌虐他人或加害他人的举动,亦不欺骗、不诈伪。而且,各尽其职之所应尽,不被道理以求其富,则无论如何发展,将不会发生与他人相侵相害之事”[413],则其事业可久存。这不仅是出于利益上的考虑,还出于道义,合于日本武士道的“报恩”精神,对社会给予自己的心存感恩,以尽其义务来报答社会。故他对富豪倡议,“举凡社会救济,公共事业等等,要经常率先参与尽力,则社会才能日趋健全,同时,自己的资产运用也能渐次稳健踏实。”反之,富豪们若是吝啬于锱铢而漠视社会之事,“则富豪之士与社会民众必然会产生冲突。不久,对富豪的怨嗟之声就造成罢工罢市,其结果将招来极大的损害。” “因此,谋取财富的另一面,应常常思及社会的恩谊,无忘对社会尽到道德上的义务。”[414]
三、天命观
“天命”即“天的命令”,指由自然的规律、法则而感受到的上天的意志,也指上天主宰之下的人们的命运。这种自然的规律也可称为“天道”,常与人道对称。天道与人道一致,以天道为本。
孔子重视人道,罕言天道,《论语·公冶长》:“子贡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他的天命观因没有系统的论述和其只言片语在字面上的龃龉之处而在后世产生了两种相反的解读。冯友兰和蔡尚思即认为孔子的“天”是有意志的人格化的上帝,是人类和自然界的最高主宰。[415]徐复观则认为“孔子的‘知天命’即是他的本心的全体大用的显现,所以他不是神秘主义。”[416]郭沫若认为孔子所言之天仅仅是一种自然的力量,并非人格性的存在,“他既否认或怀疑人格神的存在,那么他所说的命不能被解释为神定的运命……而应该是自然界的一种必然性。”后者之论更符合实际,《论语·述而》篇记载:“子不语怪、力、乱、神”,可见孔子并不信奉神秘主义的“天”。孔子的天道观实质是自然之天、道德之天。在自然之天的层面上,“天”被视为自然外在于人类的物质实体,《论语·阳货》:“子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万物生焉,天何言哉?’”天作为一种自然规律,并无意志,只是由四时和万物的运作中显现。人类也必依循规律而生息,无法超越、驾驭自然规律,故需要尊重自然规律,对于自然怀有敬畏之心,即“畏天命”(《论语·季氏》)。在这里,天命对人具有了约束作用,又具有了道德层面的意味,成为内在于人的道德之天。人的命来自于天,是与生俱来的。孔子所说的命,是指人的性命、生命历程的轨迹,其走向不是人所能决定的。《论语·颜渊》:“子夏曰:‘商闻之矣;死生有命,富贵在天。’”《论语·宪问》:“子曰:‘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孔子“五十而知天命”,是指自己到了五十岁之后,才逐渐地体悟到了客观世界的规律。《论语·尧曰》:“孔子曰:‘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孔子言“知命”,就是提醒人在任何情况下,都要能够认识到人在大自然规律面前要能顺从大自然的规律,并以此来自省,从而在顺应自然规律的基础上奋发有为。孔子的道德之天为孟子发扬为其仁义学说,其自然之天则被荀子吸收而形成其“天人相分”说。
涩泽荣一的天命观承自孔子,他认为“天即天命之意”,世界万物皆遵循天命,自然界和人的命运并不受人的意志支配,可见“人是不得不顺天而行的”。而天并无意志,不会对人间降福降灾,亦不会受人的意志左右而产生奇迹,属于自然之天的层面。正如涩泽所说,“不把天当作是有人格有灵性的动物,也不要认为天命会偶尔产生流行于天地、社会之间的因果报应的法则,人只要以恭、敬、信的信念去对待天,就是最好的方法了。”[417]这种对天的恭敬表现为“不以人力必胜自夸,不勉强而为”[418],而是依循天道而行,“行自然之大道,不做一丝一毫不合于理的事情,且时时内省而不疚者……才能得到真正的安身立命之所。”[419]这正使得天对人有所约束,有了道德之天的意味。可见涩泽荣一的天命观具有孔子自然之天和道德之天两个层面的含义,并不像孟子和荀子一样各自有所偏倚。
对于人与天的关系,他并不听天由命,而是肯定人的努力,即“尽人事,待天命”:“生民为士、为农、为工、为商,亦是天命。安其命不起非妄为善。然此所谓安于天命,是尽人事以待天命之谓,不是要人自始即不努力,当尽之责亦不尽,安逸呆坐而万事听天由命。天命无常,勉则福,怠则祸,人谁敢不努力?”[420]必须强调的是,涩泽荣一所提出的“尽人事以待天命”,不是尽传统儒学的五伦中的人事,而是尽为国为民的大事。
涩泽荣一的天命观是积极入世的,为其经济伦理建构了形上基础。人们为了眼前之利而不顾及社会、环境乃至后世,有悖于天道而终会自尝苦果,故他以天道来规范人类在各自领域内的行为,使人们不去强行做违背自然规律之事,而在行事之前先考虑国家和人民。人类亦不是消极顺从天而无所事事,而是在依循天道的基础上不断进取,方能有所成就。
四、修养论
涩泽荣一十分注重修养,他认为,“所谓修养,是修身养德之谓,包含练习、研究、克己、忍耐等所有的意义,使人渐渐向圣人、君子的境域接近的一项奋斗,并不会因此就扭曲了人的自然天性。”修养有裨于为人处世,“修养累积愈深厚,其人就愈明了处事接物之善恶,因此,面临取舍去就之际就不会迷惑,而且还能从善如流。”[421]
涩泽荣一承袭《论语》之教,以《论语》来修身养性,“《论语》说了些什么呢?不外所谓‘温良恭俭让’,‘恭宽信敏敬(惠)’,‘言忠信,行敬笃’,以及‘夫子之道,忠恕而已’之类。就是教人要以恭谦之态度接人,以信义交人。我是在这样的注意的教育之下长成,又以如斯之信念为自己终生的行为标准。”[422]
1、“穴居主义”
涩泽荣一以“忠恕一贯”为其处世方针,对任何人都以诚意待之,出入进退、起居饮食、喜怒哀乐等皆从孔子所教诲的一般有所节制而不逾矩,着眼于细节,在日常生活中践行道德。这正体现了涩泽所秉持的“穴居主义”,即安分量力,像螃蟹那样只挖掘合于自己甲壳的洞穴,在进取过程中时时谨守本分,不抱非分之想,则不会滋生事端。“穴居主义”也并不否定进取,而是否定孤注一掷、不考虑后果的盲目行为。这种“穴居主义”正是儒家所倡的“中庸之道”,通过人们的自我修养、自我监督、自我教育、自我完善,把自己培养成为具有理想人格,达到至善、至仁、至诚、至道、至德、至圣、合外内之道的理想人物。
涩泽将“穴居主义”归结到“诚”,“凡事诚心诚意,任何事以诚律之”。“诚”是天的法则,而人道就是追求诚,通过诚便能处事合理,达到中庸之道,《中庸》说:“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诚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圣人也。诚之者,择善而固执之者也。”可见“诚”既属于伦理道德范畴,又属于本体论范畴。儒家以“诚意”来“正心”,《礼记·大学》:“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诚意”意为使其意念发于精诚,不欺人,也不自欺,《礼记·大学》:“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恶恶臭,如好好色,此之谓自谦。故君子必慎其独也。”“诚意”的关键在于“慎独”,即在独处中亦坚守道德、谨慎不苟。而在日本伦理思想里,“诚”与“忠”是紧密相联的,“诚”也就是“忠诚”。或者说,“诚”的具体落实就是“忠”。由于武士道精神与天皇崇拜观念的结合,“诚”又往往体现为一种非理性的冲动,即对天皇与上级绝对忠诚意义上的狂热。涩泽深受日本武士道精神和儒家伦理影响,其强调的“诚”不仅有儒家对人对己不欺骗的含义,还具有忠诚于天皇、国家的意味。故这种“穴居主义”是对于人们行为的一种节制,以“诚”为标准来行事,在行事前先考虑是否符合道德标准,是否对国家人民有利,从而始终忠实于自己和国家。
在陷入人生的逆境之时,这种“穴居主义”正适合于人们安身立命,“一旦面对自然的逆境时,首先领会自己的本分是什么才是唯一良策”,唯有如此才能豁达知足,认清现状,不贸然行动或者怨天尤人,而是正如《周易·乾卦》所云“潜龙勿用”一般韬光养晦,待机而动。在此藏锋守拙的时候还应不断加强自身学问修养,即涩泽“尽人事以待天命”观点,“应安于天命,慢慢等待应该到来的运命,不屈不挠,勉力勤学为上策。”[423]
2、精神修养
涩泽荣一以儒家的“孝悌忠信”作为修养之法,“儒家注重孝悌忠信之道才是具有相当权威的人格养成法。”而孝悌忠信的内核是仁义之心,即“以仁为本”[424]。儒家以孝悌为基础,推及忠义,“德”与“礼”使得仁能在各个关系网中得到广泛施行,正如《论语》所云:“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
涩泽面对当时的社会教育只注重知识教育而不关心道德教育的现状甚为痛心。过去的教育虽然是精英教育,只限于武士,但多以汉学教育之,书籍多专注于心灵,探讨精神修养,故“过去的青年总是能自然地修养其身,且常以天下国家为忧而养成素朴质实、重视廉耻,以信义为贵的气习。”[425]自1872年明治政府颁布了日本近代教育史上第一部教育法规《学制》开始,汉学遭到摒弃,该法规全面主张西方近代资产阶级的教育思想和理念,把传统的儒教说成是“虚理空谈”,使得过去经由汉学进行的精神教育而今无人顾及,乃至于社会道德水平大不如前。这可以说是现代教育之弊。而明治政府也渐渐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峻性。1879年,明治天皇亲自颁发了《教育大旨》,重新强调坚持儒家伦理道德观念的重要性,政府也随之改变态度,颁布了《改正教育令》,提出要重视修身,明确规定道德教育的中心就是尊祖训、明忠孝、学孔道。此后在1890年明治天皇又颁发了《教育赦语》,不仅再次肯定儒家道德,并把天皇奉为道德的化身。儒家伦理伴随着道德教育再次进入人们的视野。
涩泽对于农工商教育缺乏的情况亦十分不满,早先面向百姓开展的普通教育水平很低,只教授极浅近的行为教育及数学运算等。百姓无学识。维新之后,商人仍被认为不需要拥有太高深的知识,直至明治17年才渐兴商人教育。但这种教育并无精神教育的内容,只关注科学知识和致富知识,精神教育日渐衰微。人们只汲汲于物质而忽略精神文明,涩泽叹息道:“故物质文明进步的结果,反而害了精神文明的进步。”
涩泽面对此境况,大力提倡商人教育,并指出应以儒家伦理进行道德教育,以提高精神修养。精神与财富缺一不可,故他提出:“精神的向上和财富的追求必须齐头并进,而人应该秉持的坚强信仰也必须由此出发。”而修养精神则必须不断学习,“要使精神不衰弱,除了依赖学问之外,别无他法。一个不断求取新知、不落时代之后的人,其精神当永无老化之时。”[426]
3、知行合一
智慧是一个人为人处世的关键,“大凡人立于世,最重要的莫过于求智慧的增进。”[427]智慧能帮助人辨别是非,趋善摒恶,“如果人的智力发挥得不充分,识别物的能力自然就不足,一旦成为不能识别物之是非善恶的人,或对利害得失都无法鉴定,那么纵有学识,比如能认识善者为善,能看出利之所在,由于不能将其付诸于行,那么此人的好学问只好归于徒然了。”[428]
而行动则是体现智慧、帮助修养的途径,在以智慧判别了是非后就应坚定信念,大胆进取,“只要自信自己的作为是正义的,就应以进取的、刚健的行为,奋斗到底。”[429]
正如王阳明所倡导的“知行合一”,涩泽荣一也指出,知识和行动在修养自己的过程中应相结合,人应注重精神修养以提升智慧,并通过力行来实现精神修养,“今日的修养要以勤勉力行为主,才能得到完全的智德。亦即在精神方面倾注心力,同时也应求知识的发达。”涩泽所倡的修养更是为国为民的,“不单为了自己一个人而修养,也必须为一乡一邑,乃至于国运之兴隆而贡献己力。”[430]这正合于儒家以天下为己任的胸怀。
涩泽荣一时时遵循儒家伦理而行,“知行合一”在他身上得到了完美的体现。他不仅将儒家思想运用于实业,诚信经营,还以儒家伦理修身,待人接物无不体现其仁义之心,他对于教育、慈善等公益事业的热情更了体现其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这也正是对儒家君子人格的践行。“知行合一”也是其“实学主义”思想在修身观方面的体现。
五、涩泽荣一《论语》观的启示
涩泽荣一通过挖掘《论语》经世致用的内在精神,对其中的义利观进行了重新诠释,他根据日本近代化的经济实践和西方现代管理方法对《论语》加以积极改造和创造性的转换,使得儒家伦理能运用于工商业发展,构建了强调团体主义的东亚集团主义,内部推崇“孝悌”而外部主张“道义”的伦理哲学和人际关系的二重结构成为东亚集团主义精神的社会基础。儒家伦理在资本主义浪潮中焕然新生,并产生了东亚独特的儒教资本主义。
自明治维新起,日本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经济高速发展,跻身世界强国之列。这一切的变化不仅是由于政治制度的改革和西方文明的引进,更是由于儒家伦理与资本主义经济建设的结合。涩泽荣一作为“日本资本主义之父”,开日本资本主义之先河,他率先以西方的资本主义经济原则建立起一批企业,而以重新诠释的儒家义利观来肯定商业活动的重要性,使日本的贱商思想得以减轻,商人地位逐渐升高,工商业者得到良好的教育,商业活动也能够广泛地开展。他以儒家伦理来规范商业活动,使得日本的经济得以有序、快速发展,其儒家经济伦理思想可以说影响甚巨,造就了一批以儒家文化安身立命的企业家如丰田纺织公司创始人丰田佐吉、日本经团联前任会长士光敏夫,可见“涩泽现象”具有普遍性。
儒家思想是源于中国的,在日本得以改造和运用,焕发出新的光芒,却在中国走向近代化的过程中被打压、践踏,不可不谓是一大憾事。中国如今正面临这样一个局面,人们远离了儒家文化后,又只吸收了西方利己主义的一方面,只追求财富而忽视道德,毫无儒家所提倡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社会责任感。涩泽荣一就针对当时中国人缺乏社会责任感的情况予以批评:“以全体国民来观察,就发现个人主义、利己主义相当发达,而且普遍缺乏国家观念,没有人真正关心国家,加以一国之中又无中流社会,全体国民又缺乏国家观念,中国现今最大的缺点应该在这里了。”[431]利己主义导致中国的经济正在因为自身道德的问题而进入了一个恶性循环。可见儒家伦理亟待回归,道德教育也需要在各个领域普及。涩泽荣一的儒家经济伦理可以经过扬弃而为我所用,将其改造成适用于中国当代社会环境的道德教育范本,必将革去利己主义之弊,从而创造中国经济的真正腾飞。
儒家思想是历久弥新的,尽管会因时代背景不同而有龃龉之处,但其所提倡的道德伦理仍是人类永远追求的不变的真理,部分僵化的思想经过扬弃后重现光彩,为新时代提供了改善现状的动力。不禁叹服于孔子的智慧,千年风霜未能减损其魅力。真理,永不褪色。
*沈清松,加拿大多倫多大學講座教授。
[①]沈清松:Michael Hart and Antonio Negri著,Empire,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0,478pages+xvii)一書書評,in《哲學與文化月刊》,第361期,臺北,2004年6月,第109-112頁。該文收入本書第五章前半,並加以評論和省思。
[②]利瑪竇,《交友論》,收入李之藻輯,《天學初函》(一),台北:學生書局,1972,頁212-213。
[③]同上,頁59。
[④]參見畢方濟著,〈睡答〉,收入《耶穌會羅馬檔案館明清天主教文獻》,台北:利氏學社,2002第六冊,頁414-415。
[⑤]傅泛際(Franciscus Furtado)、李之藻譯,《名理探》,北京公教大學輔仁社,1926。台北市:臺灣商務,民54。同樣故事亦見於艾儒略,《性學觕述》,收入《耶穌會羅馬檔案館明清天主教文獻》,第六冊,頁371。
[⑥]Monumenta paedagogica Societatis Jesu: quae primam Rationem studiorum anno 1586 editam, praecessere, ediderunt Caecilius Gomez Rodeles, Marianus Lecina, Fridericus Cervos, Vincentius Agusti, Aloisius Ortiz, e Societate Jesu presbyteri (Matriti: Typis Augustini Avrial, 1901)
[⑦]“In logica, et philosophia naturali et morali, et metaphysica doctrinam Aristotelis profiteri oportebit.”Monumenta paedagogica Societatis Jesu: quae primam Rationem studiorum anno 1586 editam, praecessere, ediderunt Caecilius Gomez Rodeles, Marianus Lecina, Fridericus Cervos, Vincentius Agusti, Aloisius Ortiz, e Societate Jesu presbyteri (Matriti: Typis Augustini Avrial, 1901), p.461.
[⑧]Pasquale M.D’Elia, S.J.,Galileo in China, Relation through the Roman College between Galileo and the Jesuit Scientist-Missionaries (1610-1640), translated by Rufus Suter and Mathew Sciascia,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0), pp.17-59
[⑨]艾儒略,《西學凡》,收入李之藻輯,《天學初函》,台北:學生書局,1965,頁59。
[⑩]不過在以下各卷卷首,又署名「西海後學艾儒略著」。按,艾儒略,字思及,所以是同一人。但「譯著」與「著」之間,並不完全一致。其實該書有譯、有著、有改寫、有編著。
[11]按,從《性學觕述》第六卷開始,已經開始論述靈性。
[12]畢方濟口授,徐光啟達辭,《靈言蠡勺》,收入《天學初函》(二),台北:學生書局,頁1134。
[13]聖伯爾納德乃中世紀的一個修道院的密契論者,他有首聖歌也被翻譯為〈聖夢歌〉。見《耶穌會羅馬檔案館明清天主教文獻》,第六冊,台北:台北利氏學社,2002,頁435-464。
[14]《靈言蠡勺》,天學初函(二),頁1169。
[15]前揭書,頁12-13。
[16]Gernet, J.,Chine et christianisme, Action et réaction, Paris: Gallimard, 1982, p. 94
[17]德沛,《實踐錄》,《法國國家圖書館明清天主教文獻》第十二冊,(台北;利氏學社,2009),頁95-96。
[18]同上,頁96-98。
[19]同上,頁98。
[20]同上,頁99。
[21]同上,頁99。
[22]同上,頁103。
[23]德沛,《實踐錄》,頁105。
[24]原出于《詩·周頌·清廟》:「濟濟多士,秉文之德;對越在天,駿奔走在廟。」然而,在本文中指的是由內在的道德而超越至天之意。
[25]基於兩個理由,我不贊成黃一農在《兩頭蛇》一書中將這些早期天主教徒儒者稱為「兩頭蛇」:其一,正如我以滿族親王德沛和漢人學者夏大常為例說明的,他們已經初步程度在形而上思想、人性論、實踐論上作了某種雛形的中西融合,不再是「兩頭蛇」;其二是,他們底子裡還是中國儒者的精神,立基於對中國經典的詮釋來講中國文化。另外,我不知道黃一農在如此命名時,有沒有想到中國有關見到兩頭蛇將會不幸的傳說,或有思及孫叔敖打兩頭蛇的故事。如果有,則如此的命名,在意向上值得商榷。
[26]同上,頁88。
[27]同上,頁89。
[28]同上,頁82。
[29]同上,頁91。
[30]同上,頁91。
[31]同上,頁92。
[32]同上,頁92-93。
*Hu Yeping, Council for Research in Values and Philosophy, Catholic University of America.
[33]Matteo Ricci,On Friendship: One Hundred Maxims for a Chinese Prince, translated by Timothy Billings(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9), p. 87.
[34]Tang Yijie,Confucianism, Buddhism, Daoism, Christianity and Chinese Culture(Washington, D.C.: The Council for Research in Values and Philosophy, 1991), chap. 9, pp. 115-125.
[35]Tang Yijie,Confucianism, Buddhism, Daoism, Christianity and Chinese Culture, p. 149.
[36]Joseph Sebes, “A ‘Bridge’ between East and West: Father Metteo Ricci, S.J. His Times, His Life, and His Method of Cultural Accommodation,”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Chinese-Western Cultural Interchange in Commemoration of the 400th Anniversary of the Arrival of Matteo Ricci, S.J. in China, September 11-16, 1983 (Taipei, Taiwan: Fu Jen Catholic University Press, 1983), p. 590.
[37]Ricci,On Friendship, Introduction by Timothy Billings, pp. 1-2.
[38]Fonti Ricciane,Storia dell’Introduzione del Cristianesimo in Cina, introduction, p. XCIII. (Quotation from Fontana,Matteo Ricci, p. 27.)
[39]Fontana,Matteo Ricci, p. xiv.
[40]Antonio Sisto Rosso,Apostolic Legations to China of the Eighteenth Century(South Pasadena, P.D. and
Ione Perkins, 1948), p. 224.
[41]Malcolm Hay,Failure in the Far East(Wetteren, Belgium: de Meester Bros., 1956), p. 96.
[42]Sebes, “A ‘Bridge’ between East and West”, p. 591.
[43]Matteo Ricci,Opere storiche del P. Matteo Ricci, ed. Pietro Tacchi-Venturi, 2 vols. (Macerata: Premiato
Stabilimento Tipografico, Filippo Giorgetti, 1911, 1913), 2:248; quoted from Ricci, On Friendship, p. 3.
[44]R. Po-Chia Hsia,A Jesuit in the Forbidden City: Matteo Ricci1551-1610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p. 93.
[45]Metteo Ricci,True Meaning of the Lord of Heaven (T’ien-chu Shih-i), translated, with Introduction and
Notes by Douglas Lancashire and Peter Hu Kuo-chen, S.J.; a Chinese-English Edition edited by Edward J.
Malatesta, S.J. (St. Louis: The Institute of Jesuit Sources, 1985), p. 14.
[46]Ricci,True Meaning of the Lord of Heaven (T’ien-chu Shih-i), p. 13.
[47]Ricci,True Meaning of the Lord of Heaven (T’ien-chu Shih-i), p. 14.
[48]Tang Yijie,Confucianism, Buddhism, Daoism, Christianity and Chinese Culture, p. 150.
[49]Matteo Ricci,China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The Journals of Matteo Ricci1583-1610, Translated from
the Latin by Louis J. Gallagher, SJ, with a Foreword by Richard J. Cushing, D.D., LL.D.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53), p. 93.
[50]Ricci,China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p. 94.
[51]Ricci,China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p. 30.
[52]Ricci,China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p. 30.
[53]Ricci,China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p. 96.
[54]Ricci, China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p. 97.
[55]Ricci, China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p. 96.
[56]Ricci, China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p. 94.
[57]Ricci,True Meaning of the Lord of Heaven, p. 121.
[58]Ricci,True Meaning of the Lord of Heaven, p. 125.
[59]Ricci,China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p. 82.
[60]Sangkeun Kim,Strange Name of God(New York: Peter Lang, 2004), p. 163.
[61]Ricci,True Meaning of the Lord of Heaven, p. 61.
[62]Ricci,True Meaning of the Lord of Heaven, pp. 185, 189.
[63]Ricci,True Meaning of the Lord of Heaven, pp. 50, 203.
[64]Tang Yijie,Confucianism, Buddhism, Daoism, Christianity and Chinese Culture, p. 151.
[65]Ricci,True Meaning of the Lord of Heaven, pp. 297, 303.
[66]Ricci,True Meaning of the Lord of Heaven, p. 303.
[67]Ricci,True Meaning of the Lord of Heaven, p. 313.
[68]Ricci,True Meaning of the Lord of Heaven, p. 317.
[69]Ricci,True Meaning of the Lord of Heaven, p. 209.
[70]Ricci,China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p. 98.
[71]Ricci,True Meaning of the Lord of Heaven, p. 313.
[72]Sebes, “A ‘Bridge’ between East and West”, p. 591.
[73]Joseph Needham,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1954) Vol. I. pp. 148-149.
[74]Fontana,Matteo Ricci: A Jesuit in the Ming Court, p. 57.
[75]Ricci,China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p. 389.
[76]Hsia,A Jesuit in the Forbidden City, p. 123.
[77]James C.P. Fan, “The Reverend Matteo Ricci’s Contributions to the Modernization of China,”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the 400th Anniversary of the Arrival of Matteo Ricci, pp. 231-254.
[78]Pope John Paul II, “Pope’s Address on the Work of Father Ricci in China,”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the 400th Anniversary of the Arrival of Matteo Ricci, p. 6.
[79]Yang Young-ching,China’s Religious Heritage(New York and Nashville: Abingdon Cokesbury Press, 1948), p. 20.
[80]Pope John Paul II, “Pope’s Address on the Work of Father Ricci in China,”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the 400th Anniversary of the Arrival of Matteo Ricci, pp. 5-6.
[81]Hans-Georg Gadamer, Truth and Method (New York: The Seabury Press, 1975), p. 256.
*桑靖宇,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教授;程悦,武汉大学珞珈学院传媒艺术学院。
[82]朱维铮:《利玛窦中文著译集》,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8页。
[83]朱维铮:《利玛窦中文著译集》,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8页。
[84]张晓林在《利玛窦与天主学统》(学林出版社2005年)一书的第168-170页以及第180页对此有较细致的分析。
[85]朱维铮:《利玛窦中文著译集》,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8页。
[86]朱维铮:《利玛窦中文著译集》,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9页。
[87]转引自谢和耐:《中国文化与基督教的首次碰撞》,辽宁出版社1989年,第13页。
[88]Leibniz,Writings on China. Translated by Daniel J.Cook,Henry Rosemont., Chicago, 1994. p.84.
[89]Leibniz,Writings on China. Translated by Daniel J.Cook,Henry Rosemont., Chicago, 1994. p.90.
[90]Leibniz,Writings on China. Translated by Daniel J.Cook,Henry Rosemont., Chicago, 1994. p.93.
[91]Ribas, Albert, Leibniz' "Discourse on the Natural Theology of the Chinese" and the Leibniz-Clarke Controversy.Philosophy East and West, Vol. 53, No. 1. 2003.p73.
[92]Leibniz,Writings on China. Translated by Daniel J.Cook,Henry Rosemont., Chicago, 1994. p.87.
[93]Leibniz,Writings on China. Translated by Daniel J.Cook,Henry Rosemont., Chicago, 1994. p.88.
[94]莱布尼茨:《中国近事——为了照亮我们这个时代》,第1页,杨谦立、杨保均译,郑州:大象出版社,2005。
[95]莱布尼茨:《中国近事——为了照亮我们这个时代》,第6页,杨谦立、杨保均译,郑州:大象出版社,2005。
[96]Joseph Needham,Within Four Seas, Toronto,1979, P. 26-27
[97]Joseph Needham,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 V.2, Cambridge,1956, P. 286-287
[98]Joseph Needham,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 V.2, Cambridge,1956, P. 480
[99]Joseph Needham,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 V.2, Cambridge,1956, P. 475
[100]Joseph Needham,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 V.2, Cambridge,1956, P. 478
[101]Joseph Needham,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 V.2, Cambridge,1956, P. 481
[102]方永,武汉大学哲学学院副教授。本文获得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14JZD034)资助。
[103][法]杜赫德[编]:《耶稣会中国书简集》,[中]郑德弟、吕一民、沈坚译,郑州:大象出版社,2001年1月第一版第1次印刷,第一卷,“中文版序”之第3-4页。
[104]利玛窦:《利玛窦中文著译集》,朱维铮主编(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12月第一版第1次印刷),“导言”之第6-9页的“怎样‘劝化中国’?”
[105]利玛窦:《利玛窦中文著译集》,朱维铮主编,“导言”之第9页。
[106]德礼贤:《利玛窦资料》,第一卷,第180页,注5。转引自宋黎明:《神父的新装——利玛窦在中国[1582-1610]》(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5月第一版第1次印刷),第18页。
[107]宋黎明:《神父的新装——利玛窦在中国[1582-1610]》,自序之第3页。
[108]宋黎明:《神父的新装——利玛窦在中国[1582-1610]》,第122-123页
[109]宋黎明:《神父的新装——利玛窦在中国[1582-1610]》,自序之第3页。
[110]李零:《中国方术续考》,北京:东方出版社,2000年,第17页。
[111]李零:《中国方术续考》,北京:东方出版社,2000年,第18页。
[112]孙尚扬:《利玛窦与徐光启》,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09年11月北京第1版第1次钝刷,第36页。
[113][美]史景迁:《利玛窦的记忆之宫:当西方遇到东方》,陈恒、梅义征译(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05年7月第一版第1次印刷),第22-23页。
[114]孙尚扬:《利玛窦与徐光启》,第119页。
[115]利玛窦:《利玛窦全集》第二册,刘后余、王玉川译(台北县:辅仁大学出版社,1983年10月第一版),第458页。
[116]孙尚扬:《利玛窦与徐光启》,第38页
[117]利玛窦:《利玛窦中文著译集》,朱维铮主编,“导言”之第12-18页的“渗入王学开拓的空间”
[118]宋黎明:《神父的新装——利玛窦在中国[1582-1610]》,第294页。
[119]宋黎明:《神父的新装——利玛窦在中国[1582-1610]》,第294页。
[120]《梵二文献》教会对非基督宗教态度宣言:绪言。2005年版,第469页。
[121]利玛窦著,芸娸译,《天主实义》,2007年版,第154页。
[122]同上,第157页。
[123]同上,第40页。
[124]利玛窦著,郑安德编:《天主实义》,2000年版,序十。
*严震泽,韩国人,南京大学哲学系中国哲学专业博士研究生。
[125]朝鲜中期东人派别成立的朋党中的4色党派之一。
[126]Michele Rugger(1543-1607 ):.他虽然和同僚一起在那年1月去了兆京,但因没有取得居住许可而回国。
[127]关于他宗教的宣言: 教会为了和其他宗教的信徒一起以智慧和爱对话,相互协作,以此为基督教信仰和生活的证据,也肯定其他宗教中发现的精神上乃至伦理上,社会上乃至文化上的价值,并让所有子女守护和发展这些价值。
[128]Karl Rahner(1904- 1984 ): He was a German Jesuit who made a profound contribution to Catholic theology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His role was a theological expert at the Second Vatican Council.
[129]伊格纳西奥(Ignatius de Loyola,1491-1556):这样的灵性特征不仅给利玛窦,也给以后的耶稣会传教士造成了影响。他们为了在中国古代经典中发现上帝的痕迹而努力,所谓“万物中皆可发现上帝(Finding God in all things)”就是Ignatius de Loyola灵性中的基本。
参看,Ignatius de Loyola:《灵身训练》,정제천(译), .Ignatius de Loyola研究所2005年版,第.230-237页。
[130]沙勿略和范礼安:Alessandro Valignan(1539-1606),1566年加入耶稣会,在罗马学院学习哲学及神学,1570年任命为神父后成为修道长。在印度,日本,澳门等地活动,不仅有哲学和神学知识,在数学和物理学领域也有很深的造诣。他对异邦人及异邦文化不抱有偏见,主张要出现有传教地出生的圣职者。他是继方济·沙勿略之后坚持适应主义传教方式的传教士,他觉得进行传教活动,语言十分重要,他开放的传教态度是利玛窦可以活动的背景条件。
[131]Johann Hoffmann-Herreros,Matteo Ricci, Den Chinesen ein Chines sein -ein Missionar sucht neue Wege,Mainz 1990,p.66.
[132]对于利玛窦的这些批判在他死后的耶稣会内部也是存在的,像是Niccolo Longobardi认为利玛窦对中国文化所持的态度太过于开放,另一方面主张“索隐主义者(figurist)”的耶稣会成员则认为利玛窦不够开放。
[133]他的传教方法也表现了伊格洛的灵性。
[134]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当时利玛窦的神学体系和现在是不同的,他批判当时的佛道教以及性理学的价值观是无神论,以这一事实为基础而无视他的成就是不合理的。
[135]유흥렬:《韩国天主教会史,上》,CATOLIC出版社1975版,第.13-80页。
[136]星湖学派,.星湖学派分成了两个流派。一个是老师(星湖 李瀷, 1681~1763년)继承了对天主教教理持批判态度的传统儒教立场,并对西学采取全盘否定态度的“攻西派”,另一个则是老师继承了开放性的实学精神,接受科学技术和伦理解释,并发展其的“信西派”。李瀷初期的弟子有愼後聃,安鼎福等人,他们不关心西方科学,对天主教教理持批判态度,形成了所谓的“攻西派”,李瀷后期的弟子和其继承者是權哲身,李家煥,李檗,丁若鏞等人,他们对西方的科学技术态度积极,并由此发展了对天主教的信仰,形成了“信西派”。
实学:从17世纪中旬到19世纪初在李朝后期出现的新思想,目的是为了解决当时的社会问题,批评性理学的非现实性和教条主义,同时强调经世致用、实事求是、利用厚生等学习态度。
参看,최상천:,“正祖时代天主教会运动研究”,韩国教会史研究所编,《崔锡祐神父花甲纪念韩国教会史论丛》,韩国教会史研究所1982版,第9-15页。
[137]Charles Dallet, Historie de l'Eglise de Coree(한국천주교회사), 안응렬,최석우(译), 分道出版社1979年版,第303-304页。
[138]Alexander de Gouvea,“Extractum Epistolae Excellentissimi, Admodumque Reverendi Episcopi Penkinensis, ad Mustrissimum Episcopurn Caradrensem”,天主教大学教会史研究会编,教会史研究志第3辑,天主教大学出版社1970版,第.127页.
[139]Charles Dallet, Historie de l'Eglise de Coree(한국천주교회사), 안응렬,최석우(译), 分道出版社1979年版,第99页。
[140]정조(正祖, 1752 ~ 1800):朝鲜的第22代王,正祖经过艰难的过程才登上皇位,并通过各种各样的改革政策和荡平策推进了国家大一统。
[141]辛酉迫害:也称为辛酉邪狱。从中国传来的天主教打破了当时性理学支配原理的界限,在一部分追求新原理的思想家,以及想要反叛腐败无力的封建制度的民众中传播开来,18世纪末期宗教势力得到了很大的扩张,特别是1794年清国神父周文谟来到朝鲜,以及正祖的扩大天主教的政策都成宗教势力扩大的重要契机。因此正祖死后,就进入了所谓的专制政权时期,同时也正式开始了对天主教徒的压迫。1801年正月,年幼的纯祖登上皇位,辅政的贞纯大妃下了禁止·根除邪教及西教的镇压令。因此李承熏,李家焕,丁若镛等天主教徒和进步思想家们都被处刑,流放,以周文谟为首的约100名教众被处刑,约400名被处刑或流放。辛酉迫害既是统治势力对快速扩张的天主教势力感到威胁的宗教压迫,也是一个借口,以实现老论等政权的保守势力对当时政治上的反对势力——南人为首的进步思想家及其政治势力的打压,是权利斗争中的一环。
[142]焚主废祭:为了遵守祖先祭祀禁令,烧毁祖先牌位和停止对祖先的祭祀。
[143]Charles Dallet, Historie de l'Eglise de Coree(한국천주교회사), 안응렬,최석우(译), 分道出版社1979年版,第575页。
[144]Acta Apostolicae Sedis Vol. 28, 1936, pp.406-409.
[145]Acta Apostolicae Sedis Vol. 32.1940 , pp.24-26.
[146]在尸体或坟墓,死者的相片或只记有名字的牌位前行礼,烧香,陈列饮食等行为都是允许的,禁止的事项则包括读祝词,阅门,在葬礼时皋复(고복:重新把死者的灵魂呼唤回来的仪式。),使者饭(사자밥:为了不让勾魂使者把死者的灵魂带走,在葬礼上放上饭和鞋子。),以及饭含(반함:在死者的嘴中放上米,贝壳,珠子等物的仪式。)等行动。牌位上没有“神位”及“神主”的字样,只是单纯写名字来供奉的话是允许的。
[147]Rita Haub und Paul Oberholzer,Matteo Ricci und der Kaiser von China,Wurzburg 2010,pp.8-10 . Papst Benedikt XVI, Botschaft des HI. Vaters Benedikt XVI. An Seine Exzellenz Claudio Giulidori, Bischof von Macerata zum 400. Todestag von P.Matteo Ricci.
[148]感觉到教皇厅对东方文化视角的改变以及传教政策的变动。
[149]Shim sang-tai Monsignor:他批判,韩国教会的创立者们“因为努力在朝鲜建立教会而面临死亡”,但是因为无法高度认同在教会的欧洲文化氛围中形成的教理精神,或者是不遵守充满着欧洲优越主义气息的祖上祭祀禁令,就被认为污蔑为“叛教”,并将其从施福施圣的名单中去除。 一方面Sim Monsignor强调教皇约翰保罗2世的大喜年教书《第3千年》中的“记忆净化”,并且在2000年3月12日的圣彼得大圣战中与参会仪式一起举行的庄严弥撒上请求饶恕十字军战争,教会分裂,宗教审判,屠杀犹太人等错误,但是这份声明中并不包含着给东亚传教活动带来巨大打击的“祖上祭祀禁令”。 他要求“教皇厅及西欧教会相关机关要承认下达祖上祭祀禁令的错误,并恢复教会创立者们的权利”,并且提议为了迎来历史的大转换期,应脱离一般教会将所有权力都集中于教皇厅的中世纪惯行,而将权力转交给地方教会。
<Catolic news지금여기 http://www.catholicnews.co.kr>
[150]금장태:《关于东西交流与近代韩国思想研究》,未出版博士学位论文,成均馆大学1978年版,第.42-45页.。
[151]최기복:“朝鲜的天主教废祭毁祖及儒教祭祀的根本意义”韩国教会史研究所编,《韩国教会史论丛》,韩国教会史研究所1982年版,第.87-89页。
[152]孝经,开宗明义章: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能毁伤。
[153]论语,为政下7,8:养口体之孝,犬马之养。
[154]孝经,开宗明义章: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
[155]三浦国雄(1941—),日本大阪市立大学文学部名誉教授,日本道教学会前会长,主要从事中国思想史及东亚比较文化论的研究。
*本文原题名为《止観と坐忘と居敬——三教の身心技法》,发表于日本大阪市立大学文学部《人文研究》第44卷第5分册(1992年),187-223页。
[156]《佛教学辞典》,法藏馆,昭和51年第10刷版。又参见,高振农:《止与观》(《中国哲学史主要范畴概念简释》,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本文的校正刷出来以后才知道了以下二篇论文的存在。但很遗憾未能将其吸收进本文中。楠山先生的文章是1975年的工作,只能为笔者的无能感到羞耻。楠山春树:《漢語としての止観》(《道家思想と道教》所收,平河出版社,1992年)。冉云华:《论<摩诃止观>中“止观”概念的中国化》(《中国文化》第三期所收,1990年,北京)。
[157]安藤俊雄:《天台学》,平乐寺书店,1973年第3刷,177-179页。
[158]具体名称为《略明开朦初学坐禅止观要门》。以下简称为《天台小止观》或《小止观》。引用依据,关口真大:《天台小止観》,岩波文库,昭和49年第1刷。又参考,同氏:《天台小止観の研究》(山喜房佛書林,昭和49年第7版)所収的《定本稿》。还参考了同氏:《現代語訳天台小止観》(大东出版社,昭和62年第3版)的读解。
[159]关口真大:《天台止観の研究》,岩波书店,1985年第2刷,300页。
[160]《摩诃止观》卷三上也说:“止即是断,断通解脱,观即是智,智通般若”(大正46—22c)。以下引用《摩诃止观》依据《大正藏》第46册。
[161]《摩诃止观》卷九上也说:“定者,只一心澄静,若缚着不动,是太过,若驰散万境,此不及”(大正119页c)。
[162]《摩诃止观》卷九上也有“观禅定境”一章(大正117页a以下)。
[163]《摩诃止观》卷五上云:“夫心地难安,违苦顺乐,今随其所愿,遂而安之,譬如养生,或饮或食,适身立命,养法亦尔,以止为饮,以观为食,药法亦两,或丸或散,以除冷热,治无明病,以止为丸,以观为散……慧定偏者,皆不见佛性,八番调和,贵在得意,一种禅师,不许作观,唯专用止……又一禅师,不许作止,专在于观……两师各从一门而入,以己益教他,学者则不见意,一向服乳,浆犹难得,况复醍醐”(大正59页a)。
[164]关于这个问题,本文第四章中还会再提出讨论一下。
[165]这种止观的解释,借助于津村乔氏指教的地方很多。他把止作为“认同意识”,把观作为“观察意识”来把握(《天台止观讲义》,私家版,1988年)。
[166]关于司马承祯的传记及其《坐忘论》的先行研究,有陈国符:《司马承祯传》(《道藏源流考》所收,中华民国64年,台湾古亭书屋影印版),神塚淑子:《司马承禎<坐忘論>について》(《東洋文化》62号),Livia Knaul:"SEVEN STEPS TO THE TAO:Ssu-ma Ch'eng-chen's Tso-wang-lun," Monumenta Serica 37 (1986)等。
[167]关于《庄子》的坐忘及其后来的展开,参考,市川安司:《荘子書に見える心斎と坐忘について》(《朱子哲学論考》所收,汲古书院,昭和60年),中野达:《郭象における坐忘》(《東方宗教》75号),藤吉慈海《坐襌と坐忘について》(《禅净双修の展開》所收,春秋社,昭和49年)等。中野的论文对我很有益处。关于司马承祯《坐忘论》以后的展开,蒙文通《坐忘论考》(《蒙文通文集》第一卷所收,巴蜀书社,1987年)是必读的文献。
[168]上述藤吉的论文,将“佛教的坐禅与庄子及道教,特别是司马承祯的坐忘思想”之间的不同点概括如下:“其根本的差异是,坐禅从忘出发强调觉,依据其实修,自觉了々常知之觉体。坐忘则从觉出发强调忘,忘掉自他•内外•是非•善恶等的对立或者自己自身及知,以此作为其本质”(63页。着重点为引者所加)。如后面所述,庄子与司马承祯的坐忘虽不可同等看待。但如果限定于庄子的坐忘的话,我想标着重号的部分是正确的。
[169]关于“守一”及其展开,参考,福井康顺:《守一考》(《福井康顺著作集》第二卷所收,法藏馆,昭和62年),吉冈义丰:《仏教の禅法と道教の守一》(《智山学报》十二、十三),饶宗颐:《守一》(《老子想尔注校笺》笺証5,香港Tong nam Printers&Publishers,1956)等。
[170]“一散形为气,聚形为太上老君,常治昆仑……世间常伪伎指五藏以名一,瞑目思想,欲从求福,非也”(上列饶宗颐校笺本13页)。
[171]关于此点上述饶宗颐《校笺》也认为守一给予佛教的禅定以影响。(“汉魏所译佛经,亦每见‘守一’语。如《法句经》:‘守一以正身’。是守一为东汉道家所恒言,故取以译释氏之‘禅定’,亦格义之一例。汤锡予疑太平经之‘守一’,源于印度之禅观,按不如以格义说之,较妥”(上列饶宗颐《校笺》65页)。
[172]柳田圣山:《初期の禅史Ⅰ》,筑摩书房,昭和46年,234页,245頁,参见注(14)所引吉冈的论文。
[173]“守一”一语也见于《摩诃止观》中。如“汝勿外寻,但内守一”(卷五上,57页c)。
[174]本文中姑且以《云笈七签》卷94所收的文本(《全唐文》沿袭此)为底本。这个文本正如众所周知的,缺少了道藏本中有的《坐忘枢翼》。
[175]以下依据道藏本。得道篇的末尾部分,云笈本与道藏本完全不同。
[176]“司马承祯大胆地援引了佛家的禅观、定慧、渐悟、明心见性的学说,用以解决修炼过程中炼神入静问题”(李远国:《道教气功养生学》,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8年,262页)。
[177]《剑南诗稿》卷九,“道室”(1985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刊,钱仲联校注本,701页)。陆游提到司马承祯的地方见于《跋坐忘论》(《渭南文集》卷26)、《跋天隐子》(同上)、《跋司马子微饵松菊法》(同上)等。依据文集卷28所收《跋坐忘论》(与卷26所收是不同的文章),司马承祯之前有一个叫赵坚的道士似乎也有坐忘论。关于赵坚(赵志坚),注(12)引蒙文通《坐忘论考》中有考证。
[178]《剑南诗稿》卷41,《观方外书》(校注本2584页)。
[179]“道释二氏,本相矛盾,而子微之学,乃全本于释氏,大抵以戒定慧为宗,观七篇之序可见……善巧方便,唯能人定,发慧迟速,则不由人,勿于定中急急求慧,求则伤定,伤定则无慧,定而慧自生,此真慧也,此言与智者所论止观实相表里,子微中年隐天台玉霄峰,盖智者所居,疑其源流有自”(《说郛》卷八所收《玉涧杂书》)。
[180]《张右史文集》卷五一,《送张坚道人归固始山中序》。
[181]关于唐代道教中的“观”,目前参考,任继愈主编:《中国道教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六章第三节“观行与坐忘之道”。
[182]这篇论文附载了云笈七签本中没有而仅见于道藏本中的文字。关于此与《洞玄灵宝定观经》(《云笈七签》卷十七)基本文字相同等相关情况,可参考上述神塚论文。
[183]本条也收录在《近思录》存养篇中。又以下二程的引用,使用1981年,中华书局刊的点校本《二程集》。
[184]点校本按“……可谓良苦。人都来多少血气?若此,则几何而不摧残以尽也”断句标点,对于“都来”二字,校注云:“‘都’字疑当作‘那’,形似而误”。
[185]又参考第二下,53页。还有关于北宋士大夫“思虑纷扰”的问题,参考市来津由彦《程伊川実践論の論理形成》(《集刊東洋学》三八号)。
[186]“盖为前日思虑纷扰,今要虚静,故以为有助,前日思虑纷扰,又非义理,又非事故,如是则只是狂妄人耳,惩此以为病,故要得虚静,其极,欲得如槁木死灰,又却不是,盖人活动也,又安得为槁木死灰,既活,即须有动作,须有思虑,必欲为槁木死灰,除是死也”(《程氏遗书》第二上,26页)。
[187]此外《程氏粹言》第二,1257页中有基本相同的文字。
[188]成玄英疏云:“精神驰骛,可谓形坐而心驰者也”。《摩诃止观》中屡次见到的“驰散”也是那种意思吧。如“若身端心摄,气息调和,觉此心路泯然澄静,怗怗安隐,蹑蹑而入,其心在缘而不驰散者,此名粗住”(大正46—118页b)。
[189]下面程子的话也是相同的道理。“或曰:惟闭目静坐,为可以养心。子曰:岂其然乎,有心于息虑,则思虑不可息矣”(《程氏粹言》第二,1255页)。
[190]朱子将此条作为程明道之语(《朱子语类》卷96,中文出版社本3908页)。
[191]又参考下面的话。“张天祺昔常言,自约数年,自上著床,便不得思量事,不思量事后,须强把佗这心来制缚,亦须寄寓在一个形象,皆非自然,君实自谓,吾得术矣,只管念个中字,此则又为中系缚,且中字亦何形象,若愚夫不思虑,冥然无知,此又过与不及之分也”(《程氏遗书》第二下,53页)。
[192]这里所说的“自然”,当然不是老庄那样的“无为自然”。参考 注(36)所引程子语中的“自然”。
[193]国士馆大学附属图书馆编:《楠本正继先生中国哲学研究》,昭和53年刊,253页。
[194]比如看以下的话吧。“又问:敬莫是静否。曰:才说静,便入于释氏之说也,不用静字,只用敬字,才说着静字,便是忘也。孟子曰: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长也,必有事焉,便是心勿忘,勿正,便是勿助长”(《程氏遗书》第十八、189页)。还有这里所说的“才说着静字,便是忘也”的“忘”不是坐忘的“忘”,正如接着引用的所示是孟子说的“忘”(即楠本氏说的“功夫的放弃”)。这里,对于完全依赖“静”而忽视工夫的倾向予以了警惕。
[195]“释氏多言定,圣人便言止”(《程氏遗书》第十八,201页)。“或谓:佛氏所谓定,岂圣人所谓止乎。子曰:定则忘物而无所为,止则物自付物,各得其所,而我无与也”(《程氏粹言》第一,论道,1172页)。
[196]《程氏文集》第二(明道),《答橫渠张子厚先生书》的通称。
[197]依据姚廷杰《朱子钩玄》(《国学论衡》第三期)。
[198]“龟山说:反身而诚,却大段好,须是反身,乃见得道理分明,如孝如弟,须见得孝弟我元有在这里,若能反身,争多少事,他又却说万物皆备于我,不须外面求,此却错了”(《朱子语类》卷十八,671页)。
[199]“夫泥垣真法,入乃多途,论其急要,不出止观二法,所以然者,止乃伏结之初门,观亦断惑之正要……当知此之二法,如车之二轮,鸟之二翼,若偏修习,即墮邪倒”(序,岩波文库本23-24页)。
[200]关口真大《天台止観の研究》(岩波书店,1985年第2刷)中也说:“所谓非行非坐三昧,例如基于首楞严三昧经或请观音经而样式稍稍复杂的修行之法也被此摄入此中,实际上不但是那种规定期限或道场或作法的特定修行之法,而且贯通于日常生活的行住坐卧一切之中,作务辛劳中也好公私匆忙中也好都是应该修行的”(20页)。
[201]参考朱子下面的话。“敬中须有体察功夫,方能行著习察,不然,兀然持敬,又无进歩处也”(《文集》卷42,答石子重第五书)。
[202]“司马承祯说:‘但心不著物,又得不动,此是真定正基’(收心)。……司马承祯的这种‘主静’方法,与宋代理学唯心主义者所讲的‘無欲故静’的‘主静’功夫(周敦颐)、‘惩忿窒欲’的‘居敬’功夫(朱熹)等有相似之处,因而为宋明理学唯心主义所吸取”(北京大学哲学系中国哲学史教研室编《中国哲学史》上册,346页,中华书局,1980年)。
[203]卷七下,大正46—101c。
[204]卷九上,大正46—119c。
[205]关于穷理中包藏P(沉静意识)这一点,笔者在正文中虽未做任何说明,但将程伊川等所说“豁然贯通”放在心上。道学中所说的穷理与欧洲的认识论不同,其最终成就的是进行穷理的主体意识之改变——用佛教的来说即觉悟的体验。那么预想着与作为一者的浑然太极之冥合。这种心的状态在某种程度上与“止”不是有相通之处吗。上述就是笔者的假说。
[206]卷八上,大正46—108a。
[207]治病患第九,岩波文库160页。
[208]“……星随日九变,与时消息,规矩三光,四灵在旁,存想丹田,大一紫房,道成身化,蝉蜕渡世”(依据《全后汉文》卷62)。
[209]“善治气者,由禹之治水也,若夫导引蓄气,历藏内视,过则失中,可以治疾,皆非养性之圣术也”。五脏内视的最早的例子是西汉末年谷永的上奏文中的话,还有作为“化色五仓(=脏)之术”(《汉书》卷25,郊祀志下)的看法。(前田繁树:《<老子中経>覚書》,坂出祥伸编《中国古代養生思想の総合的研究》所收,平河出版社,1988年)。
[210]如《素问》宣明五气篇中配比如下:心——神、肺——魄、肝——魂、脾——意、肾——志。
[211]“既屏外缘,会须守五神(肝心脾肺肾)从四正(言行坐立)”(卷27,道林养性第二)。
[212]参见拙稿《気の復権——気功と道教》(《伊藤漱平教授退官紀念中国学論集》所收,汲古书院,1986年)217页以下。
[213]参见前引拙稿219页。
[214]《摩诃止观》卷四下,“若能调凡夫三事,变为圣人三法,色为发戒之由,息为入定之门,心为生慧之因”(大正46—47b)。
[215]《摩诃止观》卷七上,“右数息心定,毛孔见佛,住首楞严,得不退转,是为数息开解脱门”(大正46—93a)。
[216]参见,坂出祥伸:《长生术》(《道教Ⅰ》所收,平河出版社,1983年)269页以下,注(57)引拙稿225页。
[217]参见,赖富本宏:《密教の身体マンダラ観》(注(54)引坂出编著所收)710页。
[218]“次有师言,若能善用观想,运作十二种息,能治众患,一上息、二下息、三满息、四燋息、五增长息、六灭坏息、七暖息、八冷息、儿冲息、十持息、十一和息、十二补息,此十二息,皆从观想心生,今略明十二息对治之相,上息治沈重……”(岩波文库本166-168页)。关于这十二息的形成,据安藤俊雄氏推测,是智顗在大苏山的修业时代,有受安世高译《修行道地经》五种成败章等激发而创造出来的可能性(《治病法としての天台止観——智顗の医学思想序説》,《大谷大学研究年報》23号,49页以下)。
[219]关于止观全体的治病法,参见前注所引安藤俊雄氏的大作。只是安藤的论文对于道教一系养生法给与智顗的影响是否定的,与笔者的见解不同。此外有山野俊郎《摩訶止観•病患境の研究》(大谷大学大学院《研究紀要》第一号),同《天台智顗の医学思想序説》(真宗総合研究所《研究所紀要》第三号),但其内容没有超出安藤的论文。
[220]见于玉城康四郎《入出息念定の根本問題》(《伊藤•田中両教授颂徳記念仏教学論文集》,高野山大学佛教学研究室,昭和五四年)。
[221]见于井上以智为《天台山に於ける道教と仏教》(《桑原博士還曆記念東洋史論叢》,弘文堂,昭和六年)。
[222]如曾国藩年青时为了实行居敬而静坐,至老年则为了治愈眼病而从事于静坐(本田济:《曾国藩の哲学》,《東洋思想研究》所收,創文社,昭和62年,623、633页)。
[223]参见拙稿《朱子と呼吸》(金谷治编:《中国における人間性の探究》所收,创文社,1983年)。
[224]“胎息之说,谓之愈疾则可,谓之道,则与圣人之学不干事,圣人未尝说着,若言神住則气住,则是浮屠入定之法,虽谓养气,犹是第二节事,亦须以心为主”(《程氏遗书》第二下,49页)。“谢子曰:吾尝习忘以养生。明道曰:施之养生则可,于道则有害,习忘可以养生者,以其不留情也,学道则异于是,必有事焉而勿正,何谓乎……忘则渉乎去念,助则近于留情,故圣人心如鉴,孟子所以异于释氏,此也”(《程氏外书》第十二,426页)。
[补记]本文是在1991年9月23日コレージュ•ド•フランス主办的第六次日法コロック(在巴黎)上的发表草稿基础上修改而成的。感谢当日以シッベール教授为首提供有益建议的各位参加者。
*吴根友,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教授。
[225]雅斯贝尔斯著,魏楚雄俞新天译:《历史的起源与目标》,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33页。
[226]同上,第62页。
[227]同上,第8页。
[228]同上,第8页。
[229]同上,第62页。
[230]同上,第62页。
[231]同上,第63页。
[232]同上,第63页。
[233]同上,第63—64页。
[234]同上,第64—65页。
[235]同上,第66页。
[236]同上,第66—67页。
[237]同上,第12页。
[238]同上,第11页。
[239]同上,第8—9页。
[240]同上,第9页。
[241]同上,第9页。
[242]同上,第9页。
[243]同上,第9页。
[244]同上,第10页。
[245]同上,第10页。
[246]同上,第11页。
[247]同上,第11—12页。
[248]同上,第13页。
[249]同上,第14页。
[250]同上,第14页。
[251]同上,第15页。
[252]同上,第15页。
[253]同上,第66页。
[254]同上,第66页。
[255]同上,第61页。
[256]同上,第34页。
[257]同上,第250页。
[258]同上,第53页。
[259]同上,第53页。
[260]同上,第22页。
[261]同上,第294页。
[262]同上,第295页。
[263]同上,第295页。
[264]同上,第295页。
[265]同上,第296页。
[266]同上,第27页。
[267]同上,第27页。
[268]同上,第28页。
[269]同上,第28页。
[270]同上,第29页。
[271]同上,第302页。
[272]同上,第161页。
[273]同上,第161页。
[274]同上,第270页。
[275]同上,第271页。
[276]同上,第272页。
[277]同上,第282页。
[278]同上,第277页。
[279]同上,第278页。
[280]同上,第278页。
[281]同上,第279页。
[282]同上,第281页。
[283]同上,第272页。
[284]同上,第272页。
[285]同上,第283页。
[286]同上,第296页。
[287]同上,第297页。
[288]同上,第299页。
[289]同上,第299—300页。
[290]同上,第300页。
[291]同上,第300页。
[292]同上,第301页。
[293]同上,第301页。
[294]同上,第301页。
[295]同上,第302页。
[296]同上,第302页。
[297]同上,第304页。
[298]同上,第304页。
[299]同上,第295页。
[300]同上,第300页。
[301]同上,第300页。
[302]同上,第37页。
[303]同上,第37页。
[304]雅斯贝尔斯著,魏楚雄俞新天译:《历史的起源与目标》,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37页。
[305]雅斯贝尔斯著,魏楚雄俞新天译:《历史的起源与目标》,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44页。
[306]雅斯贝尔斯著,魏楚雄俞新天译:《历史的起源与目标》,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44页。
[307]雅斯贝尔斯著,魏楚雄俞新天译:《历史的起源与目标》,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53—54页。
[308]雅斯贝尔斯著,魏楚雄俞新天译:《历史的起源与目标》,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59页。
[309]雅斯贝尔斯著,魏楚雄俞新天译:《历史的起源与目标》,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59页。
[310]雅斯贝尔斯著,魏楚雄俞新天译:《历史的起源与目标》,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59页。
[311]同上,第39页。
[312]同上,第176页。
[313]同上,第177页。
[314]同上,第177页。
[315]同上,第177页。
[316]同上,第178页。
[317]同上,第178页。
[318]同上,第178页。
[319]同上,第178页。
[320]同上,第180页。
[321]同上,第180页。
[322]同上,第179页。
[323]同上,第180页。
[324]同上,第144页。
[325]同上,第158页。
[326]同上,第145页。
[327]同上,第159页。
[328]同上,第159页。
[329]同上,第58页。
[330]麻天祥,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教授;李彤、韩燕丽,武汉大学哲学学院学生。
[331]1574年,范礼安到日本传教,观察到日本僧人极受当地民众的尊重,并敏锐地意识到了服饰所包含的文化内涵以及对传教的助力,范礼安明确地要求传道士们,入乡随俗,改穿属于社会上层人士或文化精英者的僧服。
[332]裴化行:《利玛窦神父传》上册,北京:商务印书馆,1993年,第82页。
[333]柯毅霖:《晚明基督论》,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9年,第130页。
[334]罗光:《利玛窦传》,台北:学生书局,1983年,第47页。
[335]圆澄《慨古录》,转引自马晓英《晚明天主教与佛教的冲突及其影响》《世界宗教研究》2002年第4期。
[336](意)利玛窦、(利)金尼阁著,刘俊余、王玉川译:《利玛窦中国传教史》,台北:光启、辅仁联合出版社,1986年,第89页。
[337]参见拙作《中国宗教哲学史》第九章附录,人民出版社,2006年。
[338]李之藻编,黄曙辉点校:《天学初函》,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271页-第295页
以下所引《辨学遗牍》原文均引自该书该版。
[339]其实未必,这里只不过是虞氏对利氏批评的委婉表述。
[340]即娓娓。
[341]所指中国汉译佛经。
[342]今译毕达哥拉斯。
[344]见拙著《中国近代学术史》第一章,第三节,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年。
[345]《辨学遗牍》原跋一,凉庵居士。
[346]黄超,武汉大学哲学学院副教授。本文获得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14JZD034)资助。
[346]威尔弗雷德·史密斯在《宗教的意义与目的》中把宗教的内容划分为“信仰”和“信仰的表达”两个层面,以为宗教信仰是宗教的非历史的彼岸的、不可观察和不可定义的神圣层面,而信仰的表达则属于宗教的历
史的、可以观察和可以定义的尘世层面。蒂利希在《新教时代》中也从两个层次来界定宗教,其中一个为“神秘因素”,他称之为宗教的“纵向坐标”,另一个为“文化因素”,他称之为宗教的“横向坐标”。(参见段德智:《宗教学》,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393页。)
[348]儒家是否是宗教的问题历来存在争议,但是,对儒家或儒学具有“宗教性”的看法似乎已经成为共识。
[349]美国汉学家孟德卫指出,利玛窦来到中国的时候,中国在文化史上正处于一个非常有创造力的时期。儒家融合众说与重新诠释经典的理论倾向为利玛窦提供了本土化的文化空间。
[350]方豪在《中西交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中认为,“僧”字系万历十一年罗明鉴与巴范济在肇庆所创用。最初期教士之用“僧”字,并无依附佛教之意,但亦不排斥佛教。见该书689页。
[351]利马窦著,罗渔译:《利马窦书信集》(上),台北:光启出版社、辅仁大学出版社联合发行,1986年,第163页。
[352]季羡林:《鸠摩罗什时代及其前后龟兹和焉耆两地的佛教信仰》,《孔子研究》,2005年第6期,第30页。
[353]释慧皎撰、汤用彤校注:《高僧传》,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507- 508页。
[354]同上。
[355]释慧皎撰、汤用彤校注:《高僧传》,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507- 508页。
[356]王昆吾、何剑平,《汉文佛经中的音乐史料》,巴蜀书社2002年版第588- 589;609- 612页。
[357]僧肇:《注维摩诘经序》,载《中国佛教思想资料选编》,中华书局,1981年,第1卷119页。
[358]僧睿:《大品经序》,载《大正藏》第55卷53页。
[359]陈寅恪:《鸠摩罗什译经的艺术》,岳麓书社,1986年,第185页。
[360][唐]释慧立、释彦悰:《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中华书局,1983年,第216页。
[361](美)孟德卫:《奇异的国度:耶稣会适应政策及汉学的起源》,陈怡译,大象出版社,2010年,第52页。
[362]谢和耐:《中国与基督教——中西文化的首次撞击》,耿昇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28页。
[363]同上,第368页。
[364](美)孟德卫:《奇异的国度:耶稣会适应政策及汉学的起源》,陈怡译,大象出版社,2010年,第57页。
[365]葛伦斯、奥尔森:《二十世纪神学评论》,刘良淑、任孝琦合译,校园书房出版社,1998年11月,第79页。
[366]段德智:《宗教学》,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一版,第416页。
[367]F. Max Müller, Lectures on the Origin and Growth of Religion as illustrated by the religions of India, New York: AMS press, 1976, p.310.
[368]C. K. Yang,Religion in Chinese Society,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2,p. 6.
[369]杨庆堃著、范丽珠译:《中国社会中的宗教——宗教的现代社会功能与其历史因素之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269页。
[370](美)孟德卫:《奇异的国度:耶稣会适应政策及汉学的起源》,陈怡译,大象出版社,2010年,第373页。
[371](美)孟德卫:《奇异的国度:耶稣会适应政策及汉学的起源》,陈怡译,大象出版社,2010年,第369页。
[372]谢和耐:《中国与基督教——中西文化的首次撞击》,耿昇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226页。
[373]方豪:《中西交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688页。
[374]段德智:《宗教学》,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416页。
[375]得特勒夫·霍尔斯特:《哈贝马斯传》,章国锋译,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0年,第61-62页。
[376]宗辰欣,武汉大学国学院博士生。
[377]涩泽荣一,宋文、永庆译:《论语与算盘——商务圣经》,北京;九州出版社,1994,第5页。
[378]涩泽荣一:《论语讲义》,日本,讲谈社 ,1986,第一卷第19-20页,转引自张立文:《儒教开出东亚近代的外王之路——论涩泽荣一的“论语算盘说”》。
[379]涩泽荣一:《论语与算盘——人生·道德·财富》,王中江译,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7,第98页。
[380]土屋乔雄主编:《涩泽荣一传记资料》,日本,龙门社,1961,第41卷,第381页。
[381]涩泽荣一:《论语与算盘——人生·道德·财富》,王中江译,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7,第123页。
[382]涩泽荣一:《论语与算盘——人生·道德·财富》,王中江译,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7,第40页。
[383]同上,第8页。
[384]同上,第40页。
[385]涩泽荣一,宋文、永庆译:《论语与算盘——商务圣经》,北京:九州出版社,1994,第81页。
[386]涩泽荣一:《论语与算盘》,北京,九州出版社,1994,第4-5页。
[387]涩泽荣一:《论语与算盘》,中国青年出版社,1996,第16页。
[388]涩泽荣一:《论语与算盘》,北京,九州出版社,1994,第165页。
[389]戴季陶:《日本论》,北京,九州出版社,2005,第18页。
[390]新渡户稻造:《武士道》,周燕宏译,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09,第8页。
[391]戴季陶:《日本论》,北京,九州出版社,2005,第18页。
[392]戴季陶:《日本论》,北京,九州出版社,2005,第41页。
[393]同上,第44页。
[394]涩泽荣一:《论语与算盘》,北京,九州出版社,1994,第5页。
[395]涩泽荣一:《论语与算盘——人生·道德·财富》,王中江译,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7,第2页。
[396]同上,第123页。
[397]涩泽荣一:《武士道与实业》,《青渊百话》上卷,同文馆,明治45年,第196页,转引自张立文:《儒教开出东亚近代的外王之路——论涩泽荣一的“论语算盘说”》。
[398]涩泽荣一:《论语与算盘——人生·道德·财富》,王中江译,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7,第3页。
[399]涩泽荣一:《论语与算盘》,北京,九州出版社,1994,第110页。
[400]同上,第94页。
[401]木昌村一:《涩泽荣一》,中公新书1991年版,第一卷,第507页。转引自周见:《涩泽荣一的实业思想与日本资本主义精神》。
[402]涩泽荣一:《论语与算盘》,北京,九州出版社,1994,第77页。
[403](日)涩泽翁颂德会:《经济与道德》,周见译,1938,第1页。
[404]涩泽荣一:《论语讲义》,日本,讲谈社 ,1986,第一卷第34页。转引自张立文:《儒教开出东亚近代的外王之路——论涩泽荣一的“论语算盘说”》。
[405]沟口雄三:《“公”的概念在中国和日本的区别》,冉毅译,《船山学刊》1999年第二期
[406]土屋乔雄编:《涩泽荣一传记资料》,日本,龙门社,1961,别卷5,转引自周见:《涩泽荣一的实业思想与日本资本主义精神》。
[407]同上,别卷5
[408]《涩泽荣一全集》,日本,1卷,周见译,第509页。
[409]涩泽荣一:《论语讲义》,日本,讲谈社,1986,第四卷,第40页。
[410]村山弗编:《涩泽荣一翁:对经济人的训斥》,日本,文艺社,1992,第24页。转引自冯玮:《涩泽荣一经济伦理思想的历史渊源及其对日本后世的影响——“论语算盘论”的历史定位》。
[411]同上,第38页。
[412]《涩泽荣一全集》,日本,2卷,第583页,转引自周见:《涩泽荣一的实业思想与日本资本主义精神》
[413]涩泽荣一:《论语与算盘》,北京,九州出版社,1994,第119页。
[414]同上,第94页。
[415]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上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第101页;蔡尚思:《孔子思想体系》,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第93页。
[416]徐复观:《中国思想史论集续篇》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第254页。
[417]涩泽荣一:《论语与算盘》,北京,九州出版社,1994,第210页。
[418]同上,第210页。
[419]同上,第7-8页。
[420]涩泽荣一:《论语讲义》,冯玮译,第四卷,第140页。
[421]同上,第142-143页。
[422]涩泽荣一:《公生涯与私生涯》,《青渊百话》上卷,同文馆,明治45年,第71页,转引自张立文:《儒教开出东亚近代的外王之路——论涩泽荣一的“论语算盘说”》。
[423]涩泽荣一:《论语与算盘》,北京,九州出版社,1994,第19-20页。
[424]涩泽荣一:《论语与算盘》,北京,九州出版社,1994,第144-145页。
[425]同上,第191页。
[426]涩泽荣一:《论语与算盘》,北京,九州出版社,1994,第32页。
[427]同上,第66页。
[428]同上,第53页。
[429]同上,第33页。
[430]同上,第134页。
[431]涩泽荣一:《论语与算盘》,北京,九州出版社,1994,第171页。